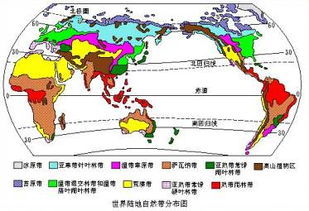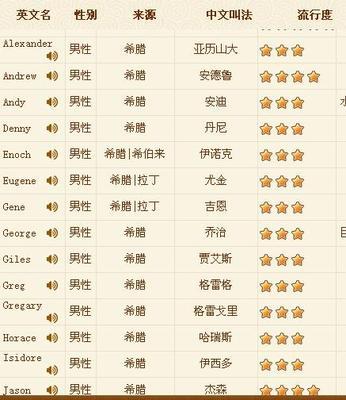自然淘汰,是指一种自然的基本竞争和淘汰法则。弱势群体,则是近两年来颇流行的一个词汇,指那些在社会中处于极端不利地位或状态的我们的同胞,说白一点,就是活得太差甚至根本活不下去的一部分公民。将这两个词语并在一起,来写这篇文章,一方面是因为在一定角度上,社会的生存环境实在比自然的生存环境好不了多少,另一方面,社会毕竟不是自然,人毕竟不是动物,更毕竟不是植物。
我们知道,自然淘汰是非常残酷的,在央视的《动物世界》栏目中,就播放过狼群袭击野牛的情形,幼牛由母牛护着向前奔跑,但仍然时有掉队的幼牛和病牛成为狼的口中餐。其实,动物界也就是这样的,正如物质能量转换与守恒一样,一种动物是另一种动物的食物,一种动物的死亡转换为另一种动物的生存、欢乐和希望。
人类社会与动物群体的差别,在这儿是显而易见的。人就是最厉害的动物,基本上只有人残害其它动物的份,所以说如果人被残害,不用说,那准是来自于他的同类。动物不足以成为人的对手时,人的对手就只剩下自己的同类了。人对同类的残害,连动物也作不出来,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其著名的《生物圈》中说:“人类还彼此互相扑噬。高度发达的社会就实行过同类相食和使用奴隶的作法。”不过,人之为人,残害同类时也不会忘记披上文明的、金光灿烂的外衣。在这方面,有一刀解决的、酣畅淋漓的残害,比如异族间的战争、争权夺利的国内同室操戈、镇压革命者,也有像猫玩老鼠的游戏,或写文章一样,弄点情节、悬念和趣味的残害。这篇文章的着眼点,就在后者。大概人比动物聪明,懂得刺激性,知道残害同类,与残害动物相比,其获得的快感真是天壤之别。难怪有人乐此不疲了。
不过,“弱势群体”一词历经数千年而浮出水面,也多少表明一直绷得太紧的社会政治神经稍稍有些松弛,真实的生存,艰难地得到了承认,在沉重的背后,有了步履蹒跚的进步。如同面对百万雄师的包围,终于将它撕开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口子。这是艳若桃花的希望,但犹如沙漠上的生命那般遥远和渺茫,能够企及的,或许更多只是风沙。
中外历史上,含冤悲惨而死、活得猪狗不如者,不甚枚举。《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包身工》等这些作品,都曾有过描述。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将军的领地,就占去全国四分之一,另外的土地,被二百六十几个大名瓜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只能租种土地,累断腰杆种出来,眼睁睁看着被拿走,有的只能得到余下的二成,饿死者当然不计其数了,令人发指的是,居然还有比农民地位更为低下、更为悲惨的“秽多”、“非人”。开端于十五世纪四十年代、长达四百多年的猎捕和贩卖黑人,马克思在《英国政府和奴隶贸易》中称之“贩卖人类血肉”,这些黑人的命运,比起任何动物来,实在都还要惨得多。中国现在还残留着的贞节牌坊,也足以让我们追寻,那些青春鲜活的女人,灵性与芬芳的生命,被吃人的政体和害人的文化夭折、摧残于历史的渺渺逝波中。死者死矣,活着的,再怎样惨,得活着,总不至于都去自杀,毕竟生存是人的本能,何况自杀需要的勇气,不会有几个人具有,再说,子民都死光了,还有谁去纳税、服劳役?说生存权也罢,自由权也罢,权不权的,管不了,就暂时别去管那么多,活着才是硬道理。余华的小说《活着》,就有点这种意义,一个历经磨难,家破人亡的孤身老头,只剩下同样孤苦的一头老牛与他做伴,在悲愤中人与动物同化,难分难舍,一起等待死亡的终点。说一句题外话,我觉得,这头老牛的本性,实在比不少人真善美得多,可爱得多,如果人人都比得上这头老牛,这世界也就平和了。
自小我大概就是所谓弱势群体中的一员。生在偏僻的农村,四渡赤水河就从那儿渡过。渡是渡过去了,几十年风雨尘埃已过去,那儿的老百姓还是老样子,看不出被渡到了什么仙境福地。在我的记忆中,只有无尽的辛劳、难挨的饥饿与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标语口号。在那儿,在所谓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下,曾经饿死多少人,难以历数,我只清楚,在三年困难时期,我那无比善良、无比勤劳的曾祖母,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好河山的田野上劳动着,饿得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没过多久,我的祖母,一个很会唱山歌、热爱生活的农村妇女——我的艺术熏陶,就是从她的山歌开始的——在集体劳作中被社会主义的石头砸残了腿,丧失了劳动能力,从此几十年,只能勉强在家里做一下饭,没得到丁点儿补偿,艰难可想而知,所幸的是,一家子挺了过来,现在人丁兴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都有她的后人谋生,我也呆在这个城市,现在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文字。她老人家更是命大,当年春风得意的人早就不太好看地死光了,而她拖着伤残的腿,活了八十好几岁,直到一年多前才去世。
在我刚开始学识字时,每家的门上都贴上了阶级斗争的大红纸,其内容是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类,这样的内容还充满猪圈、墙壁和野外的石头、土坎,当然,绝不会遗漏我的小学课本。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接受新知,判断社会和事物。现在想来,让弱势群体投身到政权中,和强势群体一起干自己吃不饱饭的革命,犹如老鼠投身猫的革命一样,永远讲不通,只能算是空前绝后的创意,但这就是真实的现实。这样对同类的玩弄和残害,其手段的高明、厉害,再好玩的游戏,再多悬念、情节,再生动的文章,也永远比不上它的精妙。
最大、最弱势的群体,就是农民。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起义,都叫农民起义。整个社会中付出最大、最多的阶层是农民,收益最少、被任意驱使、宰割的阶层也是农民。农民被置于整个政治利益的风口浪尖,不管什么风,只要不是好风,就往农民身上吹;要割肉,要侵犯、牺牲别人的利益,首先就把刀伸向农民的脖子。几千年来,农民只能付出,没有任何提要求的权利,被剥夺了话语权,被剥夺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权利,连识字也只有中小地主子弟才有资格。漫漫数千年,有几个显贵、文人为农民说过一句公道话?
余华还有部小说,叫《许三观卖血记》,我没看过,但一听标题,来个“望标题生义”,就估计是写一个无奈卖血的社会底层小人物,染上艾滋病的故事。不知猜想得是不是正确?如果是,那真是挂一漏万,不知道生活中有多少个许三观?记得十多年前,艾滋病还是个洋玩意,是富得流油、骄奢淫逸、同性恋或性生活混乱的老外的专利。听官方宣传,不必惊慌,与自律的国人无涉。刚吃了定心丸,觉得遥不可及的洋东西,就先有国人卖淫、官员公费或大款自费嫖娼染上,这叫咎由自取,用人家的血汗钱,得自己的致命病,说一万个活该也不过分。但才眨眼间,河南大量穷得无可比拟的农民,还有四川资中一带的数十名农民,就大规模、大兵团地得了这富贵病了。
为什么解放了那么多年,还有这么多农民穷得不惜身家性命卖血?最投入劳力、最不偷奸耍滑的农民,为什么就养不活自己?他们的劳动成果到哪儿去了?每一个多少有点良心的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去寻找一下答案
中国的现代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现代城市是怎样修起来的?那些不可一世的现代富翁是怎样富起来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农民的粮食,被控制的、不成价格的粮食,当然还有对农民的乱摊派。农业的一头大肥猪,居然买不到工业的一双高档猪皮鞋。庆幸的是,中央政府已在关注三农问题,减免了农民的赋税。但一个好的政策,未必就一定有好的结果。减免农民赋税刚有点风声,什么化肥、农药就疯狂涨价,农民变成了唐僧肉,各路妖怪都想扑上去咬一口。

要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恐怕不是一两个好的政策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三五十年就能解决的。问一问我们的各级政府,各个官员,各路靠农民兄弟血汗发家的社会人士,长时期以来,有几个把农民的利益真正搁在心窝里?这段时间,传说有一大群农民,颇似一群游侠,专往大城市人多的地方钻,手拿针管,扎到谁算谁,谁一沾上,就被艾滋病铆上了。听来令人毛骨悚然。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出门就心惊胆寒。据说,这是一些卖过血的艾滋病患者,一直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实在活不下去,找过几级政府,得不到答复,就来个反馈,将其在社会上得到的艾滋病返之于社会。如果他们反馈给相关的人,也算反馈得正是地方,得体之举,我不会反对,但反馈给无辜者,岂不是空穴来风,大大的冤枉?这故事是否真实,没必要去考证,要紧的是,不要把人整得过惨,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同时,应当给弱势群体足够的关爱,更不要去歧视他们,既得了便宜,稍稍卖点乖,有何不可?人可不是动物,还是应当有点怜悯之心,把人当人看待。多些宽宏,多施点仁政,才会赢来民之淳朴,正如老子所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近来,有一些关爱艾滋病人的宣传,也有一些人投身进去,有了切实行动,这就不错,但实在不够,只是杯水车薪、隔靴搔痒。如果政府不动用大的气力,不把整个社会都发动起来,就难从根本上把问题解决。
弱势群体不光农民,整个社会底层的、为生计而苦恼的、法律给予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的人,都应当计入弱势群体的范畴。让我们来看一下从九十年代初、中期以来,社会底层的经济状况,物价涨了几十倍,而他们的收入,可能也就只有几倍。广东东莞一带的民工,每月工资五、六百元,还要被老板克扣,在当地维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难,一天还有十多个小时的强力劳动,媒体曾一度焦点性地报道。在中国,这种情形岂止东莞?工人这样的劳动和收入状况,不知道古今中外,有否存在过?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还达不到这样的收入标准。现在有一句经典的话,叫做干活的不拿钱,拿钱的不干活。造成弱势群体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本性使然,如同自然淘汰一样,强势群体比强势物种不知厉害好多倍,毫无人性的自私和贪婪,不断挤压弱势同类的生存空间,使弱势群体的话语权丧失殆尽——如同作空气的分离实验,氧气已被拿走,只剩下一点技术上无法提取的残留,以及大量的、无法呼吸的氮气了。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写贪得无厌的“嗜取者”,犹如一种极爱负重、极力登高,不到坠地而死不罢休的小虫,一旦得势,不停地捞取财物,每天都想着爬到更高的官位,变本加厉,看到前面的人因贪而死也不引以为戒,所谓的强势群体们,大概就是这样的小虫,只是不知他们的贪婪是本性使然,还是因为前面因贪而死的人实在少了些,或者是二者内外媾合的绝配。另一方面,几千年来的强权统治、愚民策略、文化的奴化功能,生产了不少十足奴性的产品,左脸被打肿了,还会乖乖地伸出右脸,就算以法律的形式给了他权利,他也未必就敢争取;捧到他的手上,他未必就享受得坦然。所以,一个国家的进步,没有关于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的大规模教育,没有这方面知识的扫盲,看来是难以实现的。
现在被称为弱势群体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他们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亦无法所知。不过,这样的人越多,就越危险,社会的前途,就会关山阻碍、云雾飘渺。贫富悬殊程度,是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的直接反映,是一个国家的物质分配方式的直接结果,是一个国家“公共权力”的公共程度晴雨表。一个国家的贫富悬殊太大,便表明民主程度不高,分配不合理,权力的私有化程度太严重。任何经济变革,如果是以牺牲社会底层大众的利益来获得少数人财富的积累,以牺牲多数人的消费能力来获取社会投资的增长,就算有孙猴子的七十二变,也变不出持续、长久发展的花样来。这样的变革只会带来市场的萎缩,带来经济的“龙头蛇尾”——社会财富结构的“龙头蛇尾”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龙头蛇尾”,只会带来社会矛盾、社会对抗和社会动荡。伟大的哲学家张载在《行状》中说:“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若不从根本上解决贫富悬殊,让弱势群体获得同等待遇,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社会的发展就不可能和谐,那么,任何政治经济改革措施都不会水到渠成、一战即胜,无非是谋求暂时、局部利益的苟且办法而已。
浮在面上的弱势群体,经常在媒体中提到的,还有下岗职工、低保,时常有国家领导人出来发表关心他们的讲话。遥想当年,把工人阶级捧上了天,说是领导阶级,现在居然还有领导干部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不知道用意何在,作何指谓。尽说便宜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可终究说服不了几个人。工人含辛茹苦,以厂为家,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创造过不菲的税收和利润,为什么工厂垮了,就把痛苦摁在工人身上,而弄垮工厂的一些刽子手,竟安然无恙?
暴露在大街上的弱势群体,主要是一些乞讨人员,其中更多的是缺胳膊少腿的、瞎的、年老无助的残疾人,间或有一两个读不起书的学生。实际上,给予他们施舍、救助的人,大多属于弱势群体范畴。能给穷人接济的,大抵也就只有穷人,要不就不会有“阶级”这个词,就不会有“为富不仁”这一说了。属于强势群体的,一些执法人员,时常把他们当作一件华丽的衣衫上的几个邋遢补丁,有碍观瞻,与文明不大协调,吆喝一气,甚或撵走。早就有人在报纸电视上评论,说乞讨已几乎成为一门职业,有些人甚至不惜故意致残以求获得乞讨的入场券。这样的评论真是不可思议,远远超过黑色幽默,我实在佩服这些老兄,一本正经地想得出来。堂堂大国,养不起几个彻底无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说来真是笑话。不管再小的地方,政府再穷,财政再少,也不至于就拿不出几个残疾人的稀饭钱。大一点小一点的领导,少喝一次“革命小酒”,少唱几句“革命情歌”,就再多几个残疾人,也不至于到大街上破烂衣衫面对寒风呼天抢地乞讨了。
学生也是弱势群体,因为是小孩,不仅体力上弱势,智力上也弱势,更谈不上什么话语权了。因此,怎样对待他们,除了父母天然本真的疼爱,那就靠社会的责任和良心了。近些年,校园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有学生致伤致残的,死亡的,七八岁就被老师强奸的。至于传输给他们什么东西,是个比较敏感和颇有争议的话题,不说也罢。
我六岁读一年级时的一次经历,三十年未曾忘怀,也还稍稍符合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因此不揣冒昧写在这里。那时我在生产大队的民办小学读书,刚入校没几天里的有一天,临近放学,老师不由分说,突然狠骂了我一顿,跑到最后一排我的座位前,用圆珠笔在我的小脸上乱画一气,随后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拖到讲台,使劲揣了几脚,疼得我分不清苍天大地,一急之下,冲垮墙壁(教室门紧靠最后一排座位,讲台附近的墙壁,用竹片编成架,再用泥敷上,日久天长,泥土松脱,竹架散开,稍一碰就会土崩瓦解——作者注),以极限的速度跑回家,一看父母集体劳动去了,只一个人蒙了片刻,在房前的一块大石上呆坐了好一阵子。事后知道,在我们几个生产小队上学必经的路上,有几块光滑的石头,上书有“曾钟钟”字样,而“曾钟钟”是我们伟大的民办曾老师的老爷子的别号,有高年级的学生告诉曾老师:张修林平常喜欢在石头上乱画,可能是他干的——顺便说一句,当时老爸还没有来得及给我取上张修林这个学名,这位学生说的,应该是我的小名。这位学生是谁,我不知道,也从未去探究过,不过知道他现在一定在四川的古蔺县种地,因为那几届学生中,尽管我不太出息,却是混得离那儿最远的唯一人物。他说的不错,我从小就有喜好学习的天性,又穷得没有笔和纸张,喜欢在石头上画上画下,的确说得过去,至于“曾钟钟”的字样是不是出自我的聪明才智,可能读者已经猜到,一个才入校几天的小毛孩,如果不是天才,断然写不出这几个魅力四射的方块字。大家猜对了,我的确不是天才,就算是,也不会写得出,因为在那时,那儿没有幼儿园什么的,识不了多少字的父母也从未教过我一招半式。真不知道这种教育能带来什么后果,我猜想不会有人在这样的经历后还能幸福地跑去学校。幸而,我没有将情况告诉父母,在第二天还是去上学了,而我们敬爱的曾老师,不久后也去教育其它班级了。
农民也罢,下岗职工也罢,残疾人也罢,学生娃娃也罢,弱势群体的存在,如果是社会和文化无奈的选择;如果是宿命,弱势群体是社会和文化这些笼子中命定关着的鸟,那还有何话可说?不过,是笼子就要关鸟,在逻辑上讲不通,何况,笼中的鸟儿,面对湛蓝的碧空,总会抖动翅膀,产生飞翔的欲望,笼子也有关不住鸟的时候,也总有它空虚、朽腐、陈列在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不管是残害女人的贞节牌坊,还是压死孟姜女丈夫的万里长城,抑或皇帝惨绝人寰殉葬的墓穴,无论何其庄严、雄壮与巍峨,终将消沉、湮没于历史的深渊——再说,社会和文化为什么就不可以不是笼子,而是鸟儿们栖居的,温暖而富于诗意与激情的巢穴,套用荷尔德林的诗:在社会和文化中诗意地栖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