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源的匮乏实在的说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面对现状,人们的观点甚至是学者的观点是分成两派的:
一种是认为中国在资源上已经到了存亡的关头,将资源的缺乏提到了恐怖的边缘.这是悲观派.
还有一种就乐观的多,资源对于他们显然是很抽象的概念,他们还照浪费不误.
对于中国的资源现状我是很以为忧的,但我又绝不是第一类人.
我从另一个方向看:资源的枯竭对于石油国未必是好事,同样对于中国这样的资源匮乏国也未必就不是好事情,理由有二:
一.诚如托马斯·L·弗里德曼在他的石油政治定律一文说写到的:
几年来,当我追踪波斯湾的事态发展时,我注意到,巴林是第一个举行妇女可以参选和投票的自由公平选举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它也是全面修改自己的劳工法,以使本国人民更加容易受雇和更少依赖输入劳力的第一个阿拉伯海湾国家。而巴林恰好是预计会采光石油的第一个阿拉伯海湾国家。它也是该地区第一个与美国签订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我不禁自问:“这一切可能都是巧合吗?”最后,我放眼望向阿拉伯世界另一端,看到黎巴嫩获得民众支持的民主积极分子正在把叙利亚部队从他们的国家赶出,不禁自言自语:“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恰好一滴石油也没有,这是偶然吗?”
石油政治学的第一定律规定如下:在石油储量丰富的石油主义国家,油价和自由的步伐总是朝着相反方向移动。根据石油政治的第一定律,原油的全球平均价格越高,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选举的自由与公平、司法的独立性、法治和独立的政党就越是受到侵蚀。使这些消极趋势得到加强的是,价格越高,石油主义领导人就越对世人对其怎样想和怎样评价麻木不仁。按照这一定律,相应地,油价越低,石油主义的国家就越是被迫朝着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迈进:它比较透明、对反对派声音比较敏感,比较注重建设会使本国人民不分男女,在竞争、创办新公司和吸引国外投资方面的能力最大化的法律和教育结构。原油价格越低,石油主义领导人就对外部势力如何看待他们越敏感。
二从生物学的角度从适者生存的学术观点出发:这样的现实也必然会强迫它的国家和人民去不断的创造,去不断的激发它的人民的创造力。
相关链接:
石油政治学第一定律
作者:托马斯·L·弗里德曼
(原文提要:伊朗总统否认二战期间曾发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乌戈·查韦斯要西方领导人下地狱;弗拉基米尔·普京自以为得计。为什么?他们知道,油价和自由的步伐总是在相反方向上挺进。这是石油政治学的第一定律,可能也是解释我们时代的座右铭。)
我听到伊朗总统内贾德宣称,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个“神话”,于是不禁自问:“我很想知道,假如今天的油价是每桶
20美元,而不是每桶60美元,那么伊朗总统会这样讲吗?”我听到查韦斯要英国首相布莱尔“直接见鬼去”,并对其支持者说,美国一手操纵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也“可以见鬼去”,因而不禁自言自语:“我很想知道,如果今天的油价是每桶20美元,而非60美元,以致委内瑞拉不得不靠赋予本国企业家以权力来谋生,而不是靠钻油井,那么该国总统还会说这一大通吗?”几年来,当我追踪波斯湾的事态发展时,我注意到,巴林是第一个举行妇女可以参选和投票的自由公平选举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它也是全面修改自己的劳工法,以使本国人民更加容易受雇和更少依赖输入劳力的第一个阿拉伯海湾国家。而巴林恰好是预计会采光石油的第一个阿拉伯海湾国家。它也是该地区第一个与美国签订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我不禁自问:“这一切可能都是巧合吗?”最后,我放眼望向阿拉伯世界另一端,看到黎巴嫩获得民众支持的民主积极分子正在把叙利亚部队从他们的国家赶出,不禁自言自语:“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恰好一滴石油也没有,这是偶然吗?”
我越是考虑这些问题,似乎就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油价和某些国家的政治自由与经济改革的速度、范围及可持续性之间,一定有一种相关性——一种可以衡量和用图表示的、毫不夸张的相关性。几个月前,我与本刊的编辑们接洽,要他们试一试我们是否能够办到这一点——努力用图的形式对这一直觉加以量化。沿着一条轴,我们将标绘出原油的全球平均价格;沿另一条轴线,我们将绘制自由不断扩展或萎缩的速度,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讲,按照“自由之家”等研究机构所能提供的最精确数字。我们将考察已经举行的自由公平的选举、开办和倒闭的报纸、强行逮捕、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的改革派、已经开始或停止实施的经济改革计划、私有化和国有化的公司等。
我会第一个承认,这不是一场实验室里的科学实验,因为在一个社会中,经济与政治自由的兴衰从来都不是完全可以量化或者相互兑换的。但是,由于我并没有试图在任何地方获得终身教授职位,而是要为一种直觉提供素材和刺激一场讨论,所以我想,对油价和自由的步伐两者之间的这种十分真切的相互关系努力加以证明是有价值的,尽管这样做也是有缺陷的。由于原油不断上涨的价格在近期内影响国际关系方面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努力认识到它与全球政治的性质和方向之间的任何联系。这里所搜集的图表肯定表明了油价和自由的步伐之间的一种很强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很强,以致我希望提出石油政治学的第一定律,从而为这场讨论抛砖引玉。
石油政治学的第一定律规定如下:在石油储量丰富的石油主义国家,油价和自由的步伐总是朝着相反方向移动。根据石油政治的第一定律,原油的全球平均价格越高,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选举的自由与公平、司法的独立性、法治和独立的政党就越是受到侵蚀。使这些消极趋势得到加强的是,价格越高,石油主义领导人就越对世人对其怎样想和怎样评价麻木不仁。按照这一定律,相应地,油价越低,石油主义的国家就越是被迫朝着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迈进:它比较透明、对反对派声音比较敏感,比较注重建设会使本国人民不分男女,在竞争、创办新公司和吸引国外投资方面的能力最大化的法律和教育结构。原油价格越低,石油主义领导人就对外部势力如何看待他们越敏感。
我对石油主义国家的定义是,它们不仅出口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都依赖石油生产,而且国家机构薄弱,或者其政府是不折不扣专制主义的。在我的石油主义国家名单上排在前列的有阿塞拜疆、安哥拉、乍得、埃及、赤道几内亚、伊朗、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和委内瑞拉。(而如果拥有很多原油,但国家也很稳固,在发现石油以前拥有牢固的民主制度和多元化经济,这样的国家——例如英国、挪威、美国等——就不会受石油政治学第一定律支配。)
可以肯定,长期以来,专业经济学家就笼统地指出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会对一国产生消极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诊断结果各不相同,分别称之为“荷兰病”和“资源的诅咒”等。荷兰病指的是自然资源方面突然的意外收获可能会造成的去工业化过程。该词是20世纪60年代在荷兰杜撰的,因为该国发现了天然气的大量储藏。患有荷兰病的国家所发生的情况是,由于石油、黄金、天然气或钻石等自然资源的发现所带来的现金突然涌入,其货币升值。这样一来,该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就没有竞争力,而进口却很便宜。怀揣大量现金的公民们开始疯狂地进口,国内工业部门被消灭,一转眼,就发生了去工业化。“资源的诅咒”可以指同一经济现象,更为宽泛地讲还有依赖自然资源如何总是使一国的政治、投资和教育重点出现偏差,以致一切都围绕着谁控制石油开采权,以及谁从中获得多少等——而不是如何进行竞争、创新和为真实的市场生产真实的产品等。
除了这些一般性的理论外,一些政治学家还进行了探索,尤其是关于拥有大量石油财富如何能够使民主化趋势发生逆转或受到侵蚀。我所遇到的最中肯的分析之一,就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政治学家迈克尔·
L·罗斯的研究。罗斯利用1971年到1997年期间从113个国家获得的统计分析结果得出结论:一国“若依赖石油或矿产出口,往往会使其民主制被削弱;这一效应不是其它类型的初级产品出口所造成;也不限于阿拉伯半岛、中东或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而且并不局限于小国。”我发现,罗斯的分析中尤其有用之处,是他所罗列的有关过度享有石油财富阻碍民主的确切机制的清单。他争论说,首先是“税收效应”。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的政府往往利用其收入来“缓解社会压力。否则,这种压力可能会造成对政府权力的更大问责性的要求,”或者要求增加在政权中的代表。美国革命的座右铭是:“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而获得石油支撑的政权则不必向人民征税就能生存,因为它们能够简单地钻油井,所以不必倾听人民的意见,也不必代表他们的愿望。
罗斯争论说,石油削弱民主化的第二项机制是“开支效应”。石油财富导致更多地慷慨解囊,从而削弱了要求民主化的压力。他所列举的第三项机制是“集团形成效应”。当石油收入使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获得意外的现金收入,政府就能利用新获得的财富来阻止独立的社会集团——恰恰是最倾向于要求获得政治权利的集团——形成。他争论说,此外,获得过量的石油收入还能造成“镇压效应”,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就能把过多的开支用于警察、国内治安和情报力量,从而窒息民主运动。最后,罗斯认为还有一种“现代化效应”在发挥作用。石油财富的大量涌入能够减轻要求职业专门化、城市化和获得较高教育水平的社会压力——这些趋势通常伴随着范围广泛的经济发展,并培育出这样的公众:他们比较敢于发表意见,进行组织、谈判和沟通的能力较强,并拥有自己的经济权力中心。
石油政治学的第一定律试图强化这种论点,但同时使石油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在表述石油政治学第一定律方面,我不仅认为一般而言,过度依赖原油可能成为一种诅咒,而且人们实际上能够在石油的价格的升降和石油主义国家的自由的步伐的加快与放慢之间建立相互联系。这种联系是十分真实的。正如这些图所显示,当油价实际开始上涨时,自由的步伐实际上开始减慢。
一个石油轴心吗?
油价和自由的步伐之间有这种联系,其原因今天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我们看来正处于全球原油价格的结构性上涨的开端。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较高的价格水平几乎肯定会对许多弱小或专制主义国家政治的性质产生长期影响。这反过来可能会对我们所了解的冷战后的世界产生全球性的消极影响。换言之,原油价格现在应当是美国国务卿,而不仅仅是财政部长每天注重的问题。
自9.11事件以来,油价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从20至40美元的范围变为40到60美元。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与伊拉克、尼日利亚、印尼和苏丹等国的暴力活动所造成的全球石油市场上的普遍不安全感有关,但看来在更大程度上则是因为我所说的世界的“扁平化”,以及来自中国、巴西、印度和前苏联帝国的、全都梦想着拥有房子、汽车、微波炉和电冰箱的30亿新的消费者迅速涌入全球市场。他们不断增大的能源胃口是巨大的。这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对油价的压力的一个稳定来源。如果西方不引人注目地采取节能措施,抑或人类发现矿物燃料的替代物,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就会呆在这一40美元到60美元的范围内,甚至更高。
从政治上讲,这意味着,一大批具有薄弱制度或者其政府专制的石油主义国家很可能会遇到自由被侵蚀和腐败,以及独裁与反民主行为的加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可望使国家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增加,以加强治安力量,贿赂反对派,收买选票或公众的支持,并抵制国际规范和惯例。在每周的任何一天,人们只需拿起报纸,就能找到表明这种趋势的证据。
请考虑一下2005年2月《华尔街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谈的是德黑兰的毛拉们——由于高油价,他们现在腰缠万贯——背弃了一些外国投资者,而不是对其表示热烈欢迎。土耳其移动电话运营商Turkcell与德黑兰签订了一项协议,以建设该国第一个私人拥有的手机网络。这是一笔有吸引力的交易:该公司同意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许可证费用,并在该项目中投资22.5亿美元,从而为伊朗创造2万个就业岗位。但是,伊朗议会中的毛拉们将这项合同冻结,声称这样做可能会使外国人获得帮助,以便在伊朗进行间谍活动。阿里·安萨里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一位伊朗问题专家。他对本报记者说,10年来,伊朗分析家一直赞成经济改革。安萨里说:“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变糟了。由于高油价,他们有了这么多钱,因而不必做任何事情来改革经济。”
地质学战胜意识形态
尽管我对罗纳德·里根表示应有的敬意,但是我并不认为是他搞垮了苏联。虽然显然有许多因素,但是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全球油价的暴跌肯定起了关键的作用。(1991年圣诞节苏联正式解体时,每桶石油的价格徘徊在17美元左右。)较低的油价肯定还促使共产党垮台后的叶利钦政府更加倾向于法治,对外部世界更加开放,对全球投资者所要求的法律结构更加敏感。接着到来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请考虑一下油价在20美元到40美元范围时的普京,以及现在,即油价在40美元到60美元之间的情况下。油价为前者时,我们遇到我所说的“普京第一时期”。在2001年第一次会晤后,布什总统说,他窥视了普京的“灵魂”,在里面看到一个他能够信任的人。如果布什今天窥探普京的灵魂——在普京第二时期,即每桶60美元的普京时——那里面一片漆黑,像石油一样黑。他会看到,普京利用他在石油方面的意外收入吞没了(国有化了)庞大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各种报纸和电视台,以及各种俄罗斯企业和曾经独立的机构。90年代初油价处于低谷时,就连阿拉伯产油国,譬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拥有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的埃及,起码也谈论经济改革,即使不是婴儿学步的政治改革。但当油价开始上涨时,整个改革进程都放慢了,尤其是在政治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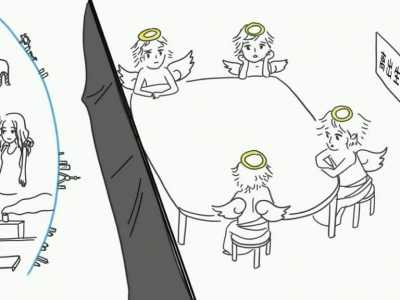
随着越来越多的石油财富在石油主义国家囤积,它实际上可能会开始造成整个国际体系和冷战后世界的性质本身的扭曲。当柏林墙倒塌时,人们普遍认为,自由市场和民主化的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也已经被释放出来。此后10年在全世界,自由选举的扩散使这一潮流成为现实。但是,这一潮流现在却遭遇到石油专制主义的一股出人意料的逆流。使之成为可能的,是每桶60美元的石油。突然间,伊朗、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政权正在退却,放弃了曾经似乎是不可遏止的民主化进程,其中每个国家的当选的独裁者都利用自己在石油方面突如其来的意外收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收买反对派和支持者,将国家的挟持范围扩大到私营部门,就在许多人以为国家已经永久地退却之后。在柏林墙倒塌后不可遏止的民主化浪潮,在石油专制主义的黑浪中看来遭遇到劲敌。
虽然石油专制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对西方构成的那种范围广泛的战略与意识形态威胁,但是其长期的影响仍然可能会侵蚀世界的稳定。不仅世界上的一些最恶劣的政权会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的时间里拥有额外的现款,而且体面的民主国家——例如印度和日本——也会被迫屈服于伊朗和苏丹等石油专制主义国家的行为,或者予以漠视,因为它们严重依赖这些国家供应石油。这对全球稳定来说不可能是有利的。
我要再次强调,我知道这些图所显示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绝对的,而且毫无疑问,有一些例外是读着肯定会指出的。但是,我的确认为,人们能够看到,它们所解释的一种一般趋势在每天的新闻中都反映出来:不断上涨的油价对许多国家自由的步伐来说,显然产生消极的影响,而如果有足够多的国家受到足够多的消极影响,全球政治就开始被毒化。
虽然我们不能影响任何国家的石油供应,但是我们能够通过改变自己所消费的能源的数量和类型,来影响全球油价。我说“我们”的时候,尤其指的是美国——因为它消费世界能源的25%左右——一般而言还指石油进口国家。要考虑如何改变我们的能源消费格局,以使油价降下来,因为这不再仅仅是超凡脱俗的环境主义者的一种爱好,也不是某种个人的美德,而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方面必须要做的事情。
因此,不论美国采取什么样的促进民主战略,如果不同时包括一项可信和可持续的战略,以找到石油的替代品,把原油的价格降下来,那么就是毫无意义和注定要失败的。今天,不论你处于对外政策光谱的何处,你都必须像“地理绿化派”一样思维。如果你不同时也是一位有效的能源环境主义者,你就既不能成为有效的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者,也不能成为有效地促进民主的理想主义者。(尹宏毅译)(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6年5月和6月号文章)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