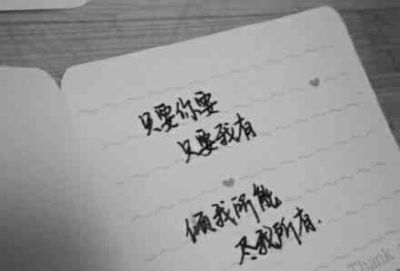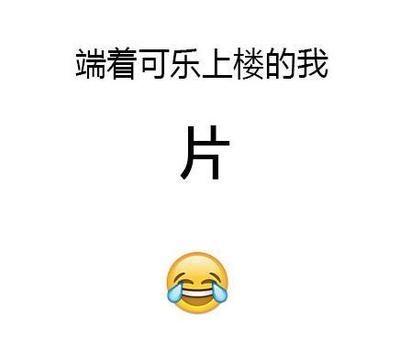中国篆刻史的两个高峰 时代周报:如果追根溯源,中国的印章最早是从何时开始? 韩天衡:我们现在能够见到最早的三方印应该是殷商时期的东西。从殷商一直到东周,东周的墓里面开始有典型的印章“玺”出现。在整个西周四百年里,考古发掘里没有印章出现。所以,我们现在讲学习印章实际上是讲东周以后。 印章作为一种信物可以说随着封建社会的出现和奴隶制度的崩溃,跟那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体制联系在一起。封建社会形成以后,要找一个东西来作证明、证件。军事上也好,政治机构的运作上也好,或者经济贸易也好,都要有一个东西作为凭据信物。比如你来我这儿订买五头牛,钱付了,牛要到几个月后再来牵,我怎么能够确定这东西是你的?印就成了中国最早的一种信物,这个东西对政治、经济、军事、商贸都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玺印是战国的,战国时候玺印用的文字是七国的文字,秦有秦的文字,楚有楚的文字,晋有晋的文字。以我们现在用艺术眼光来看,古时的文字从理念到书写都具有非常高的水平。秦始皇并吞了六国,用秦文字,汉代用缪篆,但作为印章艺术来讲,仅仅是换了一种篆字。制作印章的水平包括艺术性始终是高超的。 时代周报:古代印章留下来的多不多?艺术水准如何衡量? 韩天衡:多,大概没有人做过详细的一个统计。印章跟其他东西不一样。周秦两汉是高峰,到了隋唐朝以后是低谷。因为周秦两汉的时候,社会生活一天都离不开印章。诸如,官府的文书从地方要发到中央,这一卷竹子制作的“简牍”,扎好了以后在打结的地方上面用一个泥封封住,之后就拿官印钤在上面,这样就是密封了。如果到了中央这个封泥损坏了就说明可能泄露了,被人拆过了。所以,周秦两汉之后的印章,大多是钤在封泥上面。到了隋唐出现问题了,纸张盛行,印章怎么打到纸上去?材料没有及时解决。我们现在用印泥,印泥的制作要到明朝之后才做得精到。所以,唐宋元很多名家的书画上面印章很少,特别是唐宋。印章钤盖在纸上模糊不准,且难以持久,往往起不到鉴证作用。 我讲中国的篆刻史有两个高峰。一个就是周秦两汉,另一个就是从明末开始。明末材料的问题解决了,刻印采用了新引进的青田叶蜡石。青田石引进篆刻里,因为它软硬适中,易于镌刻,过去刻不了金、玉印的文人,都乐于提刀刻印了,于是这个队伍从印工变成了文人。这样一来,文人成了篆刻家的主体。所以,明代后期篆刻艺术又复兴了,成了中国篆刻史上的第二个高峰。这个现象在其他传统的文学艺术里是没有的。 时代周报:篆刻的风格会不会秦汉比较大气一点,到了明末比较文气一点? 韩天衡:凡是艺术,其最初都是出于实用,但里面赋予了很高的艺术内涵。所以我们今天拿它当成纯艺术品来看。周秦两汉是以国的疆域而自具风格,到明清由于文人的介入,就以地区甚至以个人形成风格,更见百花齐放。这又是明清跟周秦两汉不一样的地方。 它们的艺术性都非常高,是因为当时的印工。秦汉时期当然不叫篆刻家,也没这个称谓,但是制作印章的工匠使用当时的文字,感悟深刻且受者也都是行家,保证了很高的艺术性。从某个方面讲,明清的很多篆刻家的水准是不能跟周秦两汉比的。为什么呢?他使用的是古代文字,古代文字对古代印工来讲驾轻就熟的。而我们现在很多不高明的篆刻家连篆书都写不好的。 写好篆书是篆刻的基础 时代周报:篆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 韩天衡:我认为一个出色的篆刻家,首先是书法里写篆书的大家。我们刻印章都是以古代文字为主,不认识古代文字,老是写错别字,那怎么行?只解决这个字形,并没有解决这个字的艺术性。辞典是不能当法帖用的,所以,写好篆书乃至写出风格,对搞篆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回顾一下从清朝中期到现在,邓石如的篆书保证了他的篆刻是一流的。赵之谦,也会画,也会写,也会刻。吴昌硕,字和画都好。融会贯通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整个文学艺术是一个马蜂窝,特别是书法、绘画、篆刻、文学、诗歌,是紧挨在一起的蜂穴,一旦相互打通就可以相得益彰,左右逢源。老辈总是讲多读点书,刻图章的人不能一辈子就看一本印谱。古人讲要写好诗,功夫在诗外。要刻好一个印,功夫在印外,能书擅画,有文化,有修养,是综合工程。我对自己的指导思想就是四个字:诗心文胆。文学艺术是相互渗透、相互贯串的。字写得好,印章就可以提供一个篆法上的保障。字写得好,线条好,对画画就是一个保障。懂画的,写字刻图章就不会死板,他知道什么叫气韵生动。所以,篆刻要搞得好,字要好,要懂点画,不一定要成为画家。不一定要成为作家,但要有相当的文学修养,要有个人自塑的想法。从清中后期开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师级的篆刻家都是字写得好的,画画得好的,而且都是读过书的,都是可以写诗词的,不写诗歌也可以写文章的。

不过有时候,我开玩笑讲:搞艺术,老天爷给你这块料,也给你盘算好的,有些篆刻家写字就是写不好,有些书法家画画就是画不好。沈尹默先生的字写得那么好,他的画就欠佳。像邓散木印章刻得也不错,字也写得不错,文学修养也不错,画画欠佳。 时代周报:印章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东西,外国是否也有类似的艺术? 韩天衡: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在3000年前就有印押的使用,西亚有滚筒印,欧洲有火漆印,但是不像我们三千年不断地生发下去的。所以,印章就成了中国特具的民族瑰宝。 时代周报:现在社会渐渐数字化,电脑出现以后很多人连用笔手写也不用了,更不用说篆刻。你认为当代中国的篆刻艺术发展水平如何? 韩天衡:最近三四十年,印章基本上就是游离于使用,成为以赏玩为主的艺术。过去的印章首先是证件,或官府、军中的吏员,或是姓名章。明清已经拿很多的诗词歌赋放到印章里面去,就是所谓的闲章,带有很重的文学色彩。现在谁还拿一个大的图章去盖在一个领款单上?领工资也不会用印章了,都直接打到你的卡上了。所以,现在的篆刻艺术越来越摆脱实用而成为纯艺术。另外,篆刻艺术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多传统艺术里面发展得最快,人气最高,取得成绩也是最明显的。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这样呢? 韩天衡: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值得去探讨。一个就是它走向纯艺术,一个民族随着温饱的解决,对文化艺术的需求也必然更见渴求。第二个是队伍很强大,篆刻艺术确实有一个史无前例的很庞大的创作、研讨与欣赏群体。这三四十年来,在篆刻的领域里面,在创新突破和理论方面的努力都是超乎之前的。 就我个人来说,大致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在印风的创新上,二是在理论的探索和对史料的整理上,三是注重对篆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上。从1960年代后期收学生到现在,在大学里上课的不算,我的入室弟子有200多名。 “我是恋古的革新派” 时代周报:在中国的篆刻历史上,西泠印社是非常特别的机构? 韩天衡:西泠印社是1904年创建的,是几个对印章特别有嗜好的文人聚集在一起,以星星之火慢慢发展起来的。十年以后请吴昌硕当社长。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里面也有曲曲折折,也停掉过几次。西泠印社是一个古老而充满生机、饶有传奇色彩的社团。 时代周报:你在“文革”的时候跟很多画坛的老先生都有交往? 韩天衡:交往很多。因为我当时还没有“荣幸”地达到反动学术权威的档次,比较自在。那些老师们都已经被打倒了,所以经常去看看他们,为他们去做点事情。诸如帮他们料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去销毁一些所谓的罪证,帮他们去写一点认罪书、检讨报告。 他们跟我关系也非常好,叫我刻印打在他们的字画上面,所以属于忘年交。在处处存在戒心的“文革”年代,我跟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讲。黄胄第一个被打成“驴贩子”,那时候我在部队,要我揭发他,我就讲:他从来不跟我谈政治,上级说这算什么揭发?要我跟他划清界限,我说:他在北京,我在上海怎么划?他们说:黄胄有不少画送给你,你还有没刻完他的印章,全部要上交,划清界限。后来这些东西也就黄鹤一去,再也回不来了。1973年,黄胄下放,跟我说:小韩,我放在你这里的印章呢?我说:全部都上交了。后来我再刻了一些印章送他。 我给陆俨少先生刻过300多方印章,给谢稚柳、应野平、程十发、徐子鹤先生都刻过100多方,刘海粟、李可染先生各刻过20多方,黄胄、唐云、吴作人、宋文治都刻过一些。因为我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探索怎么推陈出新的问题。大概到1972、1973年的时候基本就有了点眉目,他们觉得小韩这个人很懂艺术,所以给我的书画都很精。我没有辜负他们,就算是现在商品社会,外面到处在拿那些东西去拍卖赚钱,我没有卖掉过一件。我所有东西都在,因为我感到这是我跟他们友谊的象征,感情的依托,是不能去卖掉的。我可捐掉,但不卖掉。我只卖自己的土产—篆刻字画。 时代周报:刻印是不是中年最好? 韩天衡:也不见得,有专家讲,刻印到55岁就“结壳”、定型了。到现在为止,我感到我还在变、还能变。我所熟悉的个别上海老印人很早就叫学生代刀了。这还是要看你是不是心志专一,如果是在商品社会里为了多赚钱,当然可以搞个工作室或者找学生来代代刀。但书画篆刻是艺术家的独立劳动,所以不能这样“大协作”。事实上你如果不是将赚钱看得很重的话,完全还可以继续静下心来去探索。艺术的探索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一定会有很多新的追求,一定会有很多东西让你着迷,叫你要继续探索下去。所以,它不存在有年龄的限制。而且,我们现在比古人好的条件是:古代的艺术精华包括很多古人自己都没见过的新鲜史料,现在出来很多,美不胜收,足资借鉴发挥。总之,我是恋古的革新派:传统万岁,出新是万岁加一岁。 时代周报:中年以后,你对治印又有新的思考? 韩天衡:我们现在讲艺术要推陈出新,因为文学艺术跟科学技术不一样,科学技术不讲基因的继承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必然替代、打倒现有的、陈旧的,且是摧枯拉朽无情地推翻更新。文学艺术的规律则绝然不同,是讲推陈出新,不是革命,是革新,讲四世同堂。石涛出来就把董其昌打倒?吴昌硕出来就把扬州八怪打倒?齐白石出来就把吴昌硕打倒?没有。后者并不能遮盖前者的声望和光芒。这就是两者最根本的不同。 文学艺术是必须要讲借鉴,我认为推陈出新的本质是推新出新。邓石如的风格出现,在历史上不是新的吗?但是不管谁重复他,邓石如始终闪耀着新的光芒,邓石如之后出了赵之谦,赵之谦是新的吧?但是学他的人是旧的,他自己却是新的。所以,这些历史上创新的大家,他的本质是一个“新”字。我们借鉴这些人,不是在推陈,实际上是在推新,是以推往日之新来出今日、明日之新。 现在有的年轻人,受外来思潮影响太多,对民族的优秀传统多取虚无主义和否定主义,是不足取的,有害的。我也是主张创新的人,创新的东西不仅是表象新,更是有内涵的新。艺术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今天全盘排斥传统而自以为全新的东西,很可能明天就会销声匿迹。当然那些真正的新东西、好东西,就能从流行走向经典。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