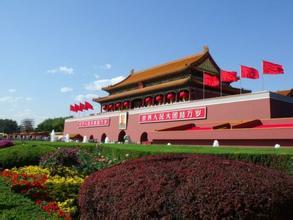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文献,不说是汗牛充栋,也可谓之丰富繁杂。今天,尽管有人还在就这个老问题发表新文章,但读者似乎已陷入“审美疲劳”,对此提不起太大兴趣。因此,当孙津以锲而不舍的精神相继推出《转型的中国》(1994)、《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1999)、《中国农民与中国现代化》(2004)、《打开视域:比较现代化研究》(2004)等四本有关现代化研究的专著后,我们不禁要问:孙津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现代化问题?他孜孜不倦研究现代化的“道理”在哪里?其现代化研究提供了那些新东西?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面评价这四本书,只想着重就最后一本《打开视域:比较现代化研究》(以下简称《视域》)发表一些看法,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自己的现代化研究的一个理论性总结。透过这本书实际上可以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我们的问题是:这本书打开了现代化研究的什么样的“视域”?
首先,我们要弄清“视域”概念。“视域”一词是孙津对近十余年来现代化研究思路的一个总体性概括。按照孙津的表述,“视域”就是指怎么看待现代化与现代化的真实含义之间的某种关系。按我的理解,视域就是某种关系的看待方式。视域不同,决定看问题的角度和范围不同。视域不同,敞开或遮蔽的问题空间也不同。孙津的视域同时向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敞开。另外,视域可以作为一种学术方法运用于各学科领域,但它本身还是比较现代化专属的形式特征。视域由此指向某种形式化过程或特征的观照。这种形式化过程或特征所涉及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谁反映谁的一般认识论关系,而是一种意义生成的本体论关系。它关注的是现代化各比较因素的互动结构。视域确定了现代化研究的最终目的:“各种形式化过程(活动、现象等等)所可能具有以及实际生成的意义”。就比较现代化而言,它具有什么性质的形式化过程或特征呢?基于孙津对现代化的界定:“世界范围穷国追赶富国的过程及状态”,(第10、125页)现代化最主要的形式化特征就是“追赶”二字。现代化的真实含义是由“追赶”二字来确证和体现的。“追赶”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比较的;不是泛泛而谈的,而是有针对性的。作者的针对性非常明确,那就是中国,或者说“中国特色”。
在世界范围的比较视野中,如何动态地(包括当下)看待中国以一个独特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追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形式化过程或特征以及由此生成的意义,这大约就是孙津力图为我们打开的“视域”。
应当说,这一“视域”的打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以往看待现代化的角度和范围,使比较现代化研究不再是单纯地为比较而比较,也不再是就中国的问题静止地谈中国。它试图摆脱现代化研究的固有模式和固定对象,彻底地从“西方中心主义”走出来。这样的视域,不同于前几年日本学者倡导的“亚洲视角”,也不同于美国学者“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柯文,1984)。“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并不只是执政党的政治教义,而是包含有中国现代化的实实在在的学理基础。《视域》一书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的反封建及社会主义选择的世界意义”的文章对此作出了独到的阐发。
关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研究,孙津在《转型的中国》和《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两书中已有所论及,前者研究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形成、性质以及它的政治结构,试图解决意识形态承诺和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后者从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看法中分析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创新意义,反驳西方人看中国现代化的致命弱点即意识形态偏见。那么,在《视域》一书中,作者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又提出哪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呢?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可能引发进一步思考,即可持续发展问题、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创新问题、农民问题。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就中国而言,和平既是发展的目的,又是发展的条件,保持一个和平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才能兑现发展这个硬道理。换句话说,兑现发展这个硬道理,中国才有可能和平地崛起。因此,发展被置于首位。在现代语境下讲发展,只能是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化说到底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发展中的人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现代化发展得以可能说到底又是一种可持续发展,一种人的可持续发展。正是在这样的问题背景下,孙津运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对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关系的探讨是相当有意义的。他对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和社会学家有关人的生存价值理论和发展观进行了清理,在自我与环境的关系、政治的生活化、生存态度的终极性、自然人与法人的区别、知识的广告化运作与隔除、文明的虚拟等众多层面,为我们提供了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般性的理论基础。
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在谈到人与自然、人与地球关系时,孙津使用了“伦理制约”的概念,他否定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作为可持续发展具有伦理制约的依据。他认为人类同地球有同一的伦理关系,人类有责任遵循这种制约。人如何运用知识直接影响到人能否达到可持续发展。当知识成为人的功能并构成人这个自组织系统的有机部分时,人这个物种就发生了质变。从自组织系统进化的非连续性和非决定性特征来讲,人类这个演变被称之为物种的“跃迁”(第71页)。“跃迁”是孙津创造的一个新概念,在他的思想框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这个概念他推导出一些结论性看法:“人自身的发展如果是可持续的,那么它必然与地球的进化同步;如果有什么跃迁发生,那么最根本的跃迁是人与地球的功能同一”(第75页)。根据这个推论,孙津并不担心“人口爆炸”,因为,人类自组织系统与地球这个自组织系统之间的互存关系,将会自动调整地球与其所承载的人口数量的比例关系。如果将这种理论贯彻到底,中国的人口数量问题对中国人的可持续发展似乎不构成实质性压力。显然这有悖于人们关于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常识。目前,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在一些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呼吁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有所松动。不过,我始终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短期内难以克服的“瓶颈”。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粮食产量世界第一,国民生产总值也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一旦人均化则马上落入后进国家的行列。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生产产值,人均国民收入以及人均受高等教育水平至今仍列入世界上比较落后的位置。巨大的人口压力,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悬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上面的“达摩克利斯剑”。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由于人口数量问题将难以解决经济总量较高与人均水平很低的矛盾和冲突。“跃迁”理论,能否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解除人口压力指出一条出路,孙津的道理是乐观的,但我个人还是心存疑虑。

实现现代化,不只是一种抽象的理念,它有一整套具体的可测量的指标体系。一般认为,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是硬性的,世界通用的,具有可参照性,可比性,比如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等。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是不宜搞“中国特色”的,但孙津却要在这个问题上创新。他认为指标只是说明现代化运动中不同发展水平的比较标准,使各种“追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不等于说达到了这些指标就是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特色”要求对中国现代化指标体系有创新的认识和设计。他把城乡统筹作为第一个重要设计因素考虑进来,以便反映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我以为这方面的考虑确实顾及到中国的现实以及中国现代化含义的真实性。他的第二个立场是防止各种西方中心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不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标参照和依据。它“既不适合中国的现实,更不能对中国特色起导引作用”(第205页)。这个问题则比较复杂。既然现代化被界定为世界范围内穷国追赶富国的过程与状态,那么,一旦加入到世界性“追赶”的游戏之中,你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或指标体系,而规则的制定一经形成就对所有游戏的参与者具有一种先在性和强制性,在世界性的现代化追赶游戏中,判定追赶过程的成绩或尺度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各种现代化的指标,否则,如果你自立一套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那就不叫“追赶”,而是单打独斗,没有进入游戏。规则不是不可以修改,但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修改规则是多国或多种利益体反复商谈或妥协的结果,如WTO;世界性的游戏也不是不可以加入新项目,但只是个别或局部,如奥运会比赛项目加入日本的跆拳道。因强调“中国特色”而重新制定一套现代化指标体系,它可能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变味”,变成缩水的现代化,尽管作者已经意识到不能“以特色为由降低指标体系的标准或水平”(第207页)。
我们指出世界性游戏规则的全球通用性,并不是要否定有关“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创新思考的意义。实际上,孙津已表明,他不是为特色而特色、为创新而创新,而是要为中国现代化找到一条尽可能合理有效、切实可行的途径。他试图弄清楚我们要建设的是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的主要特点是人口太多,而且大多数又是农民。由此产生两个基本情况,“一是资源比较起来特别贫乏,二是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特别困难”(第205页)。由这两个“特别”得出一个判断:“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中等生活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第206页)。这是孙津坚持以创新态度对待中国现代化的最基本依据。他从指导原则上为中国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创新提出包括真实、合理、有效、可比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一些在技术上极为复杂的设计,如把城乡关系列为中国现代化指标体系的一个重要项目,就充分体现作者创造性思考能力,但有些指标体系的剔除则有待斟酌,如城市化率问题。孙津认为,“一般(西方)意义上的农村城市化很可能会导致道德和社会两方面的结构失范”;“城市化率就不符合中国的发展可能,因此作为指标项目反而不真实”(第206—207页)。这里的问题是,城市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阶段,中国农村的迅速城市化是既成事实,是真实的存在,不是你主观上不把它作为指标项目它就不存在了。我们只要看一看中国市管县所带来各地城市圈的扩大,就不能不感叹中国城市“旧貌换新颜”之飞速变化。如何评价这种变化则另当别论,如农村城市化可能导致道德和社会的结构失范,那是城市化的后果之一,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指标项目的修改,更不能因此取消对城市化过程本身的测量或计算。
国外有学者宣称,21世纪全球最激动人心的两大变化或课题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管我们赞不赞同这一预言,我们都有必要在思想上、理论上乃至技术上作好充分的准备,包括有关指标体系项目的重新设计。
在孙津所有有关“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研究中,我认为农民问题是他做得最专门最深入的一个领域。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当下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共中央已经连续两年就此问题发布“一号文件”。如何从基础理论方面说明了农民问题的成因、性质、内容以及意义,孙津做出了长期的思考和研究。他清晰地回答了因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农民成了问题,由于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农民不再成为问题。在前现代农民占主体的社会中农民不成为问题,当现代化发展到农民能够自我负责时农民也不成为问题。中国农民成为问题是在新民主主义这个特定时期形成的,主要有三个原因,即中国的反封建、国内武装斗争以及农民不能由现代化而消灭自己。孙津把中国农民问题提升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问题,进而认为“中国农民与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特色”有一种二而一的关系。我非常欣赏他用中国农民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来说明“中国特色”的真实含义。这样就避免了两种偏向,一是把中国农民问题从属于中国现代化,不能从相对独立的角度分析农民问题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和作用;二是就农民问题谈农民问题,缺乏对农民问题的现代化背景的相关性研究。《视域》一书中只有两三篇是论述这个问题的(见“农民问题的真实含义”,“农民的文化裂变和农村的公民社会”等),要全面了解作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可以去读他的另一本专著《中国农民与中国现代化》,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评述。
关于农民问题,这里我只想补充一点看法,那就是除了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外,执政党或政府的有关政策直接影响农民问题的演变与解决方向。从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致的人民公社制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焕发活力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可以看到,决定中国农民问题变化的动力并不主要是来自现代化的经济因素或社会结构,而是政府的政治性政策或者说制度安排。2004年,中国农民的生产力并没有明显地超过前一年,但中央一号文件却能引领农民增收6·8%、粮食增产9%,可见政策的威力。为什么政策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动力,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解决农民问题的政策的持续正确性?没有政策的干预,中国的农民问题最终是否能够不成为问题?这些追问恐怕也是“中国特色”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中国特色”我又想到最近学界和媒体谈论很多的“北京共识”问题。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顾问雷默于去年5月发表《北京共识》一文,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他在去年底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北京共识”拓宽了视角,有助于拓宽中国国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他认为,“2004年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解决方案。这是传统发展模式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发展模式中的一些内容如重视创新、重视人力资本和重视运用‘不对称力量’等,仍然十分有效。”(见薛彦平:《“北京共识”意在客观考察——专访〈北京共识〉作者雷默》,载《参考消息》2004年12月30日,第16版)我以为,“北京共识”虽然在具体内容上与孙津论述的“中国特色”不同,但它也可以视为是“中国特色”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就拓宽视角,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过程这一点而论,孙津对“中国特色”的思考如同雷默的思考一样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而且孙津的思考更加系统而深入。
(孙津:《转型的中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中国农民与中国现代化》,中央编译出版社二00四年版;《打开视域:比较现代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0四年版。)
部分载于《北京晚报》2006年10月16日第42版
作者通讯处:430079 武汉、武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张三夕教授收。
E-mail: [email protected]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