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2日是我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颁布十周年纪念日,我为拟于那天在北京召开的“破产法十周年研讨会”准备的论文,提前于10月24日向四川联合大学300多位朋友作了介绍。 后来北京的研讨会因故不得不取消,而四川的这篇演讲则成了真正的纪念。
首先,我有一个爱好是和上帝交朋友,上帝是谁,就是在座诸位(掌声);其次,我爱站着向上帝诉说(掌声)。我想掌声表示大家接受我这个爱好,我感到荣幸!今天我要诉说的题目就是“破产法十年评价”。这十年评价,包括两个大问题:破产法立法评价、破产法实施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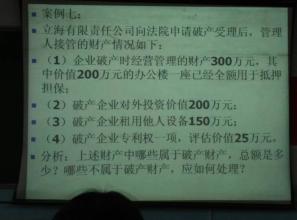
第一个问题:破产法立法评价 第一点:破产法是经济生活呼唤的产物。 经济生活呼唤破产法,谁听到过?── 我听到过! 什么时候?──1978年。那个时候,鄙人在江西景德镇当完了六年制药工人以后,在市委党校任教。当时市委召开了一个全市工交系统干部大会,我作为市委机关人员,很荣幸地坐在最后一排。市委书记声色俱厉地批评了一家机械厂:“你们太不象话了,连年亏损,亏了十年。我们市里面财政收入就那么几千万元,却让你们吃掉了一半。不能让你们老这么亏下去了,现在我宣布:限期一年整顿。如果到明年这个时候还不能扭亏为盈,那财政局就不再给补贴了!”全场鸦雀无声,财政不给补贴,那意味着亏损企业要关门,工人要失业,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家都为这个厂捏着一把汗。一年365天,一晃就过去了。第二年, 同月同日同样的全市工交系统干部大会,我同样坐在最后一排。这个厂亏损依然如故,全场鸦雀无声,市委书记皱着眉头吸烟。最后,书记掐灭了烟头,很严肃地站起来了:“机械厂太不象话了!我去年限期他们一年整顿、扭亏!到现在都没有扭转亏损局面。现在我宣布:延长一年整顿。”(大笑)当时全场就象你们这样地笑起来了,市委书记脸红到脖子了。他说:“笑什么!我说话是算数的。”结果又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因为你刚刚就不算数嘛!市委书记无地自容,我很为这位书记抱不平。他需要有一个对长期亏损,不能扭转局面的企业的最后处理办法──破产法。可是当时这位市委书记手上没有,当时景德镇没有,当时江西省没有,当时中国也没有。只有我有──在我的心中,我听见了生活的呼唤,我决定响应这种呼唤时刻准备捕捉机遇,倡导建立企业破产制度。
真是天助我也!1979年我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光远教授的研究生,来到了北京。有人问:“曹思源开什么后门从江西的山沟里到了北京呢!”我说:“对北京,除了地图上那个五角星以外,我不认识任何人。”到了北京以后,我就开始传播经济生活的呼唤──为制定破产法而奔走呼号了。
第二点:院外活动,初结硕果。
什么叫院外活动呢?“院”不是法院的“院”,而是议院的“院”。这在西方是国家立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一个很成熟的社会现象,就是议会辩论立法提案时,议会院子外面有人在活动、游说、鼓吹,以种种理由动员议员投票通过某项法律,同时也有一些人在议会院子外面游说,以某种理由动员议员投票反对某项法律。议员是选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选民当然可以给他反映意见,只是不能到院内或会场里面去游说,但可以在院外反映你的意见。此谓之:“院外活动”这是一项受到法律保护的重要的民主活动。不过中国以往没有院外活动,为什么呢?老百姓有问题要解决,习惯于找党委、找书记啊!谁找人大代表呢?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有一个“雅号”叫“橡皮图章”,不解决问题,没有用啊!中国原先没有院外活动,中国第一次院外活动从哪儿开始呢?很荣幸地,就是从我开始。所以我第二点的题目便是院外活动初结硕果。
1982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毕业后,首先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江西省委党校是我大学生活的摇蓝,景德镇市委党校是我大学毕业当了六年工人以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研究生毕业以后,又把我分到了中央党校。应该说我与党校有过一段不解之缘,但这段缘最后还是解开了,为什么呢?因为党校的宗旨明明白白──向学员灌输绝对真理。灌输二字是不打引号的,脸都不红,就是硬要往人家脑袋里灌输某种思想。在我看来,某些被称之为“绝对真理”的理论,本身已经出现了必须重新研究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研究过程需要重新铸造砖瓦,重新构建理论大厦;而现在交给我的任务却是向学员灌输现成的100%的“绝对真理”,你说这怎么能相容呢? 我心中的使命是前者,我接受的任务是后者,我感到很痛苦!(掌声)因此我就离开了中央党校。上哪儿去重新采石、重新铸造理论的砖瓦呢?我想到经济改革的政策制订中心,这样我就到了国务院。
我在国务院先后呆了三个单位,第一个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第二个是国务院办公厅,第三个是国家体改委。前后呆了6 年,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破产法的方案给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党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挨个寄去。寄了一封又一封,起先毫无反应,后来终于有了反应,1983年底,国家经委的一位同志给我打电话,他说:“曹思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胡耀邦同志对你的信有了指示!”我特别地高兴,问是怎么说的?胡耀邦同志说:“关于破产法问题,我不了解,”这是一个很诚实的,也可以说是很科学的批示,我们不可能要求党的最高领导人对每一项具体法律都很了解,并且逗号后面还有一句话:“请国家经委和国务院经济法规中心加以研究”。但是这两个单位研究研究再研究,五个多月过去,却没有下文了。
我按捺不住,便决心去找人大代表,鼓动他们提提案。那时正在开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我找了当时的一位人大代表温元凯,向他鼓吹一番如何之需要破产法,怎么用破产法,长期吃大锅饭对国家对企业对人民的危害是如何如何之深。这位人大代表被我说动了,他说“讲得好,有道理!”我说:“你既然说有道理,你应该帮忙啊。”他说:“你这个人惹不起,表扬你一句,还脱不了身了”。我说你既然是人大代表,应该运用手中权力给我帮忙啊!他问怎么帮忙,我说:“你能否在人代会上提一个提案──制订破产法!”他说:“可以,但我没有时间起草啊!你能不能帮我起草一份呢?”我说:“就在这儿”!(哄堂大笑)于是,通过人民代表的提案,我的破产法立法建议,终于列入了国家的立法议程。这便是第一次院外活动,首战告捷。
长话短说,1986年1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第99 次会议一致通过了破产法草案。然后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6月16日召开了第一次讨论破产法的会议,发言争论激烈。这儿我只讲一下发表不同意见的比例:当时有51名发言者,41人表示反对,只有10人表示赞成。怎么办?再做院外活动呗!于是我就突击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谈谈企业破产法》。出版社突击出版,在7月31 日拿到了样书,我立即给每个人大常委委员寄了一本,八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审议破产法时,每个人大常委委员手上有一本14万字的《谈谈企业破产法》,这里面有大量的调查研究材料。第二次会议讨论情况如下:反对搞破产法的从41人下降到27人,赞成搞破产法的从10名上升到27名,27:27,发言中的赞成者与反对者旗鼓相当。但是, 还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因为人大常委委员总共156人,发言者只有54人,还有100多人没发言。但是表决时,他们是要按表决器的,这100 位没有发言的人到底是反对还是赞成就不知道了。根据人大历来习惯,要100 %通过才行,这距离可就太远了。所以,第二次会议本来是要表决通过,结果没有表决,第二次会议等于没有通过。我就得继续做院外活动了。于是分别给人大常委会各位委员打电话,当时全国人大一位副委员长黄华(他原来是外交部长),在电话中说:“那你到我家里谈谈吧!”于是我就去跟他谈了半天。还有一位姓林的委员,也邀我去他家里谈谈,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同时,报纸上也发表文章,人大也组织常委委员到各个地方去进行专题视察。通过这些工作,尤其通过报刊上大量的文章,人大常委委员的认识逐步地发生了变化。在1986年12月2日,就破产法问题进行第三次讨论之后终于付诸表决。表决的情况如下:110人出席会议,101票表示赞成,9票弃权,零票反对。 破产法以绝对多数获得了通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院外活动,初结硕果”。
第三点:“无冕之王,初登宝座”。
无冕之王是谁呢?有人说是记者,有人说是舆论。不错,如果用一句通行用语,便是“新闻媒体”,它是“无冕之王”。有关破产法立法的舆论材料,1980年有一篇,1981年一篇都没有,1982年有1篇,1983年有7篇,1984年有20篇,1985年有66 篇, 1986 年有多少呢,1986年有357篇,几乎是每天一篇了, 如此密集的舆论,其影响力可谓大矣。《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企业破产制度可以先行》,登在1986年8月28日的头版第三条位置上。而头版第一条位置则是《人大开会再次审议破产法》,形成了在报纸同一版的显著位置上,一边正在开会,一边是“可以先行”论。当时就有一些人大常委很不高兴,说:“我们刚刚重新开会讨论,还未说话,还未发言呢,你《人民日报》就说可以先行,这不是分庭抗礼吗?”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追查,谁写的?谁批的?其实舆论它本来就有这个权力,拿我们的话说,舆论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你不能片面地概括为只能“上情下达”。为什么人大开会时,《人民日报》不能发表评论员文章呢?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有一次在人大讨论时,有一位常委说:“我们的法律要有阶级性,我们的法律只能保护人民。可是破产法是要让我们工人受苦,请问它保护谁?”我赶快写了一篇文章《对人民的利益是保护还是损害?》在《嘹望》杂志发表。会还没有结束,我的文章便出来了。我给他说道理啊,破产法不是侵害工人利益,它是保护工人利益,道理一二三四五……。由于这样密集的舆论导向,的确对于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思想认识及发言有所影响。这便是“无冕之王,初登宝座。”
第四点,“橡皮图章,首次钢化”。
以往的人大常委开会,通过某项法律,场面是热烈鼓掌、一致举手、全场欢呼,“通过了”!破产法可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第一次通不过,第二次又通不过,当时有人跟我说:“小曹啊!你要糟糕了!人大常委会通不过了。”我说:“我很高兴,不论通过与否,我高兴的是橡皮图章在开始变硬了!”我作为破产法的倡导者,当然希望破产法早日获得通过,但我不仅仅是一个破产法的倡导者,我同时又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者。我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这一问题,人大对一项议程能这么深入地、认真地、反复地研究,一丝不苟地进行讨论,充分独立地行使它的表决权,这是可喜的现象。我认为这对于我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破产法两次没有通过以后,又进行了反复的调查研究,在第三次会议讨论时还出现了一个插曲。第三次常委会时大多数意见认为可以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后来不知道谁向彭真委员长作了汇报,说有些人并不赞成。彭真委员长于1986年11月18日凌晨3点写了一封信给陈丕显、彭冲副委员长说:“不能颁布一个在常委审议过程中还议论纷纷、认识未能真正统一、带着许多漏洞的法下去。建议把其它的议程暂停一下,重新讨论破产法。”当时讨论告一段落,正讨论邮政法,后来便又开始讨论破产法了。这时,有一位女委员(前两次坚决反对破产法)因迟到刚来,彭冲向大家传达了彭真委员长的信然后说:“大姐,有意见可以提!”接着又有三位委员发表了不同意见,讨论来讨论去,所提出的若干问题都是大家在调查研究当中已经解决的问题,都是报刊上反复讨论过的问题,提来提去,提不出新的可以否定破产法的理由了。这对破产立法可是一个考验。这里没有任何人施力压力要“议员们”通过破产法。没有,绝对没有高压,不但没有高压,而且还有一个反弹──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形下表决通过破产法应该说是非常扎实的,人大常委会的投票是完全自主的。也可以说,在破产法的表决问题上“橡皮图章”第一次表现了它应有的“钢性”。“首次钢化”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开创性的启示作用。 这是破产法立法的四点评价,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破产法的立法过程正逢中国经济改革的高潮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阶段,破产法如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当中首先钻出樊笼的一只小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破产法的诞生过程中,有公民主动倡导立法,有院外活动,有舆论的干预(尽他们的责任来影响立法),有充分的议会辩论,有执政党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协调工作,有民主地行使表决器等等……它反映了我国在未来的政治制度现代化进程当中将要涉及而以前未曾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因此我认为,破产法的立法,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当中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一个立法上的标志,同时又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这就是我对破产法立法总的评价。第一个问题到此结束!
第二个问题:破产法的实施评价
破产法于1986年12月2日颁布,于1988年11月1日生效并开始实施。对于我国公民来说,这是一部很陌生的法律,缺乏实践经验,可是在1989年头五个月当中,全国破产案件立案就达98件,这说明经济生活需要破产法,就等着破产法,渴望它出台并发挥作用。当然,1989年6月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改革进入了低潮, 破产法因之也被束之高阁,进入了一个“冷冻期”。有人说:“曹思源,你好大胆,敢讲中国的改革自1989年6月进入了低潮。 ”(掌声)中国人一向喜欢讲高潮、高潮,又一个“高潮来临”,谁听见广播里说过“低潮来临”吗?中国人不喜欢说低潮。但是客观规律是:“两山夹一谷,两波夹一伏”啊。既然有高就有低,怎么会永远高潮呢?不敢讲低潮是怕挨板子。我说我国的改革自1989年6月进入了低潮,光胆大不行,还要有根据。根据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说,中国的经济要以调整为主──把调整放到首位,改革当然就放到末位,当然是低潮了。“低潮”时期同时又有一个“高潮”──那就是批判资本主义进入高潮,大讲“姓资姓社”的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破产法就成了资本主义改革的项目,当时有很多人写文章反对改革。但他讲“不是反对改革,仅仅是反对一种……‘资本主义改革’,而拥护‘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样的作者我没有见他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改革意见,他就是专门批判某种改革项目,并扣上“资本主义改革”的帽子,破产法的遭遇当然如此,有无根据?有!《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1日以第一版显著位置和第二、三两个整版发表了一篇长文,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那篇长文章就说,“有人建议引入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比如引入失业、破产机制等。近年似乎也局部地试验过一下,但效果并不佳。”在批判资本主义的高潮中破产法就进入冷冻时期。1990年全年的立案数只有32起。
可是时代真正需要的东西无论你怎么样地批它,怎么样地禁止,也很难奏效,何况破产法毕竟是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完成了立法程序的。你可以把它束之高阁;我需要,我则可以爬上楼梯,请它下来,捍卫我的权益。有人打官司,涉及破产法的,法院就受理。这样1991年全国破产案件又上升了,上升到117件,1992年428件,1993年 710件,1994年1625件,越过了“马鞍形”。到去年是2348件。也就是说,破产法自生效以来,到1995年总的破产立案数字是5358件。今年,上半年破产立案数1692件,超过去年上半年数字一倍,今年的7~9月份,一个季度1970件,三个季度共3662件,距以往历年总和5358件不远了。所以说第四个季度即使是持平的话,也会超过5358件。虽然今年除夕的暮钟还未敲响,但我敢断定,今年全年的破产立案数字必超过历年的总和!(后来实际统计数据是,1996年全年破产立案达6222 件──编者注)破产法立法之后实施的一个轨迹已经绘成, 对于破产法在实施中表现出现的作用。我们可以作出以下一些评价:
(一)破产法是破产还债法。破产法直接解决的问题就是“债务人还不起债”──此谓之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按照破产程序可以清算、拍卖债务人的财产,用以抵偿债务。比如说一家工厂借了2000万,剩下的财产是1000万,他既还不了债,又没有办法借新债还旧债。那么他只有一条路──依法宣告破产。把他的破产财产清算,拍卖后变成1000万现金用以抵偿2000万债务(也就是借2万还1万,借5000还2500,按1/2的比例还债), 剩下的那一部分未能清偿的债务便依法宣告豁免,实际上也就是另外一部分风险则由债权人承担。由此而引起的良性反应则是:债权人要充分地保持警惕性,提高监督能力,债务人要提高经营水平。所以说,破产法的第一个作用是破产还债法,使得10年、8年未能解决的债权债务关系得到一个合理的、合法的、 及时的了结!
(二)破产法──双向保护法。过去有些企业到银行去借钱,一般经过两部曲。第一部,厂长拍胸脯说,保证能连本带息地如期偿还你,而且到时还可以买点东西意思意思。银行当然很高兴能够连本带息地按期偿还,当然更希望能够意思意思,就把借钱给他们了。但是很遗憾,后来产品销不出,厂里货款收不回来,也没有办法归还银行。于是厂长第二部曲即第二次拍胸脯说:“人是一个,命是一条,要钱没有,要命拿去。”银行毫无办法,既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银行作为债权人,毫无保护自己的手段。而有了破产法,银行便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债务人破产──破产是要以债务人企业的死亡为代价,以企业的解体为代价,这不是开玩笑。
这就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保护了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有这样一事例:一温州商人,他欠了债,还不了。逃到广州去卖衣服,碰到了一熟人。熟人便回家告诉了债权人,债权人那边来了十个人将他抓回温州。但由于没看好。他再次逃了,又逃到武汉开了一家餐馆,过了二年平安日子,可是到第三年又碰到了一老乡,这次他可不敢怠慢,请这位老乡好好地吃了一顿。此人答应不说的,但回去照说不误,于是又来了一些人将其所赚的钱全部弄走了。所以他写信来说,我没有活路了,赚一点钱就给收走了,我都没有办法重新做人啊!你得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啊!那个债务人就相当于过去的杨白劳还不起债,债权人要他的女儿抵债。当时若有破产法该多好,杨白劳就宣告破产,免去卖女之苦。所以,破产法还是挺人道主义的,对于债权人和债务人来说,破产法是“双向保护法”。
第三点,破产法是双向鞭策法,是对债权人的一种鞭策。在我们调查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沈阳有一家大的国营公司,公司采购员说可以买到锡锭,汇了100万元的货款给人家。可是三个月后,锡锭没来,采购员说:“由于××原因来不了,但下次肯定来,锡锭很畅销的,我们还得汇100万元过去。”结果共花了200万人民币,却是一无所获。追查起来,采购员、厂长没有犯法,因为没有贪污嘛。200 万元反正是挂在企业的帐上了,人不死,债不烂!现在就不行了,债务人企业可能宣告破产。比如说剩下的财产只有债务总额的十分之一,破产后只能按十分之一的比例分得20万元,其余180 万元就不得不依法宣告豁免。债权人当然会心疼,在这种情况下,他今后做生意就必须要考虑:债务人是否有偿还能力。有人认为破产处理中未能清偿的债务依法免除偿还责任,对债权人太不公平了。但是,谁叫你当时不看清对象呢?要提前看准,一旦债务人失去偿债能力就要及时申请宣告它破产,而不要等到它只有10%资产时才申请。这对债权人是一种鞭策,同时对债务人也是一个鞭策。过去赖债有理,现在则要以企业解体为代价的。企业须充分履行债务人的责任!所以说,破产法是“双向鞭策法。”
第四点,破产法是竞争促进法。很明显,在没有破产法时,所谓优者能胜,劣者不能汰。(它是一个不倒翁)过去企业即使经营失败,也照样能够生存,有的厂长把一个企业搞垮了,还升任某局局长。现在企业有生死存亡之忧,当然就要奋斗,企业有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改进经营管理,到市场上去参加竞争,所以第四点是“竞争促进法。”
第五点,“破产法”是地雷扫除器
地雷已经埋下去了,有些工厂10年、20年都翻不了身、还不了债,已经是资不抵债没有任何利润了,事实上已经造成破产状况,但是没有宣告破产,等矛盾积压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发生爆炸。如果通过破产法这种“社会地雷扫除器”把它引爆或把它挖开来,有时也要付出一点点代价,但显然要比触雷爆炸损失要小得多。所以我说,破产法是地雷扫除器。为了保持我国的长治久安,对一些无药可救的企业实行破产法不但是应当的,而且是必要的,是刻不容缓的!企图掩盖矛盾,在地雷上面铺一些稻草,插上一些鲜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掌声)。
最后一点,破产法是“信号弹”。什么“信号弹”呢?就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信号弹”,就是“大锅饭”的丧钟敲响了的“信号弹”,因为过去的企业很简单。张春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的企业永不破产──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们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吃大锅饭,但现在有了破产法,就非常具体地、形象地、入木三分地、有切肤之痛地告诉人们:大锅饭时代已到此结束了,搞得不好饭碗是会被打破的。
说“破产法”是“信号弹”,其意义就在于:如有100 个企业破产,用不着对100个企业都去动手, 只要破那么一两家就起到了“信号弹”作用,就会促使其它一些面临破产的企业猛醒,丢掉幻想、奋发图强、改变面貌。曾有人找我辨论:“曹思源,你希望我国的企业都破产吗?那天下岂不大乱?你看看,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这么多企业都破产,那还了得?”我说,哪里要都破产呢?破产与亏损是两个不同概念,对于企业破产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如同“树上有10只鸟,猎人开枪打下了一只,请问还有几只?它们还不会腾飞求生去么?”以此为喻,恐怕是一种最好的回答了(掌声)。
【《当说则说——曹思源演讲录 连载三十》
】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