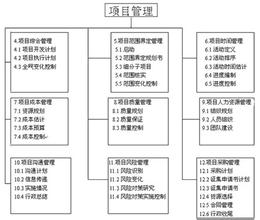——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二)
吴高兴
我国是一个具有十三亿人口、数千年中华文化积淀和近半个世纪计划经济经历的大国,国有企业改制无论在方向或路径问题上,都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过程。郑州造纸厂的改制,在路径的选择上应该说是颇为明智的,但改革者所确定的目标——“全体职工(股东)集体所有”,即由六百名职工共同持股,只能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国。“由六百名职工共同持股”与现行公司法的矛盾如何解决——应该修正的究竟是公司法还是该厂的注册方案,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这里只打算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全体职工(股东)集体所有”这一改革目标所内含的深刻矛盾。
首先是“集体所有”这一明显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改革目标与“六百名职工共同持股”这一改革方案之间的矛盾。从规范的意义上说,集体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两大基本形式之一,是与任何形式的个人产权不相容的。我在十五年前那本因经济原因而未付梓的专著《社会主义雇佣制初探》一书中指出,从抽象或本质的意义上看,公有制排斥任何个人凭借对财产的所有权获取收入,只承认劳动的收入即按劳分配收入,产权上的不可分割性或者说产权不能量化到个人,这是公有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产权一旦量化到个人则势必导致财产的收入,从而也就否定了公有制本身。郑州造纸厂的改革者一方面坚持“集体所有”这一目标制度,另一方面又提出并试图实施“六百名职工共同持股”这一方案,二者可谓南其辕而北其辙。公有制内含着产权的不可量化,而股份制又以产权的明晰即量化到个人为前提,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二律背反”。可见,“全体职工(股东)集体所有”这一目标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注定了该厂解除兼并以后第二次改制失败的命运。可以断定,如果不改变原来的思路,不管怎样该,都只能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要坚持“集体所有”这一目标制度,就不能注册成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要注册成股份公司,就必须放弃“集体所有”这一目标制度。实际上,由六百名职工共同持股的企业组织形式,除了股份公司(撇开公司法问题不谈),还有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但这些也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
其次是集体所有制与股份制企业控制权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化的现代企业,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要求通过产权民主制来保障自身的性质,亦即所有者的利益。这种产权民主制,就是建立在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这三方代理人分权与制衡基础上的企业治理结构。企业治理结构主要是通过委托-代理制度运作的,在委托人(公有产权的所有者或股东)之间如何分配企业控制权问题上,公有制企业通行的是一人一票制原则,私有制企业通行的则是一股一票制原则。实行一人一票制是为了保障产权不可量化到个人的集体或全民所有者的利益,一股一票制则是为了保障产权各不相等的股东的利益。郑州造纸厂改为创美公司以后,在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时候,实行的究竟是一人一票制原则,还是一股一票制原则?如果是一人一票制,在不同职工占有的股份不相等的情况下,一部分股东显然侵犯了另一部分股东的控制权;如果是一股一票制,又如何能够保障不可分割的集体产权?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理顺,甚至没有受到关注。
第三是公有制的产权结构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一个缺乏动力的企业注定是无效率的,因此激励问题是决定效率高低的根本问题。公有制企业固然象有的左派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可以借助于人的利他精神、事业心、荣誉感等等,通过道德教化激发参与者的动力,但公有制企业中一层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公有的范围越大,层次越多)降低了参与者的动力,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进一步分析,增强经济动力还要求财产权的适当集中,特别是向企业管理层的集中,但公有制企业的财产权恰恰是无法集中的。必须指出,这里讲的集中是经济运行的自然过程,即产权的自由流动过程,而决不是我国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倡导的以公共权力为前提、以窃取为手段的所谓“双赢的买卖”。再则,产权的集中只能通过产权的流动来实现,但公有产权的不可分性决定了它的不可流动性——就全民所有制来说,它只能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流动,而不能在全民所有制内部流动;就集体所有制来说,它只能在不同的企业之间流动,而不能在个人之间流动。而且,相比于私有产权,公有产权流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要大得多,并且容易发生公有资产流失现象。从这些方面看,公有制企业不可分割的产权结构显然是反效率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公有制产权的均等性决定的收入分配上的均等性,是有利于消费,从而也有利于生产的,而且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根深蒂固的我国,产权和分配上的均等性也便于减少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但是,无论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严密的“公地理论”,还是根据二十世纪计划经济的实践,我们都应该承认反效率是公有产权的主导方面。关于公有产权与效率的矛盾问题,由于郑州造纸厂的改制工作并未完成,而且新成立的创美公司“身份”未定,“年龄”尚小,我们还无法进行实证性的分析,但是,在实施国企改制方案以前,仔细权衡公平与效率的取舍问题,却是十分必要的。显然,郑州造纸厂在这一问题上是不够慎重的,而且改革的决策人明显有盲从民意之嫌。
那么,根据上述所做的规范性分析,我们能不能断定某一个具体的公有企业肯定是无效率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这一问题上,我赞成某些左派经济学家的说法,一个企业的效率高低问题是由各种十分复杂的因素决定的,仅仅根据一个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就“裁定”其有无效率,这是用抽象的理论分析去代替事实,从而难免失之于武断。从个案事实看,国内有河南的南街村,国外有以色列的基布兹;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公有制经济虽然有开始于二十世纪末期而至今仍然汹涌澎湃的世界性转轨,但毕竟也有前苏联仅仅二十多年就跃居与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的辉煌。所以,与“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一样,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究竟谁更有效率问题,似乎也是一个永无终止的问题。为了走出理论困境,让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分别以马克思和科斯为代表的两大经济学流派的异同点是不无裨益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证明私有制趋于消亡的必然性,而科斯等人则通过成本-收益分析阐明了私有产权(私有制)的产生及其代替公有产权(公有制)的必然性,两者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但是,两者所隐含的假设前提却惊人地一致,即都认为效率是决定经济制度的唯一因素,从而都陷入宿命论。进一步分析,在《资本论》的结构中,从简单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直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走向无效率,马克思自始至终抽掉了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习俗等等其他所有因素,而把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弊端仅仅归咎于所有制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虽然也承认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习俗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但不承认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在一国或一地对经济制度的选择过程中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根本不承认这种选择。科斯等人看问题比马克思全面得多。以科斯为创始人的新制度经济学同样强调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所谓“制度”,指的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它不仅仅指经济领域中的产权制度,还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文化习俗、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等诸多因素。问题在于,跟西方经济学的其他流派一样,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绩效的评价同样是建立在主观效用论基础上的,由于效用是主观的,不同的人对效用的大小有不同的评价,从而一个社会或集体的效率是无法评价的。问题还在于,在产权制度的起源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者同样是一元化的效率决定论者。他们虽然考察了政治制度对产权制度形成的影响,甚至认为政治规则决定着经济规则,但始终着眼于成本-效益的分析,从而无法解释何以在交易成本极大的专制制度下也可以出现市场制度。综上所述,把一个企业的效率问题仅仅归结于所有制问题是错误的,仅仅用效率问题去解释一个企业对所有制的选择也是错误的。或许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看到了这个问题,干脆把效率极大化驱逐出经济分析的范畴,而把社会公正即“一致同意”当作经济分析的核心。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一个社会或企业究竟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取决于是否经由“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的决策程序问题,而不是马克思和科斯他们所信奉的效率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郑州造纸厂改制过程中所走的民主之路,将是一条通往 “理想国”的成功之路——“全体职工(股东)集体所有”这一目标制度虽然无法实现,但是,只要坚持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经过不断探索,终究能够找到既有公正性或合法性(得到多数职工或民众的同意),又有现实可行性的目标制度。
作者通讯地址:浙江省临海市米筛巷13号201
317000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