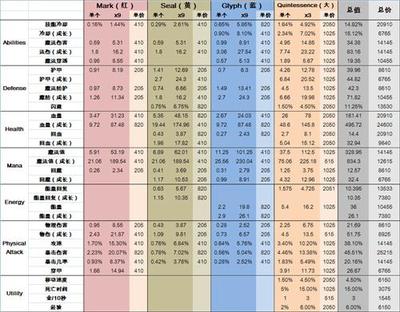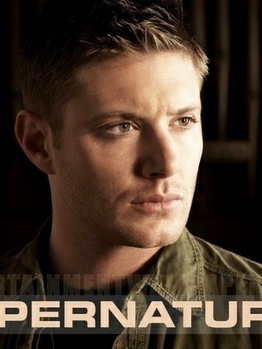8月13日 从北京到宁波
诗人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是的,学问要从现实中求。研习契约理论与企业理论,我总觉得应该去真实的世界中验证一下,再说炎炎夏日老待在这钢筋水泥充斥的北京城实在无聊,便想去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南方一带走走看看。承蒙大师兄周业安帮忙,联系了两家上市公司,一家是浙江宁波境内的农业企业,一家是江苏苏州境内的工业企业,这种地理位置和企业类型上的搭配是再好不过了。于是,2004年8月12日欣然启程。
8月13日到达杭州,兴致勃勃想先去西子湖畔一饱眼福,可谁料台风“云娜”已经登陆浙江,天气预报说西湖湖面风力达到6-7级,我只得悻然作罢。于是直接取道慈溪市——目标公司所在地。
8月14日 对企业家对话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按照和总经理约好的时间准时达到该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以果蔬加工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上市公司,依托慈溪市在农业资源方面的优势背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品主要出口东南亚国家。我和总经理的对话从一个最普通的话题开始。“你觉得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一般提供两个答案。一、我公司拥有良好的客户关系以及对行业的深刻理解,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二、我认为中国的多数企业谈不上核心竞争力,小企业没有竞争力。因为跟国际上的大公司相比,规模小,利润薄,根本谈不上竞争。”企业家的这种“坦诚”让我吃惊!
“核心竞争力”即“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对它的正式研究肇始于1990年Prahalad和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经典论文《公司核心能力》。但是管理学家们对于什么是“核心能力”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经济学家们一般不使用这个术语。经济学拒绝“核心能力”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术语定义不清,无法模型化;另一方面,我想是因为经济学认为“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胜了就有竞争力,败了就没有竞争力,试图通过一些指标来事前量度企业的“竞争力”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做法。直白地说,竞争力是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得来的,像中石化这样的垄断企业,讨论它的“核心竞争力”有何价值?总经理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识,使我感到庆幸。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中国企业家们应该对自己的处境和实力有清醒、理性的认识,靠国家力量的拼凑即便进了“世界500强”,也依然不表明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考虑到该公司是一家农业龙头公司,国家对这类企业一直十分重视,理论界也经常见到学者盛赞“公司+农户”模式的种种优越性。但我总担心,如果龙头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安排使农民旱涝保收,不担任何风险,那么谁来为龙头公司分担风险?还有,老头公司与农民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如何监督农民?如果监督是有效的,那么与“公司+农户”模式类似的早期的“合作社”就没理由会失败。总经理的回答再次让我吃惊。他认为,“公司+农户”是低效率的,我们采取的模式是“公司+农场”。因为农民文化水平低,在生产指导、监督和培训方面成本很高,而农场是一种相对有组织的生产方式,合作成本低,风险也小。谈到风险,这位总经理无奈地笑了笑,说中国农民是最可怜的群体,但有时也是最不“讲理”的群体。隐含的意思是说,分散的农民力量弱小,但是农民一旦联合起来就可能出现可怕的蛮力。我以为,经济学家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应该避免感情用事,而应该把农民、工人、企业家、官员和知识分子作为同样具有人格尊严和人权保障的群体,在此基础上考虑他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
8月17日 中国经济的希望
离开宁波之后,我匆匆赶往下一个目标公司,它位于江苏省吴江市下面的一个小镇。吴江也是一个县级市,隶属苏州市。吴江市在2004年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10位,它与前面提到的慈溪市在人口规模、幅员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差不多,地理位置也很靠近。不过我要去的公司却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从浙江杭州出发,先坐火车到湖州市,再坐汽车到南浔镇,又坐汽车穿越江浙省境线才到达公司所在的小镇。这个小镇在经济实力上可不小,它去年的GDP是23个亿,财政收入2个亿,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综合经济实力大抵相当于我老家江西的2-3个县。小镇位于太湖边上,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和“丝绸之乡”。
当晚,帮我安顿好住处后,公司的姚总设宴招待我们,在座的还有某证券公司的陈经理及其同事。姚总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经过山重水复的颠簸之后,没想到一个在行业独占鳌头的上市公司居然是在一个小镇上!陈经理说,和你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一位,他就是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罗奇当年也是颇费周折才找到这个地方,他感叹说,在这样的一个小镇上居然能诞生出一家行业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中国民营企业的力量实在是了不起!这样的民营企业,将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在座的各位对罗奇的看法都深以为然。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中国有无数个这样的民营企业,中国经济才能有今天的辉煌。民间的力量一旦释放,其势无穷也!转型时期,学者们应该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民营经济,为它们的健康发展鼓与呼。
然而,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问姚总,现在做企业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他说是企业的管理跟不上企业的发展。企业规模壮大后,如何有效管理就成为一个现实的瓶颈。企业小的时候,老板可以先拍板再论证;现在企业大了,还能这样做吗?如何做到信息畅通、上情下达?他甚至担心,民营企业一旦做大,可能就会逐步变成充满官僚主义的国有企业。我告诉他,很遗憾,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在企业理论上一直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只能逐步在实践中探索。那一刻,作为经济学人的我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惭愧”。
8月18日 太湖边的思考
经过了一整天紧凑的访谈,傍晚时分,我决定到太湖边散散心。金乌西坠,太湖洒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芒,在风的推动下层层尽染,波光粼粼。独自站在湖心的浮桥上,我希望借这股清新的江南之风吹去几天来纷乱的思绪。
这几天,我感慨最多的,是经济学对现实的严重滞后。以企业的并购问题(M & A)为例。GHM模型是企业理论中对这一问题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型理论,它以“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所带来的激励变化为主要变量,来解释两个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并购。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并购关乎多个因素,而经济学理论为了求解的方便通常只能假定少数几个变量。问题在于,少数几个变量如何尽可能地囊括多个因素中的任何一种组合?GHM模型推测被兼并一方的企业主由于丧失剩余控制权因而失去积极性,但是假如被兼并企业能够扭亏为盈,那么企业主反而会提高积极性。而且,现实中很多并购都是基于企业战略的考虑,而经济学中关于并购或者企业规模的理论几乎不考虑这点。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变量都看作是有方向的矢量,那么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就好比是在一个三维的世界中刻画一个三维以上的事物。打个比方,要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四维的东西,你说难不难?就目前而言,经济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还比较简单,要用它来指导企业管理,恐怕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理论如果要做到一般化,就必须足够精简,但这可能会导致上面所说的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如果复杂一些,就又变成“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了,缺乏一般性。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两难悖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经感叹,说一个经济学教师仍然可以用200年前斯密的《国富论》来教现在的学生,但是你能想象用200年前的数学、物理学来教今天的学生吗?必须承认,尽管经济学在200年间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但是这种进展相对于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无疑是相形见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一个解释是,为了使自己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构建一个数理化的公理体系方面,过于重视形式的完美而忽略了内容的拓展。相比之下,管理学更受企业家青睐的一个优势在于,管理学没有形式化之累,无须保持学术传统的“自洽性”,它毫不犹豫地抛弃过去的假设和理论而追逐最新的潮流。同样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则不断地向自然科学靠拢,我担心这会不会是以己之短搏人之长?如果社会科学“科学化”的过程必须如此,那么我们只能埋怨经济学应该更快进步;如果这一“科学化”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是南辕北辙。
8月20日 支持企业才能搞活经济
短暂的一周很快过去了。既然已经到了江浙,那么就干脆回趟家,江西作为“江南西道”也算是泛江南地区了。从富庶的江浙回到江西,认为江西落后的感觉就尤其强烈。一个突出的对比是,企业太少了。经济说到底是由企业干出来的。但是江西的企业为什么这么少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因:一是资本缺乏,办企业很难融资;二是苛捐杂税多,做点小生意还不够政府各个部门的“吃、拿、卡、要”;三是大凡能赚钱的项目基本上被政府和有组织势力垄断了。
要解决第一个难题,需要发展一个自由竞争的金融体系。这是Rajan和Zingales两位经济学家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基本结论。单靠国有银行的融资是不够的,没有那么多资本来支持民营经济,因此要开放民间融资渠道。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政策建议了。我的看法是,落后地区可以考虑把乡镇企业作为解决融资难题的手段之一。尽管由于在产权和治理结构上的先天劣势,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在上个世纪末的改制中已经基本上被私营企业所取代,但是它在短期内筹集创业资本、降低风险的功能却依然值得落后地区借鉴。江浙一带很多地区以前也没有一家企业,大家集资先搞一个集体企业,这就降低了融资成本和经营风险。集体企业做大后,自然就带动了一批相关企业,也培育了一批企业家、管理者和销售员。这些人各自创业后,民营经济就马上发展起来了。

要解决第二个问题,政府需要认识到“拉弗曲线”——向企业征收过多的税费只能是饮鸩止渴。要想使政府具有长远追求,官员的任期是很重要的。现在乡镇一级政府的任期由过去的三年改为五年,这是一个进步。要解决第三个问题,政府必须从上到下转变发展观。官员如果唯GDP论,以政府行为大搞招商引资,甚至鼓励官员带职下海经商,实质上是与民争利,这与行政垄断没有本质差别,都将扼杀经济活力。落后地区的官员,实在应该多到发达地区去走走看看,结合本地实际真心学习,而不是去游山玩水。
8月22日 弄巧成拙的管制
由于北京还有很多事情,因此我在江西的家里住了几天就得匆匆赶回人民大学。可是没想到火车票这么难买,提前一个星期就没票了。车站规定学生不能买站票,我只得买了无座的站票。这件事情值得玩味的有两点。
一是火车票如此紧俏,通过提高价格是否可以有效降低需求?根据经济学原理,价格越高,需求就越少。因此看上去似乎提高火车票价可以缓解交通状况。但是,提高价格能够降低需求的前提是,需求的价格弹性足够大。如果需求弹性非常小,那么即便提高价格,人们还是不会降低需求,只能通过减少其他消费来满足需求。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民工一定要在寒暑假回家,那么铁道部门提高票价就会增加学生和民工的支出成本,降低他们的总福利,而对缓解交通状况不会有什么改善。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社会中财富分布不均,假设社会上存在穷人和富人两个群体,那么提高票价的结果则是穷人受损而富人福利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因为富人可以选择坐飞机,用更高的价格享受更好的服务,而穷人因为收入条件的约束而没有其他选择。如此,则对火车票进行提价管制的结果,不是“扶贫”而是“劫贫”!
二是不允许学生买站票是否真正保护了学生的利益?今年铁道部规定,学生客流较大的车站不得向学生签售无座车票。看上去这似乎是保护了学生的乘坐有座位票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如何呢?因为火车的座位是固定供给的,当为学生预留的座位数量少于需求数量时,有部分学生买站票是必然的。如果不允许,他们就会付出双倍的代价。像我这次,如果没有这条规定,我就可以半票的价格买到站票。现在有了这条规定,我为了要及时赶回学校,反而需要放弃学生票的优惠,用全票的价格来买站票。原本旨在保护学生利益的票价管制,反而损害了学生的利益。
这件事情的基本教训是,政府部门学习经济学是多么重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1月19日(No.620)第四版,转载请注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