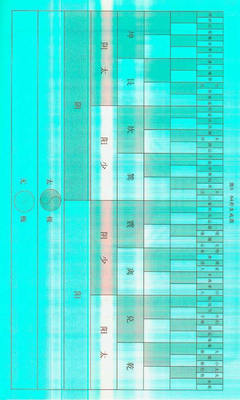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司马迁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以它丰富的内容和各具形式的手法,记载了从远古到汉武帝时约三千年的社会变革、学术文化、宗教活动、天文地理等情况,反映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活动以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还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伟大的史学著作还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观点,尤其是《货殖列传》中的“善因论”,即:“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本文就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1、“善因论”的含义
这句话是司马迁主张经济自由的集中表现。“善者因之”就是说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经济发展之自然,听任私人进行生产、贸易等活动,不加干预和抑制。“利导之”就是在顺应、听任私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前提下,由国家在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的引导,以鼓励人们从事这方面的经济活动。“教诲之”是指封建国家用教化的办法诱导人们从事某些方面的经济活动,或劝诫人们勿从事某方面的经济活动。“整齐之”是指由封建国家采取行政手段、法治手段来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和强制。“与之争”是指封建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并借以获利,这是最坏的政策。司马迁积极提倡“善者因之”而坚决反对“与之争”。“利道之”、“教诲之”和“整齐之”依次居于中间,可以视条件而使用。司马迁对上述各种经济政策的等次排列和优劣区分的标准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干预越少越好,干预越多越差。这是他吸收“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并运用于经济分析的结果。因为,无论是“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或“与之争”,都是属于一种“有为”的行为,都是从外部向内在主体施加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从而也就意味着是对人的自然人性的一种逆违,这将或多或少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欲发展经济,首先是要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欲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必须充分肯定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自然追求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司马迁认为,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各任其能”,会自然地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来从事经济活动,政府根本用不着去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
2、对司马迁“善因论”的评价
司马迁的自由经济主张与西汉经济政策的前后变化有密切的联系。汉武帝以前西汉统治者实行的是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理论依据是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汉统治者简政省刑尽量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使百姓有较安定的环境、较充裕的时间和一定的财力从事生产和经济活动。休养生息政策实行短短几十年就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历史上罕见的繁盛景象。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并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但到汉武帝时期,经济相对空前繁荣,国家富强,非遇水旱之灾“人给家足”,这时,黄老之言的“清静无为”主张与统治者力谋扩展势力和建立统一巩固的封建王朝的意图已不相适应,甚至相违背,因而,这时候是落后的,保守的;实际上这在阶级社会也是行不通的。如果现在还一定要按此办法做事,就是堵塞百姓的耳目,社会上就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了。司马迁认为,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诗》、《书》所述的虞、夏以来,人们都是在追求“声色之好”,追求功名利禄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既然是一种客观的实际情况,那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恰恰正是这些追求促进了物质的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原动力。这时司马迁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自己关于经济政策的观点:“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种观点对繁荣经济,特别是对和秦作对比时西汉初期落后的经济情况,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西汉时期落后凋弊的经济状况的。所以,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正确的。
但是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使封建经济脱离了汉初与民休养生息的自由经济道路,使封建经济走上了一种完全由超经济强制起支配作用的道路;离开了司马迁“善者因之”的道路,走上了“最下者与之争”的道路。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批评,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他对封建经济干预的一般批评。中国封建社会官营经济排斥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空间,自身又存在诸多不能克服的问题,加上封建大一统国家自身缺陷,终于使社会经济失去了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司马迁说“百姓不安其生,骚动”是这种经济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令人遗憾的是,汉武帝以后,中国封建经济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缓慢前进,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能有以上丰富敏锐的经济思想和理论阐述,实是可贵。这些经济思想和观点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