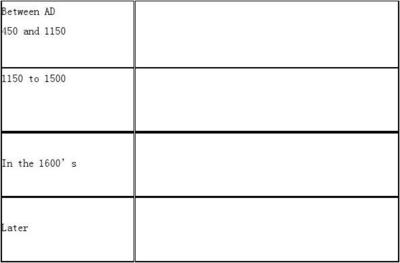成文于2001年,李曙光教授《比较破产法》课堂作业
引言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如果引进美国的企业重组制度,我国公有制企业作为债务人为什么会有动机去及时合理的提出企业重组申请,并且能够担负其企业重组的任务,尽心尽责有效完成重组?本文首先论述在美国我们为什么能够相信(至少大部分)债务人能及时善意提出重组申请,并且担负的起重组的任务,然后再以比较的方法分析中国为什么不能(按美国第11章那样做)。并且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分析各种监督机制和执行程序,而是从这些背后找出其深层次的经济、制度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设计一个可行的“经济制度”(关键是激励淘汰机制)。最后本文得出一个结论:以财产权改革为中心的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革)如果没有真正完成,也就是最终如果没有建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在宪法层次上,或de jure意义上),那么要真正发挥企业重组制度应有的作用则永远只是一种奢望,有的也只是形似而神不似。尽管我所指的企业是国有、集体企业(公有制企业),不包括其他各类私有企业,但由于前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例和影响巨大,再加上市场经济是一个链条经济是一个信用经济,一旦中间有断层,信用也就难以真正建立,而没有信用和可见的预期,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价高者得”准则就难以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将难以为继,经济也就难以良性发展,因此一旦众多的国有、集体企业行事脱离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后果可想而知。[1]
美国企业重组制度出现的原因及其经济逻辑
事实上,企业重组作为企业的一种行为,从企业诞生之日就已经存在了,这是“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使然。为了生存,企业可以自发的采用一切可用的形式和手段来战胜对手甚至市场本身,当然重组作为可能挽救企业的一种方法,企业没有理由不去采用重组。
在法律(破产法)上,企业重组制度却是一个近代甚至是现代意义上的概念。对于破产程序的目的上有关清算主义和再建主义的区分,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全球性破产法改革运动中才被正式提出来。[2]1978年,由美国总统卡特颁布的《破产改革法》,即后来所谓的《美国破产法典》,建立了全新的重组制度(破产法第11章),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成为各国破产法改革尤其是重组制度建立的典范。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没有破产法上对重组制度进行规定,企业也可以通过债务人和债权人达成重组或和议的协议,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破产法上的重组制度(程序)呢?关键就在于破产法使得债务人和债权人在法院的主持下更容易达成协议,尤其重要的是在破产法的重组程序中,一项重组计划不需要全体债权人的同意就可以发生约束全体债权人的效力。所以尽管债务人和债权人不需要破产法也可以在破产申请提出之前达成和解或重组的协议,但这种非破产法的解决方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方法)有一个致命的限制,即这种协议要求全体债权人同意。而现实中经验表明,[4]只要稍复杂的案子,这种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在有些情况下,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先对不同意这种计划的债权人做出充分的清偿来解决。
那么在美国,企业重组程序(制度)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呢?一般来说,企业重组制度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基础,其一是营运价值论,即认为企业营运中的价值远远大于企业清算的价值;其二是利益与共论,即认为法律应当使债权人成为重组企业事实上的所有人,从而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债务人的投资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与共的关系,是他们共同致力于企业的拯救;其三,社会政策论,即认为建立重组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个别债务人的“重新开始”,而且在于社会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不仅在于个别债务的及时了解,而且在于社会整体经济的健康运行。[5]我们知道,在企业的重组程序中,债务人的客观作用和努力程度可以说是重组成败的关键,债务人不仅是企业重组的最主要提出者(世界上有约90%的重组是由债务人提出的),而且也是托管人的必然或大多数的选择对象。对于前者,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可以说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没有人比债务人更了解了,因此,如果债务人不负责任从而不及时提出企业重组的申请,而等到“外部人”的发现和提出(比如债权人的强制申请)往往是已经太晚了,即企业基本已经完全丧失了重组的可能性,企业已没有复兴的希望了,那时重组往往也失去了意义。对于后者,如果作为托管人的债务人它没有能力或缺少对它的激励机制,我们往往很难期望它会努力或者会使企业正常运营下去。因为在重组程序中债务人与债权人面临的风险是不对称的,对债务人来说,除了需要它付出努力去继续经营外,重组程序并不存在风险,而相反债权人却要面对企业资产进一步减少而带来的日后清偿缩水的风险。
但是,在美国债权人甚至债务人的投资者和法院为什么会相信债务人有能力并且尽心尽责作为托管人继续经营企业呢?第一,美国国会认为债务人之所以有债务危机,绝大多数是由于市场情况和其它经济因素造成的,当然一般债务人也不存在欺诈或其他不正当行为。[6]我认为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债务人主要指其管理机构(职业经理人)是由市场筛选出来的,他们显然是有能力的。众所周知,美国存在着发达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而由于产权明确,股东(通过董事会)对经理人的任命必然是股东追求(唯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债权人和法院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认为股东不会拿自己的钱(资本)开玩笑。第二,是前文提过的信息不对称,债务人(其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处于代理人的位置,按照现代的委托——代理模型,代理人一般是处于优势信息一方,因此让原有的代理人作为管理人是明智和合理的。实践也证明由债务人继续经营的重组程序,成功率远远高有外来托管人进行经营的情况。[7]
企业重组制度在中国的经济逻辑
中国的企业是怎样的企业呢?[8]国外(西欧、美国等英语国家)对私产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即“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主人的允许,即使这间屋子已破得连风雨都阻挡不了了,但还能阻挡住权威象征的国王。这对于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的中国来讲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中国至少在20世纪40、50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前,地契等证明私产归宿的契约在老百姓心目中也是非常重要并获得极端重视的,只是到了土改后,人们才逐渐忽略了契约。[9]于是很显然我们的公有制企业是在没有自由契约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建立的唯一方式是国家的强权、命令和计划。没有从市场出发,也就谈不上衡量市场与企业的边界,或者说与西方的企业制度相比我们少了一个借鉴基础——契约自由及由此带来的所有权自由,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企业天然缺少一种激励与惩罚机制。当然我不否认借用美国或西方其他国家比较成熟的破产法或其他法律体系,对我国的改革有促进作用,至少在形式上我们可以较快的完备起来,在心理上使我们有一个满足感。但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连使我们在解决问题上走上一个良性循环也不能。
问题在哪儿呢?前文分析美国企业重组制度的经济逻辑,我们发现关键是其背后有一个市场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而我认为在中国之所以借鉴美国的企业重组制度至多只能形似而不能神似,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公有制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企业,因此天然缺少一种激励与惩罚机制。作为与“资本雇佣劳动”体制的对立,公有制企业选择了“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将一切物质资本和财务资本都归“公有”。为了彻底消除生产资料被个人占有的任何可能性,公有制的法权体系规定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而宣布个人不得拥有任何生产性资源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公有主体只能作为不可分割的产权所有者整体性地存在,而不容许把公有产权以任何形式分解为个人的产权。[10]因此,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完全不同于在个人私产基础上集合起来的合作制或股份制。按照传统的公有制政治经济学理论,个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仅仅有权拥有非生产性的生活资料。个人甚至也不准拥有其本人人力资源的法律所有权。因此,任何个人不再可能构成与他方达成生产性利用自有人力资源的合约。[11]
消除个人产权的公有制企业,合乎逻辑地实现了一切资源归公。个人不但不能充当公有企业财务资本和其他物质资本的最终委托人,而且无法凭借其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源,通过选择与公有制企业订立的市场合约、作为要素所有者进入企业合约。公有制企业已经不是科斯意义上的“企业”,因为它并不是基于一个(或一组)市场合约。公有制“企业” 当然也要使用各种投入要素,但是公有制企业利用这些要素的基础,不是要素所有者基于合约条件的让渡,而是一切资源归公以后的行政指令调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有制企业体制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其非市场合约性。[12]企业的非合约性质导致的结果就是市场意义上的激励和惩罚机制的消失——市场不能校正企业出错,这种校正显然包括企业破产清算和企业重组。
因此本文认为,实施企业重组的关键还是在于财产权的重建,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其中的关键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因为一旦国家从法律上承认了个人对自己的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那么个人就拥有了对由其劳动、创新(劳动力或人力资本在市场合约下的使用)带来的合约上的收入的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从而事实上承认了个人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合法性。这就是中国企业重组制度背后必须具备的经济逻辑,唯有此对美国等外国成熟的法律制度的借鉴才能真正做到神似。(首发于《经济学家》网站)
[1] 按李曙光教授的观点,破产法的核心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当然其出发点是中国缺乏保护债权人的传统,传统认为债主与地主、恶人等是一样的剥削者是“坏人”。李曙光:《比较破产法》讲义
[2] 王卫国:《破产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3] 同上,第34-35页。
[4]潘琪:《美国破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5] 王卫国:《破产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6页。
[6] 潘琪:《美国破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7] 同上,第194页。
[8] 本文指的企业是国有企业。因为这对分析更有针对性,虽然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着产权不明的通病,至少在宪法层次上私有财产(特别是生产性资料)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9] 周其仁,新制度经济学引论,讲义,2001。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周其仁在做农村调查时竟见到了被老百姓千方百计保留下来的地契,你想要经过炼狱般的几十年政治运动而保存下这些“凭证”是多么不容易啊,那可是要冒杀头的危险。现在我们改革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重新建立各种各样的契约,包括地契。
[10] 周其仁:《公有制企业的性质》,《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11] 产权的概念里包括交易的权利,也就是选择市场合约的权利。产权的排他性固然很重要,但是建立产权排他性主要为了交易,而不仅仅为了排他地自用和享受资源。

[12] 周其仁:《公有制企业的性质》,《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