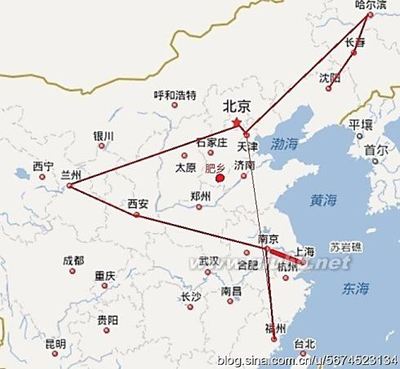【正当人们就中国的所有制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抽象的争论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实际上,在当今"社会经济"的大背景下,在股份制经济之下,国有与民有,都只不过是一线之隙而已。因为,产权已经在社会中、在股市中充分流转,在这种流转状态下,如果政府认为自己对某项产权不适合经营,不适合持有,那么它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健全的流转机制将自己所持的产权部分转移出去,转移到社会上。相反,如果政府认为自己应该、或者有必要持有某项产权,则可以在股市上展开收购,从而使产权由别人的变成自己的。对国有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且使政府的、社会上的产权充分流转,使产权流转到社会经济的最适合的位置上,流转到最适合经营它的人手上。这也是中国政府在产权改革问题上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退民进",尽管目前的产权流转大都采取这个方向,但谁也不能肯定将来不会有相反的方向。总之,抽象的所有制之争毫无意义,我们要抓住的是产权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流动性,以使其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合的方式,流动到最适合的位置上。这才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政府要保证产权流转的自由性与公正性,如果它连这一点都难做到,那它就是不称职的。而今天出现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产权流转的问题,不如说是流转过程中的公正性的问题,因此是政府是否称职的问题。政府的存在就是要向社会提供一个公正的平台,如果这个平台是存在,政府又有何作用与意义呢?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们产权流转是非常常见的事,它甚至比工人的流转更频繁。比如某公司尽管员工仍然是那些员工,但公司的所有者不知已经更换过多少次,公司产权的流转频率可能要比公司内部员工的更新频率更高,这说明什么?说明产权也是一个非常活的因素,而不是一具死的僵尸。资本市场的存在已经告诉我们这种情况。――黄焕金】
郎咸平教授的民企不如国企论是怎么推理出来的
【2004.09.30 08:22】赢周刊/陈志武
本来以为"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早已达成共识,没想到这个问题最近又成热点。我历来主张言论自由是社会良序的基础。大家有不同意见、甚至是非常情绪化表达的意见,应是很健康的一件事。
郎咸平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在所有人缺位》里讲到,国家持股现象在欧洲也非常普遍,他举例说,奥地利国家持股高达14.81%,在芬兰、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类似数量的国家持股。因此他得出结论:企业国家持股本身并不只有中国才有;既然其他国家也有,为什么中国要"国退民进"?
郎咸平忽视了在过去20多年里,世界上遍布于亚、非、欧、美各洲的120多个不同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比如说他谈到的奥地利,现在国家持股14.81%,但这并没讲出过去十几年奥地利的私有化。奥地利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吞并,二战后,德国在奥地利建设的军工厂、银行、基础设施都被奥地利没收,这些资产就成了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基础,使奥地利从此有较高的国有经济成分,1951年时其国企占产出约22%。到了1985年,奥地利的国营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一年的亏损超过了1946~1984年间所有国营企业的红利总和。从而引出争论,是否还要国有?1987年奥地利首试民营化,1993年议会通过法案正式把私有化作为主要方针,通过上市、MBO等方式套现。
实际上过去二十几年,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始,世界范围出现全面的私有化运动。首先是英国于1982年的私有化,随后1985年有意大利和马来西亚,1986年有包括日本在内的4国,1987年有两国,1988和1989分别有9个和10个国家开始私有化,到1994年最多时有13个国家开始民营化,等等。如果产权不相关,为什么过去这些年里有120多个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私有化?难道他们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说明产权无关的结论并没有历史根据,更没考虑到过去20多年全球私有化的大趋势。
国营企业在世界的普及是一个更近代的现象,其主要起因有两个:英美工业革命对世界各国如何赶超的挑战和苏联计划经济初期短暂而令人炫目的成功。在那之前,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基本都是民营。第二,世界不同的国家,其国有化都是在二战之后、1980年之前达到最高峰的。既然那次实验从整体上失败了,而且那次尝试是由于从苏联的短暂经历中得出"要想象阿炳那样作好曲,需先把眼弄瞎"这样荒诞的结论,我们为什么还非得抱着国营、国有不放?
今天讨论的"国营""民营"问题当然不是什么新问题。那么,"国营"是怎么来的?"国营"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状态,还是一种非自然的状态?我们不能忘记,当年的国有化是一场财产强行再分配的过程,而今天的"国退民进"也必然是一件艰难的财产再分配过程,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看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不管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民营"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是自古人类最自然的谋生方式,"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是再自然不过的黄金定律。而"国营"才是后来物,说得不好听一点,那才是过去100多年里"拍脑袋拍出来"的。
"国营"在中国至少可追回到十一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茶、盐、牛马交易等商业活动,使政府成为直接的创业者和经营者。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次试验只有十几年。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国营"理念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重新出台。比如,1865年由政府出资购建的"江南制造局"。但,即使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纯粹的"国营"或"官办"也是多有警惕、提防。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皇帝能够支配的资源也不过是财政收入加上盐铁等少数几个业务的垄断利润。但是在过去50年里,政府所控制的资源还包括所有的生产资料、金融储蓄资源等等。所拥有的权力是过去几千年任何皇帝所不能想象的。这当然使道德风险也达到了最大。
在我们今天讨论"国退民进"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时,我们对不公正的民营化程序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当然愤愤不满。可是,如果你再看看当年国有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你又会有何感受呢?往事确实并不如烟。关于中国的国有化经历已有不少书详细介绍,这里就不重复。
过去两年,郎咸平对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业绩比较得出结论说,民企不如国企。这似乎与与其他国家民营化后的结果不同?是不是又是中国特色呢?
其实,这里存在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第一,在香港上市的国企都已经过产权改制,像中移动、联通、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等虽然是国家控股,但它们上市后有民间和海外持股,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因此,如果想回答"产权改革是否改进国企业绩?"这样的问题,一种方法是比较这些企业在产权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业绩变化,另一种方法是比较这些经产权改革过的与那些没改过的"同类"国企在同期的业绩差别。这样做研究才能真正回答"产权改革是否应该"的问题,但郎教授并没这样做。
第二,在香港上市的国企和民企不仅属于不同的行业,而且即使属同一行业,那些国企享有各种融资特权、行业垄断权以及方方面面的政府照顾,相比之下,那些民企就没有这些特权。因此,香港上市的国企样本和民企样本没有可比性,不能由此得出任何可信的关于"产权是否有关系"的结论,更不能帮助回答"产权改革是否值得"的问题。即使拿内地上市的国企与民企作这种横向比较,其结果的可信度同样低。
为什么不能拿没有垄断权包括银行贷款权的民企与具有垄断权的国企直接作业绩比较呢?道理很简单:有了垄断权,即使产品差、效率低也没关系,反正你可多收费。你民企做得再好,也很难赶上。因此,这两类企业的业绩差并不能说明国企更有效率。奇怪的是,香港上市的垄断国企的业绩比民企只高出一丁点,而没高出更多。

其实,不管是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行业,只要那个行业既有国企或国家持股的企业又有民企,那些国家持股的企业就会是"特权"企业,那些民企的日子就没法过,这就是为什么那怕是在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期间,政府一介入哪个行业,那个行业的民间商人很快就得关门大吉。按政治学的定义,国家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是唯一可改变法律的机构、是唯一可增加各类审批权、准入权的机构,还再加上国家也垄断金融,所以国家一旦持股某企业,那家企业的特权就有了。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海外基金经理知道民企管理得像"花自己的钱最心疼",但还是愿意买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国企背景的股票。这也说明只要有"国有"股份,就不可能没有"国营"。甚至是在有了"大政府"之后,即使没有"国有"股份,也照样可以有"国营",原因是在那时候"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这就是说,只有"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除了当事人外,谁都会支持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保证国资转让过程的透明度、保证广泛的竞标权以及媒体的自由报道,以国家得到最好的价钱和尽量保证就业为目标。
(耶鲁大学金融基金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