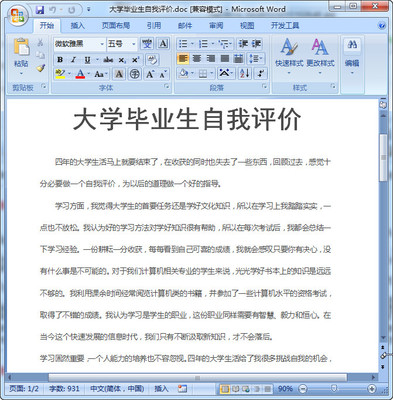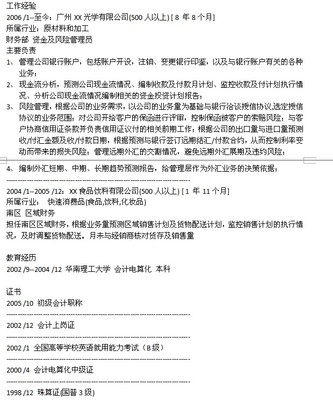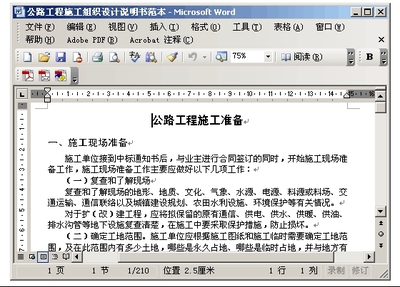OIE与NIE可以被视为两个制度研究的流派,但一种过于极端的二分法和传统对立,可能会导致人们忽略这两个学派在制度方面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和它们彼此互补以及相互借鉴融合的可能性。早期OIE学者的方法和观点存在和主流的巨大分歧,但这一分歧在后期OIE学者的研究中正在变得模糊;同样,早期NIE学者单纯强调新古典个人主义及其对制度的内生化处理,目前已经出现了向制度演化倾向的转变。这两种趋势迫使我们在比较和评价两个制度学派时必须保持必要的谨慎。正如卢瑟福在那本关于OIE和NIE比较的经典著作中指出的,“OIE和NIE可以在比通常认识到的还要大的多的范围内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可能会有重大收获,尤其当所面临的问题的相似性以及所存在的互补领域成为讨论的焦点时。”[1]
卢瑟福在分析结论中指出,关于OIE和NIE的差别及其分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主要问题上[2]:
(1)形式化理论建构与非形式化方法,包括历史方法和文学描述方法各自的作用。
(2)强调个人行为产生社会制度,还是强调社会制度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和影响。
(3)理性主义解释与对理性主义概念适用性加以限制的制度解释哪个更好?
(4)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或是看不见手的过程,是理性审慎设计的结果,亦或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5)规范性判断的基础及政府干预经济的适当边界。
就既有文献阅读的一个直观评价是,OIE和NIE分别站在了以上问题的对立面,但如果更为仔细的考察文献,我们会发现OIE和NIE在以上问题上的分歧和共识实质上是纠缠在一起的。首先,尽管OIE内部更为普遍地拒绝形式主义分析方法,而NIE内部目前在演化倾向方面的研究者也开始采用非形式化的方法,但近期OIE学者在方法论上的形式化转变以及NIE内部动态建模分析的进展说明,早期OIE和NIE的分析传统正在经历一种“颤变和转化”。其次,尽管OIE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整体主义”的代名词,但制度演化中关于个人行为决策的选择、模仿效应以及个人知识的形成及其扩散效应的分析并非绝对的整体主义。相反,早期NIE轻视制度对个人偏好和决策影响的陋习,随着诺斯等人对动态制度分析的推进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这种趋势说明,制度分析中介于有机整体主义和朴素个人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分析范式正在形成,而这一新的范式有可能是二者的折中。第三,在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的问题上,OIE十分怀疑理性的可靠性。尽管他们否定将理性最大化的逐案最优原则作为制度动力学的唯一原因,但他们并不因此彻底否定有限理性在制度型构过程中的作用。与NIE对理性的崇拜和迷恋相反,OIE学者更加注重对理性以外的其他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的考察。NIE内部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在理性方面的一种转变,部分学者也开始放弃有限理性条件下逐案协调的决策方法,并开始承认规则遵循行为在理性之外有其他原因。最后,在制度变迁的自发演化与理性设计问题上,OIE和NIE内部的奥地利学派都非常强调制度变迁的自生自发性,但NIE内部的新古典派学者则对此持有一种十分暧昧的观点,他们尽管从理性最大化这一唯一的制度动因上做了让步,但仍然对理性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存有幻想而不肯放弃“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他们也通常非常强调政府在产权制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反对产权这类基础制度的自发演化观。
通过对OIE和NIE的简要对比,以及对这两个制度分析学派所面临困境的反思,我更加倾向于认为OIE和NIE分析范式在未来将会走向一定程度的综合。而这种综合正是本文试图探索的“基于认知理论和主体相关性”的制度演化分析。当然从本人对制度分析的演化立场来看,这一判断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但也不乏事实依据。这些依据一方面来自上文中涉及的OIE和NIE内部研究的转向。而另一些依据来源于生物学关于人脑进化、系统演化以及物理学领域热力学的突破性成果。作为制度分析范式的知识背景和科学条件,我将在第二章最后一节对此做专门的介绍。
总体而言,如果我们将新古典的均衡观和奥地利传统的演化观作为两种基本的制度观来看,那么目前研究中两种方法在制度分析中的应用已经揭示了一种既定的趋向,或者说隐含了一种范式转换的潜流。这一潜流的逐步形成和两种制度分析方法所面临的尴尬是直接相关的:第一种尴尬是关于制度均衡和制度演化分歧的两难。第二种尴尬是关于基于自然选择的自发生成论和基于理性的制度设计论的分歧。
首先,对于新古典的均衡制度分析方法而言,它严格的依赖于牛顿经典力学提供的动力学解释。然而,所谓“均衡”的概念在牛顿力学中是个典型的内生静态或内生比较静态描述。牛顿力学对均衡的描述是:特定结构内部两种或多种作用力相互“对销”时(如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状态),结构就进入一种均衡态,但这一均衡结论的描述,也将均衡发生偏离的动力学因素推到了“结构外部力量”的扰动。如果不存在这种外部扰动力量,那么偏离均衡就不存在一个牛顿力学范围内的动力学解释。均衡概念引入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均衡总是被用来描述各种静态或者比较静态的制度最优状态(效用、利润、产出最大等)。这一分析既严格依赖主体理性完备这一假设,同时也受制于牛顿经典力学的约束。这一范式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新古典框架内部,既定的制度总是多方博弈的一个均衡解。但这一描述的造成的悖论是它无法包容制度变迁的事实。因为在处于均衡态的条件下,博弈主体已经采取了最优策略(在演化博弈中则是演化稳定策略,即ESS),只要博弈对手不改变策略,就没有人具有偏离均衡策略的主动性和动力学因素。有人已经指出,博弈论不可能充分考察制度变迁。因为它需要三个不变假定:即参与人不变,基本规则不变以及目标和环境不变。模型中任何形式化的处理以及所有的博弈解,都依赖于这三个基本假定。因此,与重复博弈模型研究者所声称的相反,这些模型不可能解释所有的制度变迁,也即他们只是解释了“历史变迁中在时间序列上带有线性特征的变迁”这一类小概率事件,而忽视了更多非线性和发散的制度变迁过程(相关的论点参见:米罗斯基1981、1986 P252-256;以及费尔德1979、1984年的研究)。此外,研究内生化制度的严格意义上的新古典方法,通常倾向于将制度和制度变迁看作技术约束、人口密度以及其他外生给定条件发生变化时的个人最优选择的博弈结果。亚大山·费尔德(1981:184)曾指责新古典的这一制度方法为“通过另外三个变量(禀赋、技术、偏好),来解释四类传统外生变量中剩下的一类(制度)。”由此,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均衡的分析陷入的尴尬就是,不得不将制度变迁归入一种不可知的外部力量。但这种单纯依赖理性,却又被理性所困扰的解释,显然无法令人信服。
相反,对于奥地利学派的演化制度观而言,他们仍然存在的一种矛盾就是:在否定了“理性设计制度的可能性”之后,又无法回避现实中“制度变迁存在理性参与”这一客观事实。这种尴尬导致哈耶克在继承门格尔和米塞斯的制度思路后,进一步走向了知识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但他的探索也只是延伸到“个体间‘知识分立’的特殊存在形态,以及群体认知偏离理性的误差更大”这一高度就没有更有力的突破。换言之,哈耶克通过揭示个体知识分立存在这种状态,分析了群体行动理性的自负和谬误,但是他无法解释制度变迁中理性参与的存在现实和重要作用。尽管他在百般困惑中指出了,进一步的制度研究需要更为有力的关于知识的理论作为支撑。但他却没有为此找到一个有力的解释。
[1] 参见: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01页。
[2] 同上,第209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