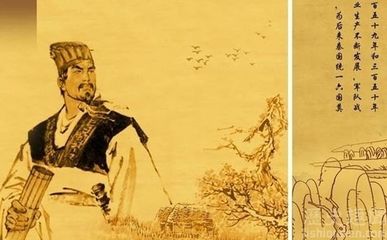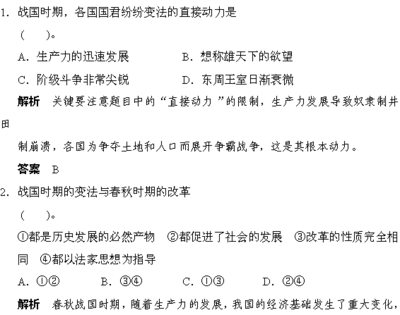正当进取多有不足秦商具有这么多优秀的历史沉淀,为什么近代以来却归于沉寂?其中当然有许多外在的客观原因,例如西方资本主义的打压、清末陕西战乱频仍、海洋运输的发达等等。究其内因,除了封建商帮的保守性之外,也与秦商正直传统的两面性有关。正直的另一面就是迂腐,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历史的拐点面前错失良机,正当进取多有不足。秦商曾经雄撼四野,在抓住历史机遇方面也有过骄人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发展;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秦商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过这里所谓的抓住历史机遇都是在条件相对成熟之后的顺势而为,那时候的社会生活节奏相对平稳,秦商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酝酿和准备。当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时,所谓的抓住历史机遇就并非可以等闲视之了,秦商还像过去那样稳扎稳打,就暴露出自己的“软肋”。在历史拐点出现时依循正统观念,缺少在商言商的正当诉求。正统观念往往是与官吏的权势联系在一起的,是当时的权贵把持的主流价值观。秦商痛恨贪得无厌的官吏,但为了获得必要的信息或者庇护,又不得不与官吏们打交道,有的则趋炎附势,甘为附庸。明朝文人执政,主流尚文而不举实,秦商有人在取得一定成功之后便成为风流文人,游离于戴发修行与文人之间,有人则喜欢结交佛门僧人,商人角色模糊。当历史处于变革的关口时,他们往往摆脱不了这些“正统”观念的束缚,反应迟钝,有的还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视为自己的仇敌。三原县商人孙豹人,当李自成的起义部队逼近三原时,还认为那是流寇进犯,不惜代价组织武装反抗,导致自己的实力受挫。其实,商人应当在商言商,否则角色的转移就是商人角色的终止。我们虽然不能要求秦商能够像政治家那样,迅速站在新兴的利益集团一边,但是至少应当为他们缺少对商业利益的正当诉求,不能巩固已有的商业阵地而感到惋惜。在商机面前对经营风险有过多的顾虑,缺少正当管理的灵活性。就秦商当时的知识结构和信息掌握而言,他们并非不善于发现商机,只是在商机面前对经营风险有过多的顾虑,徘徊观望。除了思想相对保守之外,管理结构的僵化也是重要的原因,不像晋商那样有独立于财东的优秀掌柜。秦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以中小商业为主,虽然也有合资经营和股份制的经营特色,但是多以临时的“伙伴”关系存在,始终难以成“帮”。在家族内部最终也没有能够像乔致庸那样,完成从传统地主型商人向近代商业资本家的转变,不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与相关产业适应的管理模式和敢于承担风险的执行团队。即使各地的分号要启用一些能人,分号的负责人很少有处置资产的正当权力,缺少决策的灵活性。财东习惯于把剩余资本转化为土地或者房产,甚至把银子埋在地下保值,在风险面前,宁愿放弃商机。例如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信息传进安吴堡时,财东周莹的第一反应便是收缩商业战线,以保存实力。周莹也曾想与洋商打交道,但十分谨慎,浅尝辄止。对于利益格局的变化被动接受,缺少维系正当权益的创新动力。如果说秦商于明清之际在中国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的崛起,完全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必然产物,那么它实际上是“坐享其成”的,吃祖宗饭的惯性使他们在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时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资源耗竭与创新乏力形成恶性循环后,秦商便无力在已有的商业阵地中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当利益格局被重新洗牌时,秦商只好黯然退场。陕甘总督左宗棠在西北推行茶制改革,扶持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陕西的茶商在失去支撑后竟一蹶不振。这样的例子还很多:陕西布商在外国洋布洋纱的打击下被排挤出市场,清末“陕西土布行,家家倒闭,每岁百万之利益为外人夺去”。而经营兰州水烟的陕西烟商也在外国机制卷烟打击下纷纷破产,从最盛时的大小烟庄130余家锐减到十数家。不仅各地的市场份额被其他商帮取而代之,连陕西本土的各种市场也被晋商占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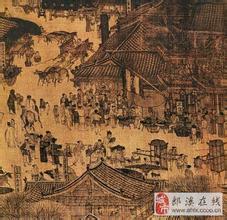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