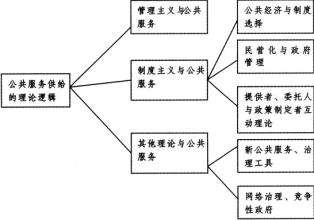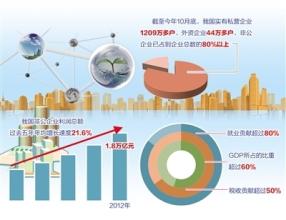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指新制度(或新的制度结构)的产生,并否定(替代)、扬弃或改变旧制度(或旧的制度结构)的过程[1]。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制度动态过程的考察,它涉及制度变迁的动力和主体问题。
任何制度,不论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一般而言,非正式制度并不是人类理性的直接对象,而是个人有限理性行为的意外社会结果,而正式制度则表现为人类集体理性的直接对象和产物,它是人类理性作用的有意识的社会结果。制度变迁的“主体”[2]一般必然的表现为,在正式制度建构过程中有意识地理性参与、并推动制度变迁或者对制度变迁有意施加影响的行动主体。因此,制度变迁的主体可以是政府、阶级、利益集团、企业或组织,也可以是自愿聚集的或紧密或松散的团体,也可以是个人。与有意识的制度变迁相反,无意识制度演化论将制度变迁的过程看作一个主体无意识参与的自发演化过程。因此,在无意识演化中,并不存在制度变迁的主体,该过程中不论个人行为怎样作用和影响制度变迁,只要他们没有在意识上指向特定的制度结果,那么他们就只是制度变迁的客体,而非主体。制度变迁的主体一旦形成,他们就会根据既有的信息和行为目标,主动积极地对制度变迁施加影响。这一有意识参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大致如下:对现有制度做出评价→形成认知和把握时机→确立制度变迁目标→选择制度变迁方式→制定变迁方案→实施变迁→调整完善目标制度→确立并巩固新的制度结构。由于制度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和结构性特征,制度变迁主体的参与同样需要特定的程序和分工。
制度变迁的动力,主要是对考察导致制度变迁的因果原理的物理学类比。如果将制度变迁的现象视为结果,那么任何导致制度变迁的因素都可以视为制度变迁的动力。黄少安(2004)主张从内外两种作用力来解释制度变迁动力的问题。他指出制度变迁的内动力是指由特定制度对应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内在矛盾作为动力源;而制度变迁的外动力则是指变迁主体从事变迁的直接动机和意图。[3]
本文根据目前制度分析中所区分的两种主要的制度变迁类型(自发演化和理性设计),来解释两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变迁动力和主体的问题。
2.4.1基于个体分散决策的自发演化型制度变迁一般而言,自发演化型的制度变迁主体并不是分散决策的个人。自发演化的过程被描述为一种由“看不见的手”所调节的机制。经济学关于制度分析所采用的生物学类比,使得社会中的个人如同自然界的其他物种一样,只是一个外部环境变化的被动受体,他们只能依赖有限理性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能动的适应。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演化理论、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演化理论,以及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的有限理性,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制度并不是个人目标函数的直接对象。相反,制度的结果和变迁过程都是个人有意识地追求自身目标时所无意导致的社会结果。因此,自发演化型制度变迁中并不存在主体,即使有主体存在,也只能视为是上帝之类的不可知力量。
与达尔文进化论解释的自然界的演化类似,一种社会制度的自发演化也不存在目的和方向。自发演化过程中的个人对制度变迁不具有主体意义。和自然界其他生物的演化一样,制度变迁表现为一种类似“自然选择”的“社会选择”的结果。自发演化型制度变迁的动力解释也类似生物学进化的动力解释。生物学关于进化动力的解释包括三个机制:(1)基于自然选择的生存竞争压力;(2)基因遗传机制;(3)遗传变异机制。与此类似,自发演化型制度变迁的动力也包括三个方面:(1)由资源稀缺引发的竞争压力。这一竞争在最原初的形式上表现为生存竞争压力,在后期随着资源丰度的相对改善逐步转化为对物质资源占有的竞争压力。(2)基因遗传和复制机制。这一机制在解释人作为物种的遗传时是有效的(例如智力遗传导致的竞争能力差异);但在解释社会组织的竞争和存续时,由于难以找到社会进化中的基因“类比物”,而显得不太令人满意。纳尔逊和温特(1982)在经济演化理论中将企业行为中的惯例视为组织遗传学的基因类比物,虽然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解释惯例行为的延续,但企业是否生物性地(准自动地)遵循惯例则是个令人怀疑的问题,此外,如果考虑熊比特关于企业组织制度创新的命题,即当企业行为不是准自动地遵循惯例,而是带有目标导向时,那么这种将惯例类比为基因的解释则显得更加无力。(3)突变或变异机制。与遗传机制相同,这一解释在应用于生命体时并不存在麻烦,但一旦进行生理之外的类比就会出现问题。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演化理论中采用了企业追求满意的假定,这一假定导致的结果是:如果企业遵循惯例带来满意结果,那么遵循惯例就会延续,而当企业遵循惯例无法带来满意结果时,那么引起对更优惯例的搜寻。显然,这里对现存惯例的“复制”是带有选择性的,但“变异”则完全是由失败引起的。纳尔逊和温特将创新视为变异的等价物,但这一类比的矛盾是:达尔文进化论中变异本身是盲目的、渐进的、偶发的,而且多数是对有机体有害的,而在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中,“变异”是被引导的和目标导向的结果。[4]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在一个扩展的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囚徒困境模型中,虽然事先假定了参与人的有限理性,但他们也无意中描述了自发演化制度变迁的第四种动力机制,即(4)适应性学习机制。在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适应性学习机制作为自发演化动力的观点,但他们将演化视为拉马克主义[5]的立场,说明他们也是承认这一机制的。正如弗罗门指出的那样,适应性学习机制是个包含它自身的选择机制。[6]在一个重复博弈的囚徒困境中,适应性学习的“变异机制”不能独立于“选择机制”发挥作用。变异只能从对旧制度的不满意结果所诱发的搜寻努力中产生。换言之,博弈参与人改变策略的变异,并不超出事先给定的策略集合,而策略改变的理由也要根据此前采用的博弈策略结果来提供。适应性学习过程中被选择的规则可以被认为是复制的,但这种复制不像自然界生物在群体层面进行那样,而是在个人层面上进行的过程。这一复制的具体形式就是社会演化中行为规则在个人之间的模仿和传递,当被模仿的行为无法通过选择检验时,适应性学习中的变异将再次发生。
概括而言,在自发演化型的制度变迁中,这一动力既外在地来自于外部环境变化对个人形成的竞争压力,也可能内在地来自于个人追求满足或最大化的动机(只要承认人的独立意识,这种内动力就无法避免)。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其实排除了外部动力的可能性),尽管没有改变制度演化的自发特征,但是他们却将特定的制度视为个人理性的自然结果。即个人在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条件下,逐案最优的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结果,也将在无意中导致制度向均衡状态收敛。而制度变迁的过程则是一种制度无法满足或实现帕雷托最优时,由个人理性所驱使的一种社会进化方向,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有完全理性的保障,自发演化的制度变迁必然会自动地恢复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但在整个“偏离→均衡→再偏离→新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所有的动力都是目标最大化这一行为动机。西蒙在有限理性前提下将行为动机由“最优”改为“满意”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古典假设的改进。但同样的问题是,如果行为主体仍然存在追求满意的动机,那么这一动机就将再一次成为有限理性条件下自发演化型制度变迁的动力源。
2.4.2基于群体决策的理性设计型的制度变迁与自发演化型制度变迁不存在明确的主体相反,基于群体决策的理性参与设计型的制度变迁则存在明确的主体。在理性设计型的制度变迁中,制度结果在最初就是主体目标函数的直接对象和行为指向。一般而言,在理性参与型的制度变迁中,制度主体很少以个人形式出现(君主专制下例外),而更多的是以特定群体(组织或机构、利益集团、阶级或阶层、各级政府)的形式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制度主体有意识参与制度变迁的程序大致如下:对现有制度做出评价→认知和把握时机→确立制度变迁目标→选择制度变迁方式→制定变迁方案→实施变迁→调整完善目标制度→确立并巩固新的制度结构。
基于群体决策的理性设计型制度变迁,是以理性的独立存在为前提的。一种较为乐观的观点认为“群体理性”是可靠和完备的。而较为悲观的观点则认为群体理性是不可靠和不完备的。需要指出的是,认为群体理性绝对可靠和绝对不可靠都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二者往往造成很大的误会。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一直被指责为极端乐观主义的代表。我将在以下的分析中指出,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中,他将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力量归结为阶级,并认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7]”,也正是阶级斗争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关于阶级斗争的根源,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8]恩格斯则指出,“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9]尽管马克思将阶级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而将阶级斗争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阶级是否就具有设计完备制度的完备理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指出阶级作为一个群体具有理想的完备理性,他只是论证了无产阶级这一群体是推动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主体力量,而实现这一制度的手段则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至于建设共产主义制度所需要的群体理性并不是事先就存在于共产主义者的大脑中的。相反,他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0]”他们还明确指出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来看,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11]显然,我们一方面澄清了马克思所背负的不必要的指责,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斯大林模式之国家主义[12]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征。因此,对完备的群体理性的指责更准确的应当是指向斯大林模式的。在该模式中,国家作为更加直接的主体可以创造和设计完美的制度,并具有完备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否了这种认识观念,它告诫人们那种具有完备理性的政府和国家是不存在的,尽管其行动的目标和本意或许是好的,但是往往一种好的意图反而可能导致很糟糕的结果。
关于群体理性的另外一个极端的看法来自群体心理学的研究。群体心理学认为个人是有限理性的,但是一旦作为群体的一员而行动时,个人就丧失了理性,而变得疯狂,群体理性在群体心理学看来是个十分可疑的概念。“群体在智力方面缺乏创造力,同时也没有历史首创精神,更不能领导艺术、科学或政治革命的潮流。这是因为当所有个体融入到群体中时,其个人才智被削弱了,对现实的敏感性也变得麻木。”[13]与群体心理学的观点相似,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曾经对群体理性的神话给予过尖锐的批评。上个世纪30年代展开的关于计划经济可行性的争论,在本质上与群体理性争论的是同一个问题。尽管当初如科尔内等同情社会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但事实证明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概率无法排除),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现实中的可行性。计划经济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说明对群体理性的过分信任和依赖是危险的,所导致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但现实留给我们的问题是,群体理性如果不是完备的,它是否就一无是处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像哈耶克这种极右的经济学家虽然曾写过《致命的自负》来抨击计划经济的谬误,并借助其知识理论警告人们集体理性是不可靠的,社会秩序是个自发演化的结果,而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社会秩序的维系必须依赖法律体系的有效运作。但法律体系建构本身似乎无法离开集体理性的参与和创设。
很明显,社会群体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其理性是有限的,但不是不必要的。尽管自发演化的非正式制度在较大程度上是个人分散决策的社会结果,但正如同新古典理论所部分正确地揭示的那样,如果没有个人的有限理性,我们仍然无法解释习俗、惯例以及文化模式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正式制度的变迁而言,它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群体理性参与的结果。我在本文中拒绝接受那种认为理性可以不依赖历史和现实创立制度的唯心主义观点,相反,我认为参与正式制度变迁的群体理性,必然是根据历史和现实所提供的制度素材和信息,进行加工而形成的有限的意识或认知,但这种认知如同哈耶克指出的那样,在个人间是以“分立的知识”存在的。群体理性的完备程度依赖于群体在个体知识交流和形成共识方面的有效程度和准确程度,而后者是群体理性参与制度变迁的重要条件。群体理性越是完备则导致的制度变迁越理想,反之则反是。从动力源上来讲,群体理性参与的制度变迁则直接表现为群体利益的导向。当然,在一个分化的社会系统中,群体利益导向将有不同群体博弈的结果所决定,特定制度往往是该社会中强势群体的利益体现。从制度变迁历史来看,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制度所维护的群体利益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大小与该制度的生命力正相关。此外,在系统分化的条件下,特定共同体内部多数成员的利益导向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和应然方向。
[1] 参:胡家勇主编,《转型经济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2] “主体”一词的使用,在哲学上,主要指称人在认识论上的内涵,即作为“意识”和“理性”的同义语。主体性的存在前提依赖于“意识认知的自我”的存在和行为的有意识和目的性特征。参:彭诚信,《主体性与私权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3] 参:胡家勇主编,《转型经济学》(该书第一章由黄少安执笔),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4] 参:杰克·J·弗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4-113,96-100,261-269页。
[5] 拉马克主张,有机体从外部环境获得的能力也可以遗传。
[6] 参:杰克·J·弗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6页。
[7] 参: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l一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39页。
[8] 参:恩格斯:《路德纸希8226;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51页。
[9] 参: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1894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10] 参: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一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5页。
[11] 参: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一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26、427页。
[12] 国家主义是勃朗科·霍尔瓦特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在分析斯大林模式时提供的一种称谓,用来揭示其非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另参:顾自安,《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霍尔瓦特社会理论述评》,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第6期。

[13] 参: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类似的观点可以参考:(1)古斯塔夫·勒邦,《革命心理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62,76-90页。(2)古斯塔夫·勒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9-20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