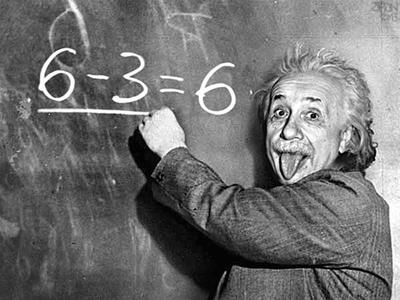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770-221年,古人以“礼坏乐崩”、“封建废而郡县行”来描述此一时期,而今人则有以“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或“从地主领主制经济向地主封建制经济转变”来解说此一时期。本文无意就此等解释框架作出评价,而只是尝试以此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以及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作为一条考察历史的线索,从制度环境或框架(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r framework)的观察角度,作些评述,希冀体现历史解释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首先,我们要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变迁或转型时期,所谓“制度转型期,是指一个社会从制度失衡到制度均衡的转变过程。“周代的典制在春秋时代已经礼崩乐坏,到战国时代则已几乎荡然无存”。“孟轲说:战国时代诸侯对周代遗制‘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下》”。(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P.10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属于“传统社会”的制度转型期,而非“现代社会”的制度转形期。在所谓“传统社会”的制度转型期中,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没有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那样大。经济因素只不过是当时社会的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古代中国“圣贤”们的脑海里,似乎不把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定位于经济发展或是物质财富的效用最大化,即不把财富的不断增长作为人们幸福的主要动机与必备条件。而文化因素在“传统社会”的制度转型期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如“舍利取义”、“杀身以成仁”的理念在“传统社会”中依然左右着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此一时期社会的变化状况,据现有史料来看,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展现似乎大大明显于经济等其它层面。至少在后人眼中即是如此,如明末的顾亭林就是这般描述的:“如春秋时犹遵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顾亭林:“周末风俗”,见《日知录集释》卷十三,P.585,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一般说来,将“封建”一词视为中国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又是一个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转型期的代名词,大概不会有太多的歧义。然而,对于“封建”一词的内涵或概念的理解,古人与今人显然有“文字障”;彼此涵义迥然有别,不可相提并论。因此,有人指出:“在中国,‘封建’的概念可以意指三个不同的对象:第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封建,如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第二是指中国从古代社会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久讼不已的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即由此而来;第三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P.29,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据王国维、顾颉刚二位前辈的考证,“封建”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诗经·商颂》的“殷武”篇中,其意当指周初的“分封建国”,目的在于“以蕃屏周”,“为周室辅”,被分封者主要是周室姬姓及其亲戚,另有功臣、故旧、先圣之后等。“史载周族灭商后,共灭国99,服国652。周族统治者在其统治势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分封同姓和异姓亲属为诸侯,共建立起71国”。(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P.3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建”乃由“封”而来,“建”字虽亦早见于金文,如“获建鼎”,但其本义与今义差异不大,即指“建国立法”;而“封”一词却有其特定涵义。“封”之本义起始于“丰”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其字形状如“植树于土堆”,而植树在此是为了划界,“封”即表示“起土界”、“疆界”或者说“田界”之意。(参见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在此,“封”字似乎已有了“界定产权”的朦胧之意;不尽如此,“制度”之意亦由此而来,“制度”几乎成了“封”字的引伸义。依许慎《说文解字·土部》所训:“封,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汉]许慎撰:《说文解字》,P.287,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版)顾颉刚先生认为,在商的后期,封建制度已很完备。(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P.329-330,中华书局,1988年版)对此,史学界颇有争议,如许倬云、董书业等均以为,“封建”一事乃周初建国之事,并非后世仍继续推广进行之常制。(参见许倬云:《西周史》,P.139-1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董书业:《春秋左传研究》,P.12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而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称,封建制度的产生便是“嫡庶制—宗法制—封建制”这样一种递进的关系;此乃周革殷命后新创之制,周初建立这种新制度的旨意就在于“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团体”。(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P.451-480,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此存而不论。如果依此思路来理解“封建”一词的涵义,那么,可以说真正的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起始于周代亦未尝不可;这是一种经过层层分封形成的层层隶属而又相对独立的“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制度。
问题在于,此一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动因何在,这与本文所欲探讨的课题有关。今人张光直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指出,夏、商、周三代文化在物质上的表现,其基本特点是一致的。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等一类的基本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三代均以农业为主要物质生产部门,以粟黍为主要作物,以猪狗牛羊为家畜;衣料所知的有麻、丝等;在建筑结构上都是茅茨土阶,以夯土为城墙与房基。中国与西方不同,其资源(文明)的最初聚集,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的。我们在中国这幅图景中所看到的,是政治文化对资源配置的首要作用。财富的积累须首先凭借政治权力的行使来实现,而政治权力在中国的成长,又为若干具有内在关联的因素所左右,它们是:亲戚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等手段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等等。(参见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有人据此推论,“在古代中国,一种‘文化—政治--经济’的作用过程似乎要胜过相反方向的作用过程。精神文化与价值体系在古代中国比在古代西方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初始的差别,无疑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同路径”。因此,“经济的发展在此对西周大举封建似乎并不起决定性的孕育和催生作用”。(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P.9,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无独有偶,台湾学者许倬云亦认为:“西周的封建自是因周室征服中国,分遣其人众一控御四方,但封建制度的建立,并不与生产工具的改变相伴随。……是以周人封建制度的本意,是为了军事与政治的目的,颇不必用经济发展的理论当作历史演化过程中必经的一环”。(许倬云:《西周史》,P.15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此论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观点颇为相左,但亦不失为一种观点;不妨一备。笔者在此无意评述,亦非参与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的争论,因为这不是本文所要解释的课题;然而,引出此论至少可表明,经济发展并非是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唯一动因,西周封建国家制度的建立多少能佐证此一论点;这对本文后面将要展开的讨论,不无裨益。即为何在解说西周解体时,有“礼坏乐崩”之谓,而非“‘利’崩乐坏”之说?“礼”与“利”虽仅一字之差,但它对解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变迁的启发性可谓大矣。
所谓“礼坏”,就是指一种以“礼”作为社会制度的解体,是一种对于制度失衡的表述;进而产生了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初始条件。从相传的“周公制礼作乐”演变到“礼坏乐崩”,乃至“后世之乱制”,正是中国古代社会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轨迹;而“礼”的社会依托则是等级制度。对于等级制度,古人有生动的写照:“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P.2048,中华书局影印,1983年版)这里,“十等俱就王公言之,为在官者”。(俞正燮:“仆臣台义”,载《癸巳论稿》,P.68,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倘若按照社会地位的等级差别来分类,这里的“十等”则可分为贵族与非贵族两大等级,贵族是统治阶层,即“君子”、“劳心者”;非贵族为被统治阶层,即“小人”、“劳力者”。然而,在这一“礼坏乐崩”的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有一个标志性的阶层变化,即“士”的阶层。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士”被列为贵族阶层之末,而经历了“礼崩乐坏”的历史演变,“士”则成了四民之首,即“士农工商”。
关于所谓士、农、工、商的“四民”之说,即“四民社会”起于何时,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此顺便交代一下。胡寄窗先生认为:“管仲的经济思想较突出的是他的有明的四民分业定居论。他主张将被统治的广大群众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阶级集团,按各集团的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士、农、工、商四大阶级集团的划分,在中国历史上是管仲第一次提出的,……在管仲的时代,这种分类不是任意的。农业公社的瓦解既产生了独立的小农阶层,也促成了自由小工商者的大量涌现;长期的兼并战争形成了武士阶层;这些新兴阶层的出现是四民划分的客观基础。……春秋时代的士的成份是很复杂的,但管仲所谓士主要是指武士。他把士列在四大社会集团之首位,这是体现了古代阶级社会政治家重视国家‘利用暴力去保护统治阶级的生活地位与统治地位,以反对被统治阶级’这一使命。武士的来源系从农民之‘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中选拔出来。管仲把士与农结合起来的这一点是有相当见地的”。(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P.62-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胡先生把“四民社会”中的“士”认定为“武士”。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的“士何事”一条里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始于《管子》(《谷梁》成公元年传亦云—原注)。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户!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万有文库本>卷七,P.51-52)依顾氏所言,“三代之时”,“民之秀者”方有可能“升之为士”,但“千百之中不得一焉”,欲形成一个“士阶层”,显然不成气候。“春秋以后,游士日多”,士阶层初具规模,毋须多疑,但是“四民杂处”依然如故,否则不会有“四民者勿使杂处”(《国语·齐语》)之言,“士”是否已置“四民之首”,亦未见说明;“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此时,“士”被列为“四民之首”概有可能。战国之际,私门养士,蔚然成风,例如齐陈成子“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韩非·外储说右上》)再如鲁国“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外储说左下》)即可佐证;更有甚者如“战国四公子”及秦之吕不韦都无不以养士为时尚,动辄“食客三千”。《管子》一书非管仲所作,成书不会早于战国时期,已成定论。《春秋谷梁传》成书更晚,其对“四民”有如此之说:“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注疏》,见《十三经注疏》,P.2417,中华书局影印)“四民”次序是士、商、农、工,今人余英时认为:“自是四民制度成立以后的见解”。而“四民社会的成立必须以士从最低层的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其前提。这一前提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的”。(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收在《士与中国文》,P.20,P.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登原则认为,士、农、工、商的确定是汉初之事。(详见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P228-229,三联书店,1958年版)因为春秋、战国之际,在人们的脑海里,重农,但并不轻工商,如“《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择财匮少”。(《史记·货殖列传》)“卫文公……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左传·闵公二年》)《国语·晋语四》载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陈氏所谓“士、农、工、商的确定是汉初之事”,这大概与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思想的演变有关。(详见吾师谈敏:《论重农抑商思想的演变》)无论“四民社会”之“士”是“文士”,还是“武士”;是“儒”或“侠”;还是“四民社会”出现于何时,亦或“四民社会”是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一种制度思想,在此不作详论;但是,“士”要成为“四民”之首,有待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士阶层的崛起,应无太多的歧义;更何况“孔门弟子三千”,“高足七十二”中,从文习武俱有。冯友兰先生亦曾指出,士、农、工、商之士为孔子以前所未有。(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见《古史辨》)第二册,P.207-208)关于孔子与士阶层的关系,下面还要讨论。
我们要说明的是,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的崛起,是当时社会制度变迁过程中一个不可低估的问题。平王东迁,周室式微,王官失受,学术下移;西周实施的学在官府制度始而瓦解,私人讲学之风盛行于世,遂有民间诸子百家之兴起。《汉书·艺文志》称先秦诸子之学,皆出于王官之说,盖渊源于此;“士既由民间上升,则上层的礼乐刑政所谓文化,也就因士为媒介而下降。文化便起了对流。不下庶人的礼乐,一部分下了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一部分也要登了上去”。“士一成为职业,自然也就成为择业的对象。有的人认此为终南捷径,便大家竞争着来做士”。(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十批判书》,P.66,P.67,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士,不少人在文化上通晓古今学术知识,逐渐形成形成一个靠知识为生,从事脑力劳动的新的士人阶层。‘士’的这一质的变化,深化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裂,发展了‘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关系”。(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P.17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此,显示了“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贵族与非贵族之别的社会等级制度开始了裂变(breakthrough)。如果说现代社会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是由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而“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T·W·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P.251,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话,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则是由于人的文化道德价值与对知识技能的需求的不断提高。所以,“学而优则仕”(孔子:《论语·子张》,杨伯峻译注,P.202,中华书局,1980年版)成了一种历史的呼唤,“学而优”的“士”成了“仕”的前提条件,士可以进仕为官,两者之间仅一步之遥。“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收在[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P.266,中华书局,1983年版)因而,一种“官”与“民”对称的“士臣民”官僚制度的社会将呼之欲出了。这也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设计制度安排方面的不同之处。
我们在此引出士阶层的沉浮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具有标志性的社会现象,无非是想透过此一社会现象来考察当时社会制度变迁的内在诱因何在,是何种因素在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意欲籍此为以后关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制度思想的展开讨论作个铺垫。
“从孔子到孟子这一个世纪之中,士阶层的发展最为惊人。一方面,士已成为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集团,另一方面此集团本身有发生了学派的分化”。(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收在《士与中国文化》,P.6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毋庸置疑,士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具特色的一个阶层,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变数和动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特征中的许多秘密都应到这一阶层中去寻觅,况且“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杨伯峻译注,P.37),“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同上,P.168),“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同上,P.80),恰似章学诚所言:“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P.40,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士”以道自任,“知书识礼”,是各种思想的承担者,“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P.1)所以,士阶层尤其值得引起我们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工作者的注意。
根据《说文解字》所训:“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汉]许慎撰:《说文解字》,P.14,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版)
清代学者段玉裁:在其所著《说文解字注》中注曰:“引申之,凡能其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P.18)许慎以“事”训“士”,段玉裁则引申为“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然而,“事其事”为何事?段注引出“《传》曰:通古今,辨然否”。汉代的刘向也称:“辨然(疑脱‘否’字),通古今之变,谓之士”。([汉]刘向:《说苑》,P.88,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由此而点出了“士”的职能与属性,“亚里斯多德早已指出,事物的本质须由其属性(attributes)见之”。(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P.4)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当时的士阶层没有特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地位,应属无产者,正如孟子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朱熹注曰:“恒,常也。产,生业也。恒产,可常生之业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尝学问,知义理,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P.211)试想,在一个等级制度的世袭社会处于“礼坏乐崩”的制度转型期中,何以在一个贵族阶层--“世卿”、“世族”中地位最低的而又“无恒产”的士阶层竟然执时代之牛耳;何以一个穷得了只有“三寸不烂之舌”的游士—苏秦,竟然“挂六国之相印”?难道此一社会现象不足以不发人深省?所谓“时势造英雄”,此言不谬也。“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似乎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似乎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P.4)这也是我们要探讨在古代社会,中西之间制度变迁的不同路径的原因之所在。
如上所述,士阶层是一个“无恒产”的无产者,他们没有大夫的那种“采邑”,亦无大夫的那种“家”、“室”,因而士对于官职的依赖性甚大。顾亭林指出:“古代之士,大抵皆有官职之人”。(顾亭林:“士何事”,见《日知鹿》上册,P.85,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孟子曾曰:“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万章》下,见《四书章句集注》,P.317)而今人顾颉刚则认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见《史林杂识初编》,P.85,中华书局,1963年版)诚如顾氏所言:“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然而,士阶层的“弃武”“从文”,“从政”活跃并崛起于政治舞台,左右时势,当归功于孔子。孔子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杨伯峻译注,P.168)“学而优则仕”等,并对“士”寄予了道德使命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杨伯峻译注,P.80)“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同上,P.163)“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同上,P.19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孔子是春秋时代从士集团崛起的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孔子的影响当然决不仅仅限于一个时代或一种身份,但我们现在还是主要从孔子为春秋时代的士开启了一条新路来观察,这条路一是士从功能上由武职决定性地转向文职;一是士从其聚集并构成群体的影响力方面,不再以家族、姓氏为标准,也不再依附某一大姓强族,而是打破家族、出身的界限,根据德行、才能构成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群体。而这两都是通过孔子‘有教无类’的招收弟子,兴办私学来实现的”。“转向文化知识和打破家族世袭,可以说是孔子为春秋时代的士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结构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P.93)亦如上面所提,冯友兰先生亦曾指出,士农工商之士为孔子以前所未有。至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士阶层崛起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留待以后讨论儒家经济制度思想时再作阐述,于兹从略。在此,我们只求表明士阶层的崛起给当时制度变迁所造成的新局面,以展示各种经济制度思想产生的社会大背景。
西周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给士阶层的崛起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相当有利的社会氛围。而造成西周社会结构性解体的原因,一般来说,不外乎有四个,即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内废公族,外务兼并,为封建制破坏、郡县制推行之两因”。(钱穆:《国史大纲》上册,P.82,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其中的文化原因,即如常人所言,孔子“有教无类”,开启私人讲学之先河,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使致学术平民化,“故平民以学术进身而预贵族之位,自儒而始盛也”。(钱穆:“孔子弟子通考”,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P77,上海书店,1992年版)若从经济上着眼,则可视为分封制的制度滞后。西周立国之初,皇亲国戚,有功之臣尚少,封土赐田之制可行;但到春秋后期,贵族人数日增,可供分封的土地相对稀缺了,乃至渐趋无土可封之势。“采邑”资源严重匮乏,终于出现了所谓“无禄”、“无邑”之公子、公孙。据《左传·昭公十年》记载:“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这在春秋早期是不可思议的。那时,“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国语·晋书四》就连大夫之家臣也有“采邑”或食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左传·成公十七年》)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一种制度的滞后而又行之无效,应该创新一种制度取而代之,否则社会无法进步。这是一条历史的准则。然而,当到了春秋晚期封土赐田之制难以为继之时,可以取而代之的又是何种制度呢?对此,董书业先生颇有见地地指出:“凡有封土即有人民,得组织武装,为独立之资。春秋以来,天子之不能制诸侯,诸后之不能制大夫,以至大夫不能制家臣,悉由于此。故封土赐民之制,实为造成割据局面之基础。及谷禄制度兴,臣下无土地人民以为抗上之资,任之即官,去之即民,在上位者任免臣下无复困难,乃有统一局面出现之可能。故谷禄制度之兴,实春秋战国间政治、经济制度上一大变迁”。(董书业:《春秋左传研究》,P.370-37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值得一提的是,分封等级制度的破坏,谷禄制度的兴起,与当时各国推行的论军功行赏制度不无关系;《左传·哀公二年》就记载了赵简子伐郑时的誓言:“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晋人杜预注“遂”为“得遂进仕”;(《春秋左传正义》,见《十三经注疏》,P.2156,中华书局印影,1980年版)然也。而秦国的商鞅变法,更将此制度推向极至。试想,当社会尚存“无禄”之公子、公孙,作为贵族最低层的士阶层欲取得“采邑”、食田,岂非异想天开。遥想当年苏秦在“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时,“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懼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第九》卷六十九,P.2262,中华书局,1959年版)后来的秦相李斯也说:“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P.2539-2540,同上)显然,“颜子居陋巷,…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死有棺无椁”(钱穆:“孔子弟子通考”,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P.62, P.77,上海书店,1992年版)如此之徒似非士子们的偶像。他们亟谋仕进以取禄食,时不我待,亦无可厚非;即便“圣贤”如孔子者,也免不了不时地发出:“沽之哉!沽之哉!”的呼唤。因有谷禄可取,士子们纷纷跃跃欲试,于是“子华使于齐,然子为其母请粟”。“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论语·雍也》)“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身为士阶层的代表人物孔子官拜为鲁大夫,或欲仕卫,亦无求封邑、禄田,只取谷禄;“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卷四十九,P.1919,中华书局,1959年版)由于谷禄制度大行其道,盛行于世,使得士阶层无后“谷”之忧,因此干脆“子张学干禄”。(《论语·为政》)并振振有词:“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孟子·滕文公》下,《四书章句集注》,P.267)于是,也就有了“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等等,诸如此类的高调了。如果说儒家先圣的言论尚着重于士阶层的自身条件的话,那么,墨家则从国家如何吸纳重用士阶层参政议政的角度着眼;“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也,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墨子·尚贤》上,见孙詒让:《墨子·閒诂》卷二, P.25-26)纵然其立论过高,期望值太大,但是,无论如何,士阶层从此有了从政的物质基础,得以驰骋于社会的上流圈子,这确是不争的史实。
正是由于士阶层的崛起,使得一个以“世卿”、“世袭”为传统的等级制度的社会大为改观,真正意义上的“礼坏乐崩”,制度失衡由此而起。士阶层所拥有的只不过是学识修养、道德文化和谋生技能,即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三国时期吴国的韦昭就称道:“士,讲学道艺者”。(《国语·齐语》,P.2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而当从习武转向从文后,“士”也就只有“礼、乐、诗、书”了。如《礼记·王制》中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正义》,见《十三经注疏》,P.1342)既“无恒产”,又无“采邑”、“强族”的依托;即没有土地等的经济资源作为后盾,也没有以往宗法制社会的“血而优则仕”特权,但是,当他们有了谷禄制度的保障机制,有了“独立之资”,成了“有恒产”的“士大夫”,便可大展拳脚地登上历史舞台,活跃于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领域了。社会发展至此也就表明了制度变迁已是势所必然,势在必行了。一个“世袭社会”将被“知识社会”所替代,“君子”与“小人”的对称将被“士”与“民”的对称所替代。以分封制为表现形式的等级--世袭制度的社会过渡到以郡县制为表现形式的官僚—谷禄制度的社会。而谷禄制度的实施机制并不依赖于土地、血统或家族等传统因素,而是凭籍士子们的所谓军功、业绩、学识、道德、名声等等。有了谷禄制度的依托,士阶层便可“学也,禄在其中矣”,因为“禄足以代其耕”。(《孟子·万章下》)了。所以,梁漱溟曾说过:“中国封建毁于士人”。(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收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P.17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我们则说,“礼坏乐崩”,“坏”于士阶层,而“崩”于谷禄制度。若就士阶层的社会属性而言,他们并不粘附于某一特定阶层,其独特性在于“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是所谓的“一张皮”;即如“近代社会学家也曾指出,由于知识阶层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它始能独特其‘思想上的信念’(intellectual convictions),这一‘思想上的信念’之说正好是孟子所谓‘恒心’的现代诠释”。(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见《士与中国文化》,P.38)他们不仅以“谋生”为基本条件,而以“谋道”为充分条件,尤其是儒家所提倡的“士志于道”,“以道自任”,“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杨注,P.168)乃至“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含有相当的超越性。类似古希腊的哲学家,俨然以“精神贵族”自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与自觉承担者,把“志于道”、“谋道”、“忧道”、“传道”视为价值取向,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四书章句集注》,P.363, P.351)以“通古今,辨然否”为自身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文化和思想的传统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如果手分封采邑制度与贵族世袭制度是二位一体的话,那么,谷禄或俸禄制度则与官僚选择制度合互为表里。顺便指出,由于士阶层这一群体在当时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春秋、战国之际几乎成了士阶层的黄金时代,“士”也就成了稀缺的“人力资源”,故有人称“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罗根泽:《诸子考索》卷二“居卫”,P.21)进而有了齐国稷下学宫,而“稷下学宫的出现不但是先秦士阶层发展的最高点,而且更是养贤之风的制度化”。(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P.57)又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云:“博士一官盖置于六国之末,而秦因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P.162)该文断定博士之制起于战国时期,是稷下学宫的延续,钱穆则认为:“博士与稷下先生异名同实”。(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P.165,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版)虽然“博士与稷下先生确有制度史上的渊源,但以政治功能而论,二者却大不相同:稷下先生‘不治’、‘不宦’,俨然与君主为师友;博士则已正式成为臣僚,不复能恃‘道’与帝王的‘势’抗礼了”。(余英时:“道统与政统之间”,见《士与中国文化》,P.110)这也是确论。我们在此所关心的是,这些新的制度安排一旦实施运行,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就随之发变化,从此,“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梁启雄:《荀子简释》,“王制篇”,P.99,中华书局,1983年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布衣卿相”之途开士阶层洞开,“政权”与“治权”开始两权分离,当然,这种分离总是若即若离,形影不离的;尽管如此,从此以后,“只有治权之民主,而无政权之民主”;“中国在以前于治道,已进至最高的自觉境界,而政道则始终无办法”。(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收在《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P.111, P.100,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清人赵翼亦早有此论:“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唯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赵翼:《二十二史札记》,P.21,中国书店,1987年版)由此可见,“世袭社会”远未彻底“解体”乃至“崩溃”,因为“政权寄托在具体个人或氏族部落上,依宗法世制维持政权于久远,遂使政权成为一‘静态的实有’(Statical being),此即一‘定常之有’(Constant being)”。(同上,P.106)虽然,有人认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天下的稳定与和平而使君王世袭,并找到一种君王世袭的平稳妥当的办法;另一方面,为了社会的效率与发展而不让官员世袭,并找到一种选拔官员的公平有效的制度,这两件事确实是战国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最大的两件事,此后两千多年的种种政治举措,也相当显示出中国人的治国智慧与政治理性”。(何怀宏:《世袭社会的解体》,P.105)然而,政权的专制集权,治权的民主放权,“此中关键惟在第一义制度之转不出,……此亦为中国历史文化症结之一”。(牟宗三:“政道与治道”,见《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P126)政权世袭,治权选贤,此乃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一大悖论(paradox)。古代中国其它所有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变迁,无不与此休戚相关;而经济制度尤其为甚,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列宁语)在中国古代社会,所有涉及经济方面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创新,几乎无不先自政治制度始;政治制度的变迁成了经济制度变迁路径向导和初始条件。由于“第一义制度”存在悖论,对制度的最优选择没有前提条件,次优选择也就理所当然了。没有最优,但求次优,这便是古代中国社会历史上制度运行的轨迹。行文至此,我们力求展示一个在古代中国社会进行制度安排或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或制度框架;而此一制度环境或制度框架又是古代社会中国与西欧的一大异处。
如果说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的崛起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大变迁的话,那么,土地制度的转化则是当日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一大变迁。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这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此又不能避而不谈,因为这涉及到这一时期制度思想的制度环境;故略作叙述。
上面提到,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夏、商、周三代文化在物质上的表现,其基本特点是一致的;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基本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三代都以农业为主要物质生产部门,正由于此因,前人往往三代并称,孔子就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杨伯峻译注,P.21-21)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亦称:“三代之时”云云。因此,三代的土地制度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区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概是天经地义的。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在西周封建制度下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安排的,何以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周室沦为诸侯国,形同虚设的“籍田”制度在宣王即位之时,已开始“不籍千亩”,因而终被废除。
周初大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并能“为周室辅”。清代学者崔述曾曰:“文王始受命,而未得及身为天子。武王始克商,而未得身见四方之靖。至成王,然后安享之,以为祖、父之德而吾独享之,于心不自安,故分其禄而与诸父兄弟共之”。(崔述:《崔东壁遗书》,P.34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崔氏在此抬高周王的道德境界,未免过誉;且王国维亦有同感。(见王著《殷周制度论》)似乎不谋而合。但是,周初封建出于政治因素的程度要大于经济因素,应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仅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推导出西周封建制度的创新,断然与史实不符。如上所述,“三代之时”经济基础条件基本一致。我们说西周的封建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封建”,似大致不谬的。然而,政治制度的“封建”引致了经济制度的“封建”,是值得我们讨论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要物质生产部门的历史条件下,土地当然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或经济资源;就其属性而言,亦是当然的财富,恰似胡寄窗先生所言:“西周时代所谓财富,与一切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一样,基本上是以财物的自然属性或使用价值为内容。如:‘问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西周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它之所以成为个人财产,则是从土地自然力的有用性质出发”。(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P.26)土地是诸侯的权威、财富、名望乃至军事实力的物质基础,“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邑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礼记·王制》)还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南五十里”(《孟子·万章》下)之说。这种自上而下的分封疆土形成了西周社会土地制度方面的等级占有制度;这是与“金字塔”式的政治制度相配套的。
然而,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土地自然力的本身并不足以构成财富,土地必须与人的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创造出财富。这一点似乎周人亦已悟出。试想,周人由西陲一个原先政治、经济和文化不甚发达的部落欲取代历史悠久和文化相对繁荣的殷商;克商之后,面对一片辽阔而又荒野的鄙地,况且“周初生产工具基本上与商代的生产工具处在同一水平”(许倬云:《西周史》,P.159,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仅对大小诸侯“列土分封”而不授民、殖民,诚然无济于事。“封土”只不过是手段,“授民”才是目的。因此之故,有学者根据大盂鼎、周公彞等金文资料的研究后,指出:至少在周初,分封制度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诸侯封建“封人”的性格强于“封土”的性格,授民比授土更重要。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分领了不同的人群。(详见许倬云:《西周史》)傅斯年亦认为,西周的封建是开国殖民,不仅意味着地域,还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杨希枚认为古代赐姓制度,实际是分封民姓、族属,与“胙土”、“命氏”合为封建三要素。其中“赐姓”是赐服属的人民,“胙土”是分配居住的地区,而归结为“命氏”,其中又包括给予国号(如“鲁”、如“宜”),告诫的文辞(如“康诰”)以及受封的象征(如各种服饰礼器)(转引自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P.11,P.12)故有所谓“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国语·鲁语》下)随着西周社会的延续发展,诸侯之后的不断繁衍,原先的土地资源又无法再生,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开始失调,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相对匮乏,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多少也说明些问题;正如董书业先生所指出的:天子建国,主要是周初的事情,其后天子的亲属越来越多,可分封的土地却越来越少,就无法再往外分封,只能封为“内诸侯”、“王室大夫”,有的甚至下降为“士”。(董书业:《春秋左传研究》,P.12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各诸侯国因为有了“封土”、“臣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日渐强盛,分封制下对周天子的向心力作用转化为离心力,纷纷对周室王权构成了威胁,都有问鼎中原之意,此时此境的周室已是尾大不掉了,王权亦是一蹶不振了。周初的土地分封制度岂有不“坏”,不“崩”之理?可谓是“势所必至”矣。

如果我们再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到“列土分封”这种土地分配制度的本身分析,其遭破坏,亦是“事出有因”的。所谓“王土”,一旦“分封”出去之后,周天子所拥有的只是在宗法制度下的土地所有权,而无实际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这种“两权分离”之后,就其经济意义而言,土地的占用权和使用权要远大于土地所有权;况且,“封土”还伴随着“授民”;土地资源与人力资源相结合,其对财富的创造力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封土赐民之制”,便是诸侯们“抗上之资”。由于土地资源难以再生,而对土地所创造的财富之欲望却不断滋长,“人有土田,女反有之”(《诗经·大雅》)“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诸侯或大夫领地世袭时间的延长,他们在领地内的政治特权日益和土地的占用权力结合起来。这种情况,在政治上增大了对王市的对抗力,形成周室王权的衰落;在经济上,滋长了私人长期占用领地的倾向”。(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P.56)此时此刻,诸侯们已不满足于仅对土地占用权和使用权的拥有,进而“问鼎”“王土”的所有权。于是乎就有了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公元前590年的“作丘赋”,公元前548年楚国的按土田定军赋,公元前538年郑国的“作丘赋”,公元前483年鲁国的“用田赋”,公元前536年郑国之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之铸刑鼎,一直到后来的郡县制等等;“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孟子·滕文公》上)“经界”一旦被“漫”,“王土”的所有权即被否定,所以,所有这举措无不都是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挑战。然后,“一切方式中最根本的变革是打破西周以来的‘田里不鬻’的传统,实现土地自由买卖”。(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P.57)对于鲁国施行的“初税亩”,郭沫若先生曾有这样的观点:“自殷、周以来的土地都是国有或王有的公田,虽然在西周末造已经有私田出现,但和国家的经济机构毫无关系,也可以说是未经合法承认的私有。因为初出现时不能影响大局,公家一直默认了它。然而时间一经久了,私田的亩积便超过公田,私门富庶了,公家便式微了下来。因而‘礼乐征伐’便逐渐‘大夫出’,更达到‘陪臣执国命’的地步。公家为挽救自己的式微,便被逼的把传统的公田制打破,而公开承认私有,对于私田一律课税。这样便是社会制度的改革”。(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十批判书》,P.49,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我们以为,虽然土地买卖在西周末已是日渐普遍的社会现象,其在制度上的实施,或土地私人所有权的在全国范围内的真正合法化,尚有待于秦统一之后。但至少可以说,到了“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国语·周语上》,P.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至此,“籍田”制度的被废,标志了西周的土地分配的等级制度的寿终正寝。
笔者行文至此,只是想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变迁的起因在于西周初期政治制度上的分封,由于这种分封制度日益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从而引致了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制度供求矛盾的加深。未知吾之词能达意否。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严重失衡,即“乱制”,从原先的“周公制礼作乐”发展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自大夫出”,进而“陪臣执国命”,终于导致了天下大乱,社会急剧动荡不安,制度需求严重不足。如何实现制度均衡,进而进行制度创新,便成了当时社会各阶人们心目中的时代课题。作为各种思想承担者的士阶层当然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是‘百家争鸣’的前奏”。(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P.26)于是,各种制度思想也就应运而生;而各种制度思想的传播、争鸣、继承、创新乃至实施的任务也就当仁不让地落在了士阶层的头上。这便是此节讨论士阶层问题的理由之所在。最后,有一点须补充的是,先秦诸子的制度思想主要在于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即如司马谈所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P.3288-3289,中华书局,1959年版))然而,政治制度若无经济制度的依托,恰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没法维系的,所以当我们讨论古代中国的制度思想时,很难将制度思想中的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截然分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