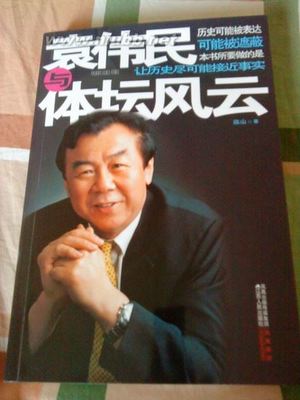走出王董(王董是中国陶瓷业巨头惠达集团的统帅)的办公间,我回到了顾问室(惠达为顾问设的临时办公间)。与这位智者交流激起的热思一时尚难平静,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创业家!
我随手抄起了一把椅子,走到面向窗口的地方,迎面一阵湿湿的凉风吹来,似乎要下雨了。我还是习惯地展开一本读了一半的书,坐了下来。多年来,我读书没有间断过,我喜欢读那些真正的思想,读我自己,书是一个框架,通过阅读我的思绪始终燃烧着。开始我是在与谁对话,这对话后来形成了一些文字。阅读其实是在共鸣,真正的大师没有造作,连孩童都可以悟明其简单的意念。不知始于何时,我开始读唐宋山水、历代书法、古诗、民间工艺、老汉饱含沧桑的脸,突然我能够感觉荣格博士的幻觉,我确信“我”应当发生于久远,并且自信将归于无极。
不再对话,我们似乎在立即或突然明白了某些东西的时候,这已超越了语言,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懂了!但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我究竟懂了什么,但我确实知道了。禅悟。
我们可以从一切现象与直观感觉的融洽中,判断和推理其他现实。这就是牛顿与伽利略的世界。但是微观或光速的世界并非如此,一个现实的存在可以立即变为无形,我们甚至无法确切地描述那是一个实体还是一个事件。这是今天科学的发现,他比禅学的顿悟更玄,但没有人敢于嘲笑他,因为暂时人类已经被科学俘获。但我还是获得了超越:我确信上帝决不会单独造化一个“道”,而为其他领域专门再造一个出来。因此从这些联觉或感悟中我已经去攫取理解领导力(组织、社会)领域的同构余味。我知道了!

那些还在质问上帝是否存在的人们,一定无法理解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佛;那些把佛当神的人们,始终会把理解停留在神与佛的差别上面;当上帝可以化为人身,当你可以容于宇宙,一切归一。宗教的争议,是表象背离真宗的滑稽。就本质而言,宗教的一切争端都与宗教无关。上帝是一种觉悟而非信仰!
看着窗外,我读自然。我经常来到佘山(这是上海这个都市,不可多得的偷闲探趣之所),坐于竹林径旁,观笋出土,悦耳鸟鸣,“李舒同你有道理”。我们与植林有大相通处。我在用心而非眼神在读,而心就是所观物,我失去了角度。
这时,一阵劲风袭进窗子,夹着毛毛丝雨,很爽。突然一枚小虫落在我的书上,我抬起手正要吹去,却被吸引住了:这是一只极小的蚊子,结构极其精致,透明,露出一条内中的肠线,质软。刚刚孵化的生命!不忍,轻轻用气推下纸页,生之。但这一低头却发现:满地的死蚊与此只相类者不计其数。研判间我发现一个惊人的现实:这些小蚊子出生之后不消几个小时就死了。直接死因:因无力补给,内中失水(蒸发)干涸而死!换句话讲,他们从未真正生存过。他们自来时那一刻,造物主就知道他们无法完成繁殖。那么我要问:那他们何以还要来呢?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关于意义。
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呢?或者:小蚊子来到世间这一短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世间的一切只要是有理由的存在,必与其他事件有关联。上帝决不会独立造一个突兀出来,我继续寻找这个联系,一个看似孤立的现象与常识的连接点。
后来,我似乎找到了理由:蚊虫排卵量大,这是上古环境的成全。而今环境已非彼时,无法保证大家都能存活,于是出现大量小蚊,破坏了均势造就了每代不多的大蚊,这种小蚊的牺牲恰成就了少量大蚊的生存,大蚊的存续将承担起繁殖延续种族的使命。
人类何尝不是如此,但我们的做法却似有伪道。人类的做法:第一是堕胎、限胎。这样做法的背后潜藏假设是:过多的生育会威胁已出生者(先来的人)的利益,这是不容许的。杀死受精卵或破坏他们的结合是为了保卫已出生者纵欲的自由。同样从上帝那里拿到出生证明的后来者被先来的人缺席投票取消了出生资格。他们永远失去了出生的机会(尽管决定他们生命的精子与卵都已存在),原因是没有机会参加投票。
人类的第二个做法:保证少数强者的存在和自由奴役多数的“小蚊”人类,那些可怜巴巴的一生没进过星级酒店、没听过音乐的、没受过教育的人类。
唯大法有逆!人类“强人”殊无自识。
人之有性,乐他而存精……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