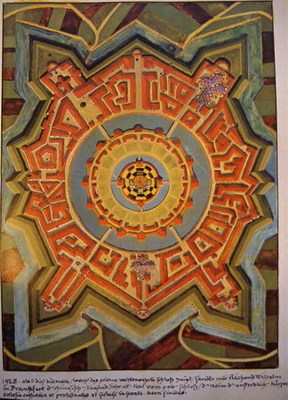沮丧与忧伤:2007中国传媒困局系列
媒体自身的异化:双重封建化与伪公共性
当采访的事件不利于被采访对象时,对方会阴阳怪气地半警告半威胁:“你新来的吧,你认识你们报社××吗?”这个××,要么是业务权威、要么就是带“总”字号的人物。总之,是能决定你还想不想混的人物。当你历尽千心万苦甚至冒着一定危险,写就一篇有深度、有读者关注度但涉及了一个大企业大部门的特稿时,即使上了版,要么是因为人家投在报纸上投了广告,是你们报社的衣食父母与上帝,要么是因为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那老板和领导的一个电话,稿子就得撤掉。主任啊总编啊还会教育你“你小子以后注意点,别惹事!”
想必以上的情况,不少新闻从业者都有类似经历。这些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人治、长官意志等封建意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极大影响,媒体抗击封建化的任务还很艰巨;另一个方面,社会实行市场经济的初期,这一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它与生俱来的弱点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媒体,不少地方,从官媒合一到商业大亨和媒体勾结,以致官商媒共谋,以私人和团体利益冒充公众利益,这就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称为的媒体封建化与再封建化。很不幸,中国传媒领域的封建参与未尚完全消除,再封建化的问题却已出现。现在面临封建化和再封建的双重封建化的威胁。在国内,有学者将媒体的双重封建化称为媒体的伪公共性。下面是几个当年中国传媒界比较典型的例子:
(1)以商业和私利集团以各种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等公关形式频频制造的“媒介事件”成为某些媒体的新闻主角,私人和团体利益俨然成了公众利益。 (2)商界朋友成了新的媒体英雄,如同自身出问题一样,一旦这样的“英雄”失势和案发,则三缄其口。 (3)部分传媒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居住在本地的外乡人为乐事,对真正的监督对象——不法权势集团——则曲意逢迎。 (4)在本地新闻表现歌舞升平的同时,并不是不知道“负面报道” 的用处,只是更经常地利用别人的“全是坏消息”报道模式从事“进口转外销”,仿佛天灾人祸只发生在异域和外地,似乎还在验证“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真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季鸾主持《大公报》时,提出报训“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办报方针,寥寥八字,掷地有声。这“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向外界传达了中共的良好形象。
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的现实情况依然是否认媒体的社会公众职能和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对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控保留了法制的盲区和人治的特区,不禁使人叹息。
马克思说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在专治统治下接受检查的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它有伪善、懦弱、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为统治者粉饰大平,或为小市民提供一些无聊的谈资,这样的报刊既扼杀民族精神,又破坏人民的教养水平。
对于,中国媒体的双重封建化已有政治学者指出,症结在于体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 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国情,但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双重封建化。一个现代国家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社会。 学者展江给出的对策是,第一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发展适应现代化的媒体理论,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第二有步骤地与国际接轨,赋予新闻自由、信息公开和新闻舆论监督以法定地位,为社会转型的有序进行充当守望者,降低转型的社会成本;在法制的规范下建立多样化的新闻体制(尤其是国有公营和社会公营体制),消灭新闻传播领域的法治盲区。第三坚持媒体的社会公共论,构筑公众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制定和恪守严格的新闻专业标准,反对媒体公司论和集团工具论,抵御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对媒体的腐蚀。
传媒生态困局总评:恶劣的传媒生态

不但记者的生存处于困局,传媒的生态环境也让人沮丧。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始终得不到相应的独立地位,只是政府的一个附属工具。有人说别看媒体老总一个个训记者编辑时凶巴巴,他们在宣传部里也像个小学生一样一声不吭的挨批。这样的体制设计下,就出现了中央媒体爆光的同时,地方党报在大篇幅的正面报道的现象。地方媒体不是忠于事实,而是必须捍卫地方党委。真实、公正、客观,也就无从谈起。记者是弱者,媒体也是社会中的弱者,它必须服从了领导,又不敢得罪利益集团,只有自己违心去做事去面对公众对自己的失望和漫骂。
真正的政治家必须明白,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是建设现代国家大厦的栋梁之一。没有这些栋梁的牢固树立,现代国家大厦就无法矗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