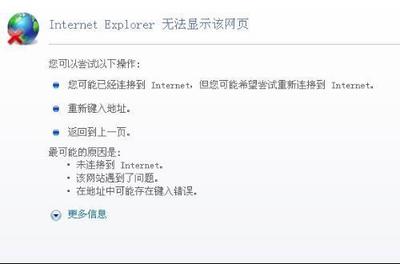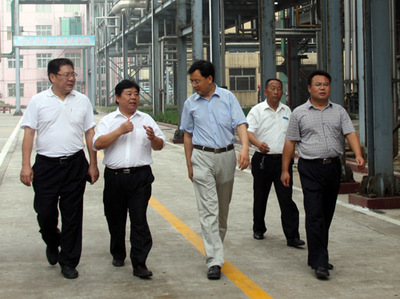张五常教授新文《口香糖的故事》很有意思,一位朋友说这篇可以和以前的《质以类聚》一起,看作是《经济解释》之续篇,我深表同意。
产权是重要的,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知道的人都去搞无产阶级革命去了。)谁也都知道好的习俗能够降低成本,等于没说,我们不能用习俗来解释问题,那是落入事实对事实的误区。重要的是产权的选择和习俗形成的关系。如果说现在产权制度是“谁大力谁得”,那么习俗就不是一个民风淳朴社会,而是一个流氓恶棍横行霸道的社会了。
这位朋友用在日本游学时候碰到“香烟头”的例子,进一步探讨了风俗、产权等问题。其观察到日本街头很干净,但是却很多烟头。
我想,如果清洁人员每天都定时打扫卫生,不管地面清洁还是肮脏,也就是说,其投入是个定数,已经安排好了多长的地段用多少人打扫,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如果地上每天都清洁如新不一定是社会最大收益。制度虽死,人的脑袋却是活的。因为每天要打扫,人员固定了,他们的工资也基本固定,清洁工人无所事事人们反而觉得是浪费。他们可能会觉得扔几个烟头不碍事,自己方便,别人也不太麻烦,是实现“约束之下的最大收益”,并且烟头打扫很容易,即所谓“扫地成本”很少。反之,如果是香口胶,清扫成本是很大的,并且对其他人负面影响也很大,所谓“外部性”是也。政府将额外增加支出,而羊毛出于羊身,这笔帐最终是摊到每个纳税人头上。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对乱扔垃圾的人予以罚款之类的惩罚。恐怕垃圾会越来越多,因为这和囚徒博弈是一样道理,个人的“乱扔垃圾”,无论他人选择如何,他们总觉得“有着数”,不管他们爱不爱卫生。
这便是乱扔垃圾的成本问题了。如果想扔垃圾时候,周围就有垃圾桶,人一般会扔到垃圾桶的,毕竟即使没有罚款,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也是种成本。所以如果我站在街道上,手里有垃圾,扔到垃圾桶还是扔到街道上,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是我有多大机会会被戴红袖章的老头抓住罚款,二是罚款的金额,三是扔到街道比放到垃圾桶中节省的体力消耗等成本。被抓概率乘上罚款金额的损失如果小于我乱扔垃圾所带来的方便,那对不起,我不是圣人,我很可能把垃圾一丢了之。当然,如果身边就有垃圾桶,随手可放进去,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里就想起另外一个类似问题,为什么越肮脏的地方,人们越不讲究卫生。如果我去到一个陌生地方,看到街道上垃圾成堆,我多半也不讲究卫生。我乱扔垃圾这个事实并非是因为其他人也不讲究卫生,这样是解释不了问题的。我在这样环境下乱丢垃圾,而是源于我的经验判断:这里丢垃圾不会罚款,或者很少有人来管。这才是我一到这样地方就不讲究卫生的真正原因。很多西方人来中国住久,也会乱丢垃圾,就是这个原因。同理,我去到一个一尘不染的地方,看到人人都遵守卫生,我恐怕也要“入乡随俗”了。“入乡随俗”真正随的不是习俗,而是经济人的本性。
我想起张教授以前那本论文集《经济解释》,其中有篇是研究中国旧家庭传统的,比如童养媳、女子裹脚等。对女子裹脚这种传统用“偏好”的话语解释就是那时候的人们对女子脚的偏好就是“小就是美”。“考虑一下裹足,许多中国作家把这种做法归结为想增加女性的妩媚与性感,换言之,裹足给男人增加效用。但为什么现在这种做法不存在了呢?通常答案是趣味已经改变。” 用便好、习俗等来应付,是经济学的无赖行为,张教授当然不会落入此套子中。教授在此文中,作出的经济学分析为:
“中国父母已拥有对子女的产权,父母要保护他们投资收益,就禁止孩子以后分家。实际上可以认为中国不断强调子女的美德,只是为了降低子女产权中成本。由于两个原因,通过婚姻娶回家,和保留顺从的儿子成本较低。”(《经济解释 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出版社)

而其新写的《经济解释》卷三《制度的选择》也对此作了回顾:
“那七二年的文章解释了盲婚是父母不容许子女选择配偶,从而较为方便地增加家庭的财富;解释了童养媳是提早收购,价格较低,购入后自小培养比较听话、服从;解释了扎脚是为了恐怕外家引进的媳妇逃走,而农业操作之外的家务、纺织等工作,扎脚为害不大。”
在导致这样的个人行为选择是由于社会制度前提:“虽然雇用劳力或租用土地的安排早已存在,但大致上生产要素是长者的私产。子女也是父母的私产,一家之主是父亲。一方面看,子女算是奴隶了。”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反复阐述的科学的方法,便是提醒人们不要走入误区,比如事实解释事实、套套逻辑等。可惜,说者有心,听者多为无意。一碰到问题,就是“三招两式”,可不是五常所言之“三招两式”,而是“传统、习惯、风俗”三招,“制度、偏好”两式。遇到问题不是说“传统所致”敷衍,便是“制度所然”搪塞了之。
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少出街了,更很少去娱乐场所。据报摘,如今犯罪率、离婚率都比以前大为减少了。难道这便可以说“民风淳朴”了么?或者说,“少去娱乐场所”是人们的偏好?“犯罪率和离婚率低”是传统,是风俗?用这些可以解释么?如果不是“非典”这两个字如此如雷贯耳,这个约束条件如此之明显,恐怕很多人又要面红耳赤地争论什么习俗、传统和偏好问题了。
而张五常教授在非典时期连写几文,“建议中国必须培养出清洁的风俗习惯”,这种“俗”和“惯”是要怎样形成的,我认为才是个重点问题。
人人都“惯”了,便是“俗”。所以“俗”的形成,必须有待个人“惯”的培养。我们不可能从亚当夏娃社会开始研究博弈。制度的演进及相关背景等是重要的,某个时候的文化背景、道德伦理由于一些约束条件,作为人们的一种因“惯”而“俗”的东西,将影响当中每个个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的预期,从而也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这样排除了风俗、传统、偏好、口味这种大而无当的东西,才是态度严肃的经济学分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