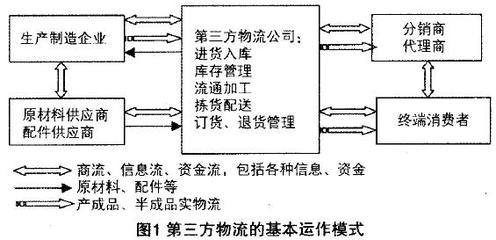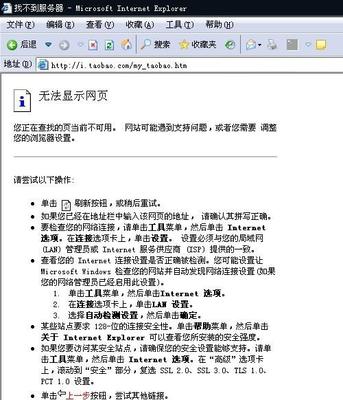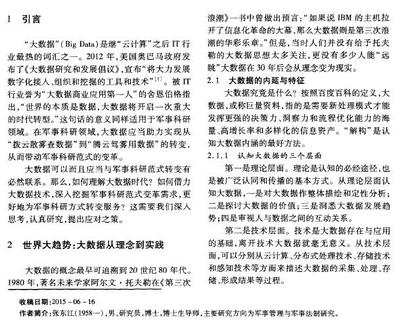笔者《“经济”一词的含义》发表后,一些朋友来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疑问,故为此文以进一步展开有关分析、阐明有关论点。
经济一词的涵义是指人的生存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是指人在获得自己的生存资料过程中的行为方式。
人赤条条来到世界上,生存的烦恼便伴随着人的一生。人生而有着各种需要;有需要并满足这些需要,规定着人之为人的一切方面。
人是杂食动物,这使人具备了广泛分布于地球各处的可能性。早期人类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有的以采集植物果实为主要生存手段,这被称为“采集经济”;有的以渔猎为主要生存手段,谓之“渔猎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形成了农业经济,从而产生了农业文明;另外一些地区则形成了游猎经济。由于狩猎方法的改善,以至于可猎获的动物愈益稀少时,早期的游猎经济就过渡到游牧经济,产生了游牧文明。以打渔和海盗为主要生存手段的民族,本质上也属于游牧文明。历史学关于“两种经济的大分工”之说,其中的“分工”一词与经济学所谈论的分工是有区别的。在后者,分工是交易的结果,而“大分工”概念仅仅揭示了生存条件和经济方式——经济种类——的比较和不同。这是需要加以区分的。
在农业经济地区,人必须依附于土地而生存——安居才能乐业。其理想状态因此为:“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而村落与村落之间,则“虽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考诸上古的实际情形:周初的农民(被称为“氓”或“野人”,但不是奴隶!)私自到处游荡是要遭查禁和下狱的。他们如果想迁徙它处,必须获得官府批准并“为之旌节而行之”,他们显然已经建立了某种原始的户籍制度。当前困扰我国的户籍制度问题,就是在传统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产生的、同时又未能很好加以解决的矛盾的产物。商品经济则与游牧经济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而个人的迁徙自由属于游牧经济的基本生存方式,在根基上就与“天赋人权”没有关系。
两种经济的区别是根本性的。首先,早期农业采用的都是木制和石制的农具,青铜器只用于武器和礼器,这种情况在铁器出现后才有根本改变。因此这一时期的农业唯有在集体的共同劳作方式下才是可能的,故此农业文明地区形成国家的历史大大早于游牧文明地区。另外,在游牧文明地区——古希腊、古罗马等,他们的“神”大都邪淫、妒嫉、自私且好勇斗狠。注意到神的行为方式就是人的生存方式的真实写照,这就是好理解的了。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哲学追求设定为“绝对的善”,他因此决定为希腊人引入在道德上合乎这种善的理想的神。“引诱年轻人不信神”,因此成为处死苏格拉底的罪名之一。
而在一切农业文明中,神都是母亲。神是慷慨给予的,善良而威严——“天地之大德曰生”;并且祭神活动还是农业生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祭司阶级因而成为最早的威权阶级。但祭祀所需技艺和战争所需技艺是截然不同的。在部族战争中,武士集团注定要崛起并成为与祭司集团相抗衡的力量。如何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成为不同农业文明不同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古巴比伦由于地处四战之地,武士集团很早就取得了与祭司集团平起平坐的地位。《汉谟拉比法典》实际上是两大集团之间的政治契约,由此也开启了西方契约政治的先声。
在谈到国家及其组织过程时,不能不提到一个有关的重要组织原则。在人类的组织行为中,存在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笔者称之为“孟德斯鸠制衡定律”(参见拙著《经济选择的秩序——一个交易经济学理论框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即:在一个稳固的社会组织中,必定存在一个制约其组织者的力量,使组织者的行为处于有效的约束之中。但祭司的统治实际存在着一个这样的风险:由于祭司有权与神直接对话并传达神的意志,祭司本人就有了被神化的巨大可能性。统治者一旦被神化,对统治者的任何约束将不复存在。
中国、埃及、印度和巴比伦文明都属于农业文明。祭司本人是否被神化以及如何防止祭司本人的神化,在这四个农业文明之中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由于地域关系,中国、埃及和印度在早期都较少受到外来入侵,祭司集团始终处于显赫地位。古埃及文明就在国王(同时也是祭司)本人被神化的过程中永久地沉沦了。
巫术过渡到宗教,这是防止统治者被神化的有效手段。早期的祭神就是一种巫术。巫术与宗教的区别在于:巫术是功利的,属于某种技艺,宗教则包含这样两个重要因素:其一,借上帝之口颁布一系列重要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可以约束一切人,包括世俗王权;其次,宗教是说理的,任何高级宗教都以某种哲学为基础。基督教神学的哲学基础是亚里斯多德哲学;印度佛教与中国周易的结合产生了“禅宗”;印度教则以印度哲学为背景。印度的种姓制度中,虽然祭司集团被规定为最高贵的种姓,但他们却受到了两方面的制约:宗教教教规的制约和武士集团的制约。
中国在夏商两代,至少在殷代,作为天下共主的王就已经或接近于神化了。据考证,殷人“帝”与“祖”是同格的,即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同一,并且“帝”与“王”也是人神同格的,也即,“帝”生前为王,而死后为神(参阅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这样的王因而不能不是残忍而暴虐的。殷纣王的残暴为周人的“革命”准备了条件。周人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在周公旦的主持下进行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革命——周公治礼。周礼的核心是对“人主”(包括王和各方国的领主)的行为制定一个规范和约束。总原则是:人主的行为必须符合并顺从“天意”。在这里,“天意”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它特指民心——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符合民意的行为被称为“明德”,《大学》的主旨在于阐明这个“明德”。

“爱人”——仁——因此成为华夏文明的基石,也是凝聚华夏民族的核心,同时也是规范君主行为的根本原则。从实际成就来看,华夏文明是一切农业经济的光辉典范和最高经济成就。但农业经济以“安居”为条件的“乐业”,与游牧经济的自由迁徙、崇尚个人实力,在根基上就是对立的。欧洲文明本质上是游牧文明,所以欧洲在整个农业经济时代都是黑暗、愚昧和落后的时代。但以交换为特征的商品经济与游牧经济却有着共同的文明基因,商品经济因此很容易在游牧文明的基础上生发出来。
表面上,日本文化是一种儒家文化。但华夏儒的核心是“仁”,日本儒是在“礼”的外表包裹下的“霸道”,充其量是法家霸道文化的支脉,这与古代日本的游牧(海盗)文明恰相对应。古代儒家的“礼”在现代日本已经衍变为某种繁文缛节的礼仪。日本的文化基因是游牧(海盗)文明,因而在根基上与西方文明同源,而与华夏的儒文化在距离上更远。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越是完善的农业经济,在它要向商品经济转型时,困难越大、任务越艰巨。
在西方,经济一词的原始含义是家政管理——核心是对家庭奴隶的管理。从苏格拉底开始,希腊哲学由原来的关注自然(physics),转向主要对人及人的共同体(politics)的关注。苏格拉底哲学的本意是要研究和探讨人的问题,但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社会性,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因此必须从politics(城邦)开始。举例说,奴隶和主人(公民)、公民和平民的身份认同就是城邦政治的。这暗含了一个必然的视角:对“家政”也即“经济”问题的完整理解,离不开“城邦”也即“政治”。由于“家”的形态与城邦——社会的组织过程——密不可分,因而从来就没有独立于城邦的家政,也没有独立于政治的经济。经济从来就是政治的,反之亦然。因此,一切阐释学的经济学都必定是某种政治经济学。
相反,在中文里,经济一词在词源上就是经邦济世,它偏重于经济问题的社会(政治)过程。一个现代的经济概念必然同时包含着上述两方面:就个人而言,经济是人们获取生存资料的行为方式,但人们的这类活动从来都是处于某种组织过程中的,因此经济过程必定呈现为某种政治形态。因此列宁才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因此,从人们的生存方式——经济——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政治过程,这是唯一有效的认识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就必须被理解为对经济的组织过程。“经济基础”永远是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根本力量。但社会的政治过程本质上就是社会经济过程的某种表现形式,政治本然就是经济的;一切排除了政治的“纯经济理论”不能不是一堆废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