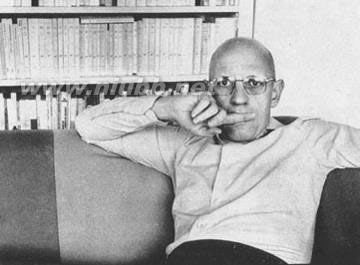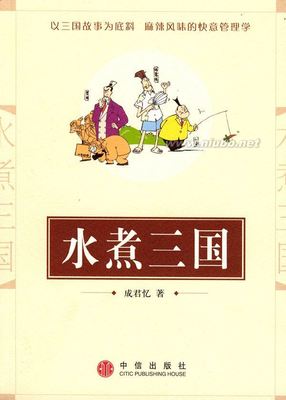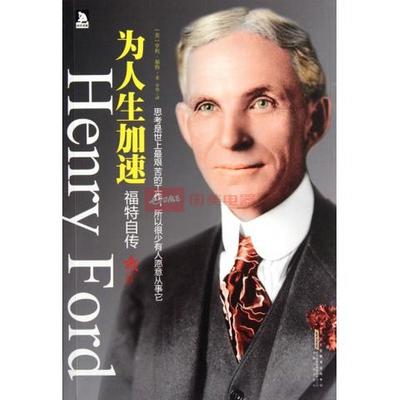为了对抗传统,他将历史聚光灯转向舞台的边缘
现代性的历史是由理性演绎的历史,在这个舞台上人作为具有最高理性原则的主体无可质疑的获得了不可挑战的崇高地位。理性的人不仅拥有决定历史向何处前进以及如何前进的权力,理性的人甚至还拥有着为自然立法的权力。理性使人获得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因此也就有权对一切他者的行为进行裁决和控制,而和权力相伴的道德优越感将权力背后掩饰的一切的专制、压迫和反抗统统埋藏了起来,粉饰给世界的是一幅朝着单向度方向演化的历史发展画卷。
这就是现代文明的历史,它一度具有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在现代性的话语里,舞台的聚光灯始终围绕着永恒不变的主题:统治者、英雄、帝王、战争、国家机器。
福柯是一个斗士,他蔑视理性所设计出来的具有强大压制能力的制度原则和道德规范。通过悬置对理性及其权力系统合法性的考察,福柯深入到了权力的微观结构并进行了惊人的谱系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通过对权力的微观运作的考察,他把关注投向到了监狱、医院等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场域,把历史的聚光灯转向了舞台的边缘,灯光照亮的是犯人、妓女、精神病人、同性恋者。在此之前,这些社会边缘群体从来没有获得历史的关照,但他们的经历却最有力的证明了在现代性的“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话语系统之中所深藏着的大量不为人知的否定、压制、暴力系统。而最让人惊恐的是,这样的“权力—知识”话语系统正是现代文明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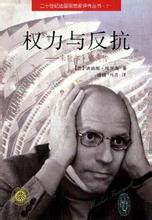
解构这套权力系统,打破现代文明的非人道主义的暴力色彩,这就是福柯的使命!
作为现代性核心的“权力—知识”体系
消极的权力和积极的权力
早期的福柯依然秉承着传统权力分析的思路,将权力视作为一种消极否定性(negative)的力量,权力分析中充满了排斥、压抑性的色彩,权力作为一种统治意志和统治工具使得单向度的支配获得合法化。
后期的福柯在对监狱等微观机构的权力运作体系进行研究的时候认识到现代权力事实上是一种生产性(productive)的实践,权力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和非信仰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权力不是某个组织、集体、亦或是个人的所有物,而变成了一个没有中心、没有主体,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张网,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作为权力的表现形式在网络中相互作用,并最终通过人的身体及行动表现为现代文明生活。
权力、知识与规训
福柯不否认知识在某些意义上具有真理的属性,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所谓的“真理”是谁的真理?即真理背后的权力及其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在现代文明中,通过与知识话语结合,权力被知识生产了出来,而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也始终不能离开知识或真理系统的介入。权力正式通过知识界定了行为的合理性,对种种不合规矩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规训,并再生产出了社会自身的模式。
规训作为社会在生产的方式体现了现代理性文明本身在扩张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种种不人道,它压抑了人自身所蕴涵的感性的动能,以纯粹的理性计算与选择完全代替了情感、欲望、想象等感性的体验。这样的文明的本质是恐怖的,也是反人文的。
为现代文明划界
立足与现代文明这一宏大范式,福柯将权力分析视作现代性分析的核心命题。这意味着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文明创造出来了“人的诞生”这一历史命题,同时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人死了”,福柯所做出的这一预言所展示的是一个文明转换的全新语境,福柯是在为现代文明唱起了挽歌。
要想实现文明范式的转换,就必须对现代文明进行更深入的剖析。而传统的分析方式并不足以为思想界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对其所生活在的文明系统进行足够的反思。并且,我们只有知道现代文明不是什么,我们才能真正知道现代文明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看到犯人、妓女、精神病人、同性恋者被现代文明排斥到边缘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被这样一个文明所能容忍的行为的边界在哪里?也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现代文明系统所不能容忍的边缘化状态的时候,这样的边缘化状态事实上才是现代文明本身的边界。
毫无疑问,福柯的学术研究展示了一种极具野心的学术理想,试图为整个现代文明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清算。略带遗憾的是,今天的福柯已经逝去,但是以“权力—知识”话语系统为统治核心的现代文明依然存在,在福柯的背影里诱惑着整个世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