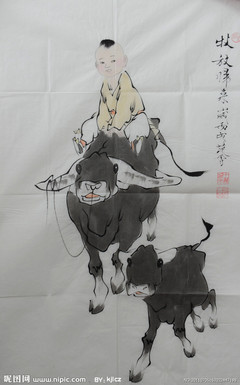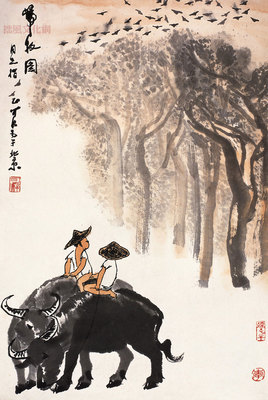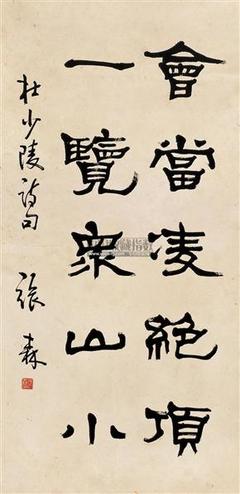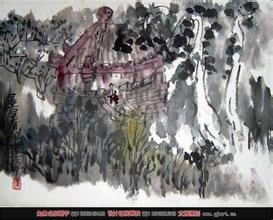
有些人生来便注定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传奇生活,甚至在他们过世之后,还不断地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乃至历久弥新,新旧印象叠加起来,远远望去更加神情飘然,别具独特的吸引力,至于真相如何,大家是不甚注意的。这时候,被公众按自己的意愿所改造过的名人们已经成为一种公众需要的存在,早已不是他们自己,他们一生的奋斗、追求、苦难、欣幸此时己变得毫无意义。想起当年他们曾那么认真地跟生活较劲,面对如此结果,真令人有说不出的悲哀。陈子庄先生过世不久,因了各种原因,几乎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不但他的艺术创造得到了极高的赞誉,其生平行事也因好事者们的口耳相传,一时间成了中国画坛内外的热门话题。不少见过或没有见过陈子庄的人也出来谬托知己,大讲不知来源的石壶逸事,把个好端端的艺术家陈子庄说成一个济公和尚似的人物:长年穿一件无袖的破棉袄,随时被美妙的川酒灌得醉醺醺,且拿起毛笔胡涂乱抹随手一挥就成一幅好画,然后又把画随便送人。其实,陈子庄是一个认真的人,不但生活上认真,艺术上甚至认真到了考究的地步。他的经历曲折,个性复杂,但这些都不妨碍他在60、70年代那样困窘的年月里,始终都保持着依现在的标准看也算是十分整洁的日常生活,更难以令人想象的是,他居然能在文化大革命举世狂热的社会氛围之中,始终都独自坚持着真正的艺术探索与创造。在1966年,陈子庄正在进行实验的山水画尚无令人满意的结果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苦心经营的绘画环境突然消失,已经改善的生活条件也被迫放弃,陈子庄再一次陷入困境。有材料说,这时候他又想到了自杀,我相信是出于失望,因为他后半生的艺术追求似乎已经不可能再有结果,但他终于没有自杀,我也相信,支持他活下来的原因还是那尚无结果的艺术追求。不过,真正的磨难这才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最初的骚乱过去之后,陈子庄这类“死老虎”已经少有人注意,思想上的压力稍有缓解,精神上的苦闷却不断加强。对于陈子庄来说,最难堪的是陷入了日常生活的陷阱。1966年以前,陈子庄每月可以从省文史馆领取60元的生活费,当上省政协委员后,根据有关政策,由政协方面补给约120元,每月有固定收入180元左右,加上从1962--1965年每周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教授绘画略有收入,陈子庄一家在当时的生活水平属中等偏上。文革一开始,所有的秩序都被打乱,陈子庄的收入就只有省文史馆按月发放的60元,这时候陈子庄已有四子一女,妻子操持家务,没有出外工作,一家七口人,均靠此生存,其捉襟见肘的窘况可以想见。然而灾难往往接踵而来,1968年,幼子寿眉游泳溺水而死,妻子受刺激精神失常,两个儿子先后被迫去农村落户,大儿子远在外地工作,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愈来愈差,心脏病不时发作,生活上的各种压力,突然之间集中到一心想为中国山水画打开一片新天地的陈子庄身上。妻子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尚能自理生活,坏的时候整天坐在里屋破口骂人。陈子庄却在外屋安静地画他的山水画。这时小女儿来报告说该做午饭了,陈子庄搁下画笔,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些零钱,交代女儿买些什么菜,然后又拿起画笔继续作画。忽然,他想起口袋里剩下的钱已经不够明天买米了,于是赶紧收拾画具,拄一根细细的青城山藤杖,出门去找家境略好的老朋友借点钱。60年代中期以后,如果到陈子庄家去,你会经常见到上述场面。这一时期,陈子庄的烦恼不仅仅来自社会,也来自他所从事的艺术,最大的压力,反而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困窘与贫穷、家人的痛苦以及自己日渐衰老病弱的身体。但就是在这艰难的时代,陈子庄的山水画进入到一个新的、澄澈清明的境界。陈子庄对黄宾虹的理解在长期的对景写生活动中因生活经历的积累而升华到一个新的层次,他从黄宾虹的墨法中悟出了笔、墨、水、色浑然一体,挥运之际随机生发的高难度画法。1968年是陈子庄家庭大难之年,他从这一年改号“石壶”,又自刻“石壶五十五岁之后作”印章数枚,不仅仅是纪念这次家庭变故,也是纪念自己艺术上开悟到一个新境界的心路历程。从1971年起,陈子庄的山水画创作进入成熟时期的高峰阶段,他不断外出写生,整理画稿,新奇的艺术风貌愈变愈多,山水画几乎每幅的情调、笔墨、趣味、结构、格调都不相同,但又和谐地统一在他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之中,一眼望去便是典型的陈子庄画风。这时的陈子庄山水画已进入到一个自由的境界。陈子庄在生活最艰难、精神最压抑、思想被严厉禁锢的时代里,以自己的艰苦努力和过早消耗生命的沉重代价,享受到了艺术创作的自由与乐趣。这一段陈子庄创作的黄金时期,由1971年持续到1976年。1972年3月,陈子庄往龙泉山写生,返成都后整理成“龙泉山写生册”34幅。10月,沿武阳江东下,历双流、彭山、仁寿三县境,得写生稿200余幅,返成都后整理成“武阳江写生册”150余幅。1973年3月,往凤凰山写生,整理成写生册12幅。10月,往夹江县改制国画纸,得写生稿数十幅。1974年秋,往绵竹、汉旺县写生,得写生稿200余幅,返成都后整理成“汉旺写生册”121幅。此外,没有记载的作品不知有多少。仅从上列时间表及作品的数量,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疾病缠身的老人在进行着何等艰苦的艺术劳动。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他在家作画期间,往往在大门外贴上“遵医嘱不会客”的字条,自己则一边口含心脏病药片,一边创作他那些美妙绝伦的山水小品。陈子庄并不是一个糊糊涂涂的人,他非常懂得自己的价值。他清楚当时中国绘画界的状况,也清楚中国绘画史的进程,他明白,在艺术史的时空坐标中,自己将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也许这些正是激起他巨大创作热情的理性基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