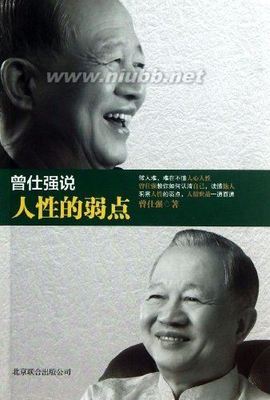【内容提要】社会何以可能?这是Georg Simmel提出的一个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本文认为,作为具有社会交往本能的人类演化的必然结果,高交往频率的人群相互间的亲和性和共同利益使合作在群体内成为可能,于是社会成为可能。美国Santa Fe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群体中自发的强互惠的出现,保证了合作在群体内的延续,从而使得群体成功演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认为,强互惠者的职业化以及政府型强互惠能更有效地对不合作者实施制裁,于是合作在强制下使得社会成为可能。这为我们展开了对制度演化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强互惠 职业化 政府
The Extens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 Theory
Wang Qin-gang
Abstract: How is society possible? This is a basic problem in social science put by Georg Simmel.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a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ings who have instinct of social contacts, familiarity and common interest among the population with high contact frequency make cooperation possible in groups. And then society is possible. The researches of economists in Santa Fe Institute of U.S. show that emergency of strong reciprocity in groups ensure continuity of cooperation in groups and successful evolution of groups. On this foundation, the article does some further research. It is considered that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trong reciprocators and governmental strong reciprocity could mete out severe punishments to non-cooperators more effectively, and the cooperation makes society possible under compulsion. It shows us a new angle of view in the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Keywords: strong reciprocity professionalize government
一、引言
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是Georg Simmel(1910)在发表的那篇英语论文的标题提出的,即“社会何以可能?(How is society possible)”。从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个体假设出发,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资源配置的博弈,自私倾向的博弈的参与者将陷入“囚徒困境”,这意味着社会将瓦解,或者,社会原本就不能形成,但事实上,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生物界,所以,理性的个体如何能够组成社会,这是一个问题(汪丁丁,2005:24-25)。动物学家Bekoff(2001)的研究表明,合作不仅是人类的行为模式,也是其它许多物种的行为模式,而正是合作以及合作的意识,才是“社会”的开端。Gallese, et al.(1996)以及Rizzolatti, et al.(1996)在人大脑皮层前运动区(pre-motor cortex)发现了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这为人类的合作交往提供了神经生物学基础。Kadushin (2002)对儿童早期的心理研究表明,人在幼年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社会交往的动机。我们有理由相信,交往是具有健全脑组织的现代人通过代际间遗传而获得的一种本能。在交往中,每个人都会生动地体验诸如良知、自尊、悔恨、怜悯、羞耻、谦虚和愤怒等情感经历,而这些体验正是有利于有关荣誉、利他、正义、同情、仁慈等普遍道德准则的形成(Wilson, 1998)。道德行为内在倾向的另一面是仇外(xenophobia),这种仇外情绪体现了信任的边界,进而人们在其频繁交往的有限人群的边界内,萌生了亲和性(familiarity)和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这使得合作在圈子内成为可能。
美国Santa Fe研究所的经济学家Samuel Bowles和Herbert Gintis在1998年的一篇论文中借用Durkheim的“亲社会性(prosociality)”这一概念,用以表示人类具有的一种偏好,此偏好有利于合作秩序的形成(Bowles and Gintis, 1998)。“亲社会性”也会损害个体,使个体为此支付较高的成本。因此,为了保证“亲社会性”在演化中的遗传优势,群体中必须存在这样一些个体,他们要求合作的对等性,积极惩罚那些不合作的人,哪怕自己付出高昂的代价,这就是强互惠主义者。“强互惠主义(strong reciprocity)”,是Bowles和Gintis等Santa Fe经济学家在最近的制度演化研究中的核心关键词。他们认为,当一个带着合作的倾向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的强互惠者,被预先安排通过维持或提高他的合作水平来对其他人的合作行为作出回应,并对其他人的“搭便车”行为进行报复,即使会给自己带来成本,甚至是不能理性预期这种报复能在将来给个人带来的收益。这个强互惠者既是有条件的利他合作者,也是一个有条件的利他惩罚者,他的行为在付出个人成本的时候,会给族群其他成员带来收益,即存在正的外部性。之所以称其为“强互惠”,是为了区别其它如互惠利他主义、间接互惠以及由重复交往或积极分类所维持的安排个体自利行为的交往的“弱互惠”(Bowles and Gintis, 2003)。在一个群体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强互惠主义者,就足以保持该群体内大部分是利己的和小部分是利他的这两种策略的演化均衡稳定,实现“演化均衡稳定性”(ESS)(Gintis, et al., 2003)。
在“强互惠主义”问题上,美国Santa Fe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们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献是Gintis (2000),Bowles and Ginits (2004),Sánchez and Cuesta (2005),Fehr et al. (2004)。Gintis (2000)开发的一个模型显示,在可行的条件下,强互惠主义可以通过群体选择在相互的利他主义中产生,强互惠主义者能够侵入一个利己类型的人群并保持均衡。Bowles and Ginits (2004)以更新世(Pleistocene)晚期的流动狩猎和根块采集为主的族群为背景的计算机仿真模型进一步显示,在大约500代以后,族群中的强互惠者的比例就稳定在人口比例的37.2%的水平上,而自私者占38.2%,合作者占24.6%,而平均卸责率为11.1%。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Sánchez and Cuesta (2005)的深入仿真研究表明,即使原来整个人群都是自私的,但只要存在产生突变的概率,如人群中突变产生强互惠者,由于强互惠者的期望接受限度(acceptance threshold)在演化过程中不断增加,也就是惩罚能力增加,从而有可能降低利己者的生存适应性,这样强互惠者就有可能在漫长的自然演化过程中得到生存。Fehr et al. (2004)利用正电子发射成像技术来观察采用真实货币支付的经济实验(an economic experiment involving real monetary payoffs with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检验了强互惠者从惩罚背叛规范者中获得满足的假说。实验结果显示,在预期的五个场合,与激励相关的脑区均被激活,尾核和壳核的血流峰值显示,其活跃程度远远超过平均水平,这时受试者表现出强烈的惩罚愿望并通过惩罚行为获得较高的满足。实验报告认为,最新的社会偏好模型所定义的效用函数包含了对违反公正和合作规范的惩罚愿望,这些模型比经济学传统的自利模型更好地解释了人类的实际行为。从Santa Fe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我们似可梳理出这样的线索:群体中的强互惠者,不论其是从相互的利他主义中产生,还是在自私群体中突变产生,他们都自愿地承担着对群体内不合作、卸责者的惩罚,他们的惩罚行为本身为其自身提供了弥补高惩罚成本的效用满足,从而使得合作在群体内延续,于是社会得以可能。
国内理论经济学界对强互惠的研究,例如汪丁丁(2005)、叶航等(2005)以及叶航、黄勇(2006)等,主要是介绍Santa Fe的研究成果,尚未对强互惠理论展开深入的的拓展。而我们的研究则希望在Santa Fe经济学家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扩展,将强互惠理论引导到有意识的制度演化研究途径上来。
二、强互惠者的职业化
Santa Fe经济学家的研究将强互惠视为群体中的一种自发力量,这种力量维持着群体意义上的生物演化所必须的适存度(fitness),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者(Voluntary Strong Reciprocator),在这样的逻辑下,制度的演化就表现为自发的无意识演化状态,显然这一思路传承了斯密的逻辑,而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也是一致的。从目前Santa Fe经济学家的研究来看,他们基本是延续了以上的进路,所以对强互惠的探索尚维持在自愿者性质的认识上,这与他们自由主义的立场是相关的。然而,我们认为,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模型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第一,强互惠者借以惩罚不合作者的条件是什么?对不合作者的惩罚可以由强互惠者自己或者由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来完成。首先,如果惩罚由强互惠者自己来完成,那么强互惠者自身必须拥有优于惩罚对象的某种质素,才能保证惩罚的有效性。这种质素可能是生物性的,比如力量、身体的强健,那么惩罚可以是身体上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比如优越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那么惩罚可以是针对惩罚对象的经济、社会利益的。其次,惩罚如果由群体中其他成员来完成,在这一情境下,强互惠者需要具有能激起群体中其他成员共同对不合作者的舆论压力或社会经济压力的鼓动力。由此我们认为,强互惠者并非每个群体成员都可能充当,或者在每一时点都可能充当,而大多数情形是,即使对不合作者产生强烈的不满,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惩罚条件,而不得不等待其他拥有惩罚条件的个体来充当强互惠者,自己选择“搭便车”。而上述不满的情绪在游戏状态下容易宣泄而付诸行动,并且游戏安排本身已经赋予了可以惩罚的手段,因此博弈实验不易察觉此差别。
第二,强互惠者如何感知何种合作模式是对于群体有效率因而需要对不合作者予以惩罚?并非所有的合作模式对群体来说都是有效率的,一些个体之间的合作可能会以降低其他个体的福利为代价,这样的合作就无须强互惠者以高成本来维系,因为其并非有利于群体的演化。那么强互惠者如何对群体中众多合作模式进行效率评价?仅此一点,我们就相信强互惠者并非任何个体皆可充当,除非他们对于一切合作的背叛都不加辨别地惩罚。因此,他们需要具备在这方面优于其他成员的认知结构,而要形成这样的认知结构又必须有相应的有别于通常个体的更广泛的社会体验。
第三,基于以上两点,我们认为,强互惠在群体中并非普遍现象,更为一般的情形仿佛应该是,普通个体在自身利益受到卸责者的侵害时,会产生强互惠行为冲动,其或者偶尔采取强互惠行为,或者由于行为能力的不足而坐享其他强互惠者的利他惩罚行为后的外部性。我们猜想,这两种情形都可以通过Fehr, et al.(2004)的实验观测到相关的脑区被激活、尾核兴奋的神经成像。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一贯性的、非偶然性的强互惠对于群体的成功演化具有不可缺失的重要意义。这样就意味着,需要有群体内特定的个体在专门的社会体验中形成强互惠行为能力和知识,笔者姑且称之为“强互惠锻炼(exercise of strong reciprocity)”,从而一贯性地从事群体内必须的强互惠行为。
强互惠锻炼,在我们看来,是指那些被群体所期待的能一贯性地有效地实施强互惠利他惩罚的个体形成强互惠能力以及手段的社会体验过程。强互惠锻炼包括两个方面的体验过程,而这两个过程都需要置身于群体中来实现。其一,在主观上经由认知过程形成必要的理性能力。如同我们在第2章中论述的那样,认知包括物理认知和社会认知,物理认知是对那些可观察到的物理世界的因果联系的把握,社会认知是对社会世界的因果联系和意义的判定。由于有限理性的假设,个体在接触和搜集信息上的时空维度的局限,其认知的形成除了自我独立的感受和思索以外,更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接受已经为其他个体证明过的经验,并在自己的实践中亲身验证和体验这些意义,由此个体获得推理能力,而通过这样的认知过程是基于群体内的交往故而其必然表达群体所共享的某些意义体系,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辨识的理性。群体成员对个体是否具有支持其强互惠行为的足够理性能力的认定,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考量其接受教育的水平以及社会接触的广度和深度,前者被认为主要对推理能力的形成负责,而后者则被用来判别其是否可获得合理性。我们注意到,因为理性形成所依赖的认知过程需要的群体内来实现,所以就一般情形而言,个体的理性很难系统性地腾空于群体的共同认知和共享意义,正是这样,强互惠者的利他惩罚才可能真实表达群体对某种合作状态的共同诉求。然而,当群体内某些个体的交往行为填补了群体之间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那么他群体也可为认知和理性的形成提供更多的渠道。强互惠锻炼的第二个方面是在客观上形成对不合作者和卸责者实施惩罚的足够力度。我们考虑,现实中的惩罚能力与博弈游戏状态下的很不相同,在博弈实验中,比如最后通牒,惩罚手段是实验设计者预先给予实验对象的,这样实施惩罚,最大的损失也仅止于没有货币收益,因此被实验者容易抱以游戏的心态对不合作者进行积极地惩罚,这也可被视为是对现实中无法真实实施惩罚而压抑的情感的宣泄。而在现实中,由于缺乏可有效利用的强互惠惩罚的手段,即使个体产生了与在博弈游戏状态中相同的惩罚动机,也难以付诸行动。那么,强互惠锻炼就正是要使强互惠者具备利他惩罚能力。我们认为,具有惩罚能力的强互惠者并非一定要通过惩罚来使卸责者得到切实的收益减少和多付成本的教训,具有惩罚能力的强互惠者在群体中的存在本身就构成对不合作者的某种威慑,从而抑制了不合作现象的真实发生。惩罚能力大约有生物性的和社会性的两种,前者如强壮的身体以及较高的战斗值,后者如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某种特殊授权。同样,除了自我修炼方式以强健肉体外,这种强互惠锻炼也必须置身于群体中来实现。总之,强互惠锻炼对于强互惠者而言,无非是获得对不合作的辨识能力和惩罚能力的过程。当强互惠锻炼在群体中已经树立了这样的认知以后,只有那些经由强互惠锻炼过程的个体才会被信任,于是强互惠锻炼也就演化成为一种标志和符号来辨识强互惠者。
正是由于需要强互惠锻炼以及随时专门性地实施强互惠利他惩罚,强互惠者就可能会失去在群体内获得生计的活动机会,如无法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收获性劳动,这就需要群体内其他成员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并不是直接针对实施强互惠行为本身的成本付出,因此与其说是补偿,不如表述为其职业化报偿更为贴切。这种报偿可以是一般财富形式,同时还可以是特殊合法化权力形式。当群体内全部成员通过让渡部分财富和权利的方式,使强互惠者身份固定化,我们坚持认为群体内经常性的而非权宜的给予强互惠者一定的身份认可对于稳定群体内强互惠者的数量、行为及其行为效果有非常强的演化优势,那么强互惠就由Santa Fe的自愿者性质转化为职业性质了,即职业化(professionalize)了。有一点需要说明,在我们的理路中,职业化的强互惠者的出现并不影响群体内普通个体偶尔的强互惠行为,也就是说,强互惠者是职业化并不意味着散落在社会中的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者的消失,前者只是从后者中被固定化而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我们认为,由于有限理性的普遍性,那么强互惠者的职业化就为社会交往提供了明确的交往符号,为群体中其他个体的理性的无知提供了更强的依赖的合理性,他们在事先已经作了必要的让渡,这种让渡可以看作是个体在日后可能自己实施强互惠行为时的成本的预先支出,由于一些个体意识到自我缺乏实施有效强互惠行为的能力、手段和知识,因此愿意预支可能发生的成本,由职业化的强互惠者来实施,我们估计这样同样能够使这些个体脑部尾核表现出兴奋状,那么,群体内其他成个体就有理由相信职业化的强互惠者会及时对卸责不合作者予以惩罚,从而他们自己就无须在掌握那些专业技能上花费成本。
三、职业化强互惠者的演化
当我们在Santa Fe的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职业化的强互惠者的概念后,深入的思索使我们接下来需要对这样的问题作以回答,即职业化的强互惠者是如何被征集起来的?他们能在演化中获得足够的生存适应性吗?
我们已经反复表明过正统的演化生物学和达尔文的演化理论认定自然选择的竞争压力只对个体以及基因显型(phenotype)起作用,并不承认群体选择。依据这样的逻辑,相同或相似生存环境里的个体必然趋于基因显型的一致,这样群体或种群内的基因显型就趋同,这一演化方向在社会学家看来,重要的功能是加强了群体或种群内部的身份认同(汪丁丁,2005:93)。而只有那些被编码进有机体的基因类型(genotype)中的特征才是可成功复制和遗传的。我们坚持认为,个体选择机制只是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生物演化的一部分。Neo-Darwinism指出,由于基因分离和重组,有性繁殖的个体不可能使其基因类型(genotype)恒定地延续下去,只有交互繁殖的种群才能保持一个相对恒定的基因库,因此,演化是体现在种群的遗传组成的改变上,不是个体在演化,而是群体或种群在演化。陈继明(1999)的统一演化理论也认为,自然选择在分别在群体、个体和分子三个层次上发生作用,这样生物演化的结果就应该表现为生物的多样化协调发展而并非简单的survival of the fittest(最适者生存)。我们从并非所有的个体都表现为某种相同类型和形态这一选择结果来考察,至少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自然选择的残酷力量并没有摧毁和灭绝掉所有的弱适应个体,因为他们借助群体的生存方式弥补了个体适应性的不足,仅就此而论,群体选择在生物演化中是存在的,至少是对个体选择的必要补充。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演化是合理的——从个体选择出发,类似环境下个体趋于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这种特征使他们以群体的方式区别于其他环境下生存的个体;同时,从群体选择出发,群体或种群内部也不排除个体间的多样性差异。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即使强互惠对于群体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并不要求群体内每一个成员都来充当强互惠者,如Ginits, et al.(2003)所言,群体中只有一小部分强互惠主义者,就足以保持该群体稳定演化均衡,群体内其他成员就成为强互惠正外部性的受益者。我们认为,在个体选择的演化理论下,强互惠个体之所以能够在实施利他惩罚丧失一定适存度后仍能获得成功演化,主要是因为强互惠者也可以从个中收获效用来冲抵适存度的下降,其中包括通过强互惠行为个体的脑部反射提供了愉悦兴奋的生物性感受以及个体得到的社会资本的积累;在群体选择理论下,作为选择单位的群体因为内部的强互惠者的存在而被选择成功演化,所以群体内就可能生发出一种倾向鼓励和稳定强互惠者的长期存在。正是这样一种倾向使得群体成员通过让渡部分财富和权利的方式使强互惠者身份固定化、职业化成为可能。
由于群体内并非全体成员都有必要充当强互惠者,那么强互惠者是如何从一般成员分化或被分化出来的呢?膜翅目昆虫社会中的单倍二倍性(haplodiploidy)的特殊遗传方式被更认为能够最大效率地传递遗传物质。这种生物性分工使得这些种群在基于群体的选择中得以生存繁衍。处于生物界食物链下端的人类,在氏族部落以及冷兵器时代,群体内也存在着这样的生物性分工,即那些身体强壮的个体更有利于出面维系群体内的某种以生存为诉求的合作方式,或者说他们更具备客观上强互惠的能力而充当强互惠者。随着人类的演化,剩余产品的出现促成了人类的社会性分工,群体、社群以及社会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使得部分个体具备了惩罚卸责者的更多的社会性手段,于是Bowles and Gintis (1998)所言的名誉效应(reputation effect of community)、报复效应(retaliation effect)和分割效应(segmentation effect)的社群治理就在他们的操作和带动下更容易显现效果。我们认为,正是因为潜在的强互惠者客观具有以上质素,他们才有可能被选择充当固定的职业化的强互惠者。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考察,希望充当群体内的强互惠者个体需要首先具有强互惠利他惩罚以维护群体有效合作模式的愿望。这种愿望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们主观上有为他者甚至陌生人提供正外部性影响的心理准备;其二,他们非常希望现有的合作模式和制度被有力的维持。以后者而言,可能因为他们从现有的制度安排中获得了利益,他们对这样的制度被维持抱有很高收益预期,所以我们认为,有谁会从群体即定的制度中、从强互惠中获益最多,那么他就主观上更愿意充当职业化的强互惠者。
那么,具备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职业化的强互惠者最后如何从群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考虑,大约有三种主要方式。第一,武力或暴力竞争方式。当缺少足够的说服手段和证明方式来展现强互惠者的能力时,这种方式最容易被选中。它反映了个体主观上急切希望职业化强互惠者的愿望,这在灵长目动物社会中可被显著观察到。第二,民主的选举方式。这种较为和平和公平一些的方式,更体现了群体对于候选个体的客观强互惠能力的共同认定,当其辅以弹劾手段时,效率会更明显。在这种方式下,个体的强互惠锻炼记录被认为是主要指标。当然,现实中并非群体内全部成员都可均等享有对结果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第三,世袭方式。由于财富以及社会地位的可继承性,那些已经获得职业化强互惠者位置的个体可以选择他所满意的子嗣来继续履行群体内强互惠行为的职责,这一过程也可被视为一种强互惠行为,即维系了群体内某种已经认定的行为方式。经由以上的方式,具有固定身份的职业化强互惠从群体中产生出来。但之后他们仍需要不断进行自身的强互惠锻炼以此不断获得群体对其强互惠行为的合法性认同,这一过程将有可能伴随其全部的职业生涯。
我们也注意到,职业化的强互惠者存在的基础必须是一个具有亲社会情感的群体。当群体中大多数成员是反社会的或者演变成反社会的,那么职业化的强互惠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群体可能就此瓦解或者原本就建立不起来。只有当群体中大多数成员表现为亲社会倾向,愿意维系群体现有合作方式和行为模式或者制度安排,愿意职业化的强互惠者充当对不合作个体的惩罚者,职业化的强互惠者才是可能的,社会在这样的第三者强制下才是可能的。于是,群体成员愿意让渡部分财富或者权利给予固定的职业化的强互惠者,使得这样的模式有效运作。
群体中固定身份专职从事强互惠利他惩罚的个体涌现出来这一事实本身应该是人类在有限理性条件下自发演化的结果。这使得群体内其他成员有可能实现对强互惠行为技能以及相关信息的理性的无知,他们只需要遵从符合被群体所辨识的共享意义的某种行为模式行事,就可获得能预期到的收益,而不必因为担心合作中被背叛而蒙受损失从而在提防不合作者上增加成本以及在合作中减少投入失却最大获益机会,他们如此行事正是秉承着对群体中职业化的强互惠者的存在及其对卸责者利他惩罚能力和效果的信任,由此即使他们在合作中确已受到不合作者的侵害,他们对通过职业化的强互惠者获得事后补偿和赔付抱有充分的信心,于是在获得同等收益的情形下交往成本被降低了。正因为如此,出于经济学的等价交换的原则,群体成员需要就他们从强互惠者那里获得的效用增进支付必要的报酬。这种报酬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让渡部分自身的权利以使得职业化的强互惠者在从事利他惩罚时有足够的合法性权力保障;其二,让渡部分自身的收益以使得强互惠者获得职业化报偿从而可以放弃一般生计性劳动。而我们坚持认为,强互惠者的职业化报偿并不是其实施强互惠行为的直接诱发因素,其主要诱因仍然是强互惠者对合作模式被维护的强烈的主观愿望,否则就不是强互惠者,至少主观上不再是。
从人类演化的进程来看,最初的人类共同生活群体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式群体或群落。在这样的群体中,主要是基于亲缘关系的合作与利他行为模式。当这样的模式的某种建构方式被群体所共同辨识到对群体的生存与演化具有积极意义时,以强互惠者出面维系这种模式的格局就可能会被选择,于是家长或族长就出现了,并且其作用以及相应的权力也随着群体的扩大而越发凸现了出来。随着群体的边界的向外延伸,更大的社群或者族群冲破了血缘关系,以互惠合作的关系将一个个家族式的小群体囊括起来。在这样的群体中,主要是基于互惠利他的合作模式,当剩余产品出现以后,这应该是促成贸易的主要途径。然而,我们注意到,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两两个体间交往的频率是趋于下降的,甚至会出现没有交往关系的陌生人。同时,强互惠者的利他惩罚的结果的正外部性,对于群体成员来说,又具有普遍效用增进的意义,从而表现为公共品(public goods),而公共品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以及不可分割性使得强互惠的外部性很难以价值方式精确地划分,所以互惠利他并不能完全不成立。那么,强互惠者实施利他惩罚行为并不是基于互惠利他的远期收益的等待,而只能是群体为长期拥有身份固定身份的强互惠而进行必要的让渡以支付的职业化报偿。这样的让渡体现了群体的共同的意志,因此其本身就体现了群体所要求的一种合作模式,即无论群体成员是否自愿,这种让渡与支付都强制的进行。这样当我们将对上述财富的让渡的征集界定为税收时,职业化的强互惠者就对应着政府,或者说,当上述财富的让渡演化为税收时,职业化的强互惠者也就演化成为政府,于是我们就构造了一个新概念——政府型强互惠。
四、一个新概念:政府型强互惠主义
“政府型强互惠主义(Governmental Strong Reciprocity)” 是我们基于Santa Fe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理路,将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扩展到职业化层面后经由以上的分析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在这个概念下,Santa Fe意义上的强互惠者的界说仍然是成立的,即强互惠者主观上愿意对群体内不合作的个体给予惩罚,哪怕自己付出高昂的代价也毅然而为之。我们的研究是在主观意愿的基础上,赋予强互惠者客观的能力和权力,从而展开了职业化的探索途径。我们认为,政府型强互惠应该是人类在演化中群体方式的生活习惯下自发演化的产物,其中至少有两个主要的理由使我们相信群体内必然生发出政府型强互惠组织。
第一,当人们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就要求更多的合作方式在更大的群体内达成并被维护,于是那些被血缘、种族或者地域分割的古老的零散群体之间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将不断被一些利益的共识所填补,这样群体就不断扩张成长,成为部落、成为社群、成为社会。因此在更大的群体或者社会内,被认定为有效率的合作模式的数量将激增,需要强互惠者以职业化手段维系的合作或者制度安排越来越多。然而,即使是经由强互惠锻炼的职业化强互惠者仍然受限于个体的有限理性而无法实现所需的全部理性能力,为此内部分工明确的组织化结构的职业化强互惠者群体逐渐演化出来。这样的群体的规模取决于社会内需要维系的合作模式的数量,进而取决于社会规模的大小。同时,这样的群体的规模还取决于社会成员愿意或者可以承担的以形成强互惠报偿的财富让渡数量。当然,由于无法精确在个体成员中间以效用增进来确定财富让渡的量,就只能以固定的方式强制性地征收来构成以上职业化的强互惠组织的报偿收入,这种对群体成员强制征收的即是税收,其形成的即是财政收入,而职业化的强互惠组织就是政府。
第二,随着群体的扩大,群体内的利益更趋多元化,这样以来,在不同场合下的不合作者或者卸责者的数量就将增加。因此职业化的强互惠者的强互惠利他惩罚的手段就必然要求加强。同时当不合作者卸责者甚至那些蓄意破坏群体已然认定的合作模式的个体拥有足够的对抗力量时,职业化的强互惠者一般性质的强互惠能力可能已经无法保障其职责的履行。于是,他们需要借助经由群体成员的让渡而获得的权力建立专门的暴力性机构以强化惩罚力量,这种力量被强化到足以对于对破坏群体所认可的行为规范者、不合作者实施最严厉的惩罚直至剥夺其社会性生存甚至生物性生存的权利。这样的权威的暴力性机构就成为了政府的重要特征。
我们认为,政府之所以有足够的惩罚性权力,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群体和社会内因为固定充当强互惠者使得被群体和社会认可的合作和行为规范被持续地维系从而获得了合法性。合法性来源于政府型强互惠者的代表性,政府型强互惠者的代表性并不要求全面,只要强互惠者维护的行为模式代表的某个亚群体可以给予其足够的合法性支持。换言之,当某种合作和行为模式被某些成员认定为是有效率的或者是可以提供满意收益时,固定身份的强互惠者对这样的模式的维系就可获得来自前者的支持,而当这种支持对于后者提供最大的适存度,后者就获得了在群体内演化机会,从而其权力就具备了合法性来源。依据这样的逻辑,我们似可得出如下假说,先有制度,才有维系这种制度的政府,制度在群体内的代表性决定了政府的代表性,并且这样的结论也是合理的,即是制度创造了政府,而非政府创造制度。即使政府不存在,社会合作范式仍然存在,人们仍然要服从某种约束。所以,不是政府制定规范由人民执行,而是人民相互间制定规范,由专职的政府人员来履行监督之责(Simmons, 1993)。依据我们论述的进路,我们可以如此界说政府,这是一个社会中或者群体内的职业化强互惠者的功能性结构性组织,他们被群体选择用以维护群体内具有代表性的规范和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政府首先是强互惠主义的。
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职业化的强互惠者的出现并不影响群体内普通个体偶尔的强互惠行为,强互惠者是职业化并不意味着散落在社会中的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者的消失,那么政府型强互惠者就并非囊括了群体内全部具有强互惠利他惩罚行为倾向的个体,或者说政府并非是全部强互惠者的集合。还有一些不具备群体代表性的行为模式制度范式被另一些没有进入政府组织的强互惠者维护者,他们可能是游散状态的强互惠者,也可能是固定身份的职业化组织化的强互惠者,后者构成了政治学意义上的院外活动集团,他们的存在对现存政府构成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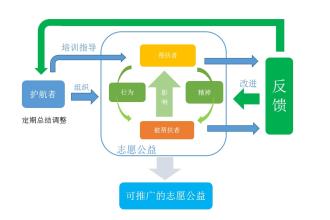
五、结语:制度演化研究的新视角
我们认为,合作或者借用Bowles and Ginits (2004)的表达——“异质人群的合作(Cooperation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对于稳定的社会建构至关重要,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拥有良好合作秩序安排的社会中的交易成本将低于缺乏合作的社会。合作是作为具有社会交往本能的人类演化的必然结果,高交往频率的人群相互间的亲和性和共同利益使合作在群体内成为可能。从相互的利他主义中产生或者在自私群体中突变产生的少量强互惠主义者保证了合作在群体内部的延续,从而使得群体成功演化。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作为群体内的自发力量的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主义并不能充分保证强互惠长期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因此强互惠者的职业化就成为改善这一状况的选择。当人类交往的技能不断拓展自己的交往范围,合作就需要在更大的群体内实现,职业化的强互惠主义就表现为政府型强互惠主义,政府型强互惠者利用其合法性权利制裁卸责者或者违背制度者,于是合作在强制下使得社会成为可能。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一旦强互惠者职业化就会产生强烈的建构主义的精英行为倾向,制度演化可能从自发演化的内生型(endogenous)被导向为强制主导的外生型,或者内生与外生相互约制的混合型。生物学家LeDoux(2002)把心智从无意识状态到意识状态的过程描述为一个连续谱系,在意识出现之前,演化主要是“天演”——物竞天择,而当意识涌现出来之后,就出现“有意识演化(volitional evolution)”。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的制度变迁行为方式有明确的认知,因此社会公众的制度演化选择必须体现这种认知,在政府认同的框架内或者边缘选择有意识的演化方式和途径,这类似于Buchanan and Vanberg(2002)所表述的“宪法约束下的制度演化(constitutionally constrained evolution)”。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公众对其强互惠行为的期望和委托这一事实也有充分的认知,因此制度的“理性设计”必须考虑到社会公众的自发演化状态,如果设计的制度与之一致,便会推进得顺利,但若与之相悖,就会显得相当艰巨,最后可能会被拖离其原先的设计目标,从而被锁定在低效率状态中。因此,在这样的博弈中,社会制度的演化的轨迹将可能呈现出非线性的点状均衡态势。
政府型强互惠主义为我们的制度演化研究展开了一个新视角。这样的研究途径将使我们可以摆脱在有关制度演化的理性设计和自发演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上纠缠,我们可以立足于包容二者的统一的框架来审视政治、经济、产业等制度的沿革路径。由此我们可以建构如下的制度演化研究思路:首先,个体在交往中逐渐生发出亲社会情感,于是他们出于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的考虑选择相互合作的行为方式,这样诸多行为方式经由模仿以及代际复制在群体中扩展,并内化为习惯、习俗或者制度;然后,那些倾向秩序欲求的个体从群体中凸显出来,无论他们是群体选择还是个体选择的产物,总之他们的出现给予了群体内选择合作的成员这样的信息提示,即习惯、习俗或者制度将会被遵从贯彻,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是高昂的,合作被维持着,这样作为群体内的亚群体的强互惠者存在的价值得到肯定;这样强互惠者逐渐从自愿者性质转向职业化,专门从事对群体内不合作者的惩罚,社会得以可能,而职业化的强互惠者开始从一般群体成员中分化出来,于是政府出现了;政府型强互惠主义模式下,职业化的强互惠者经由分工而导致其技能的提高,或者说经由强互惠锻炼他们自认为或者被认为具备了维系合作、社会方面的优于其他成员的专门知识以及理性,前者在哈耶克那里被认为是“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而正因为如此政府型强互惠主义者逐渐表现出明显的建构倾向,于是当制度在自发演化和理性设计的博弈中收敛到某个不动点时就表现为均衡。然而,我们认为政府应该达成这样对自身的定位,他们首先是强互惠者,其次才是制度的建构者。那么我们就不会因为各种蓝图式的制度设计方案无法推行或实施效率打折扣而感到不安了。以我国的企业改革为例,企业的出现基于Coase(1937)的逻辑是降低交易成本的自发演化结果,而建国初期由于客观历史原因,政府将企业替代市场的边界无限向外延伸,出现了“小而全”、“大而全”的企业办社会现象,实际操作证明这样的理性建构明显效率低下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的发展。但我们的理路并非是要将政府拉回到斯密的“守夜人”位置上,我们是希望在强互惠主义者这样一个基本政府功能上探究政府的建设性的定位。对此,我们可能只是启发了一种思路,事实上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更多智慧的参与。
【参考文献】
[1]陈继明.,统一进化理论刍议[J] .科学通报,1999,(16).
[2]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Ⅱ:社会思想与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叶航 汪丁丁 罗卫东.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J].经济研究,2005,(8).
[4]叶航 黄勇.2006,第三种叙事方式:对休谟法则的超越[J] .浙江社会科学,2006,(5).
[5]Axelrod, Robd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4.
[6]Coase, Ronald H..The Nature of the Firm(1937).in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M], pp. 33-55.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7]Bekoff,Marc. Social Play Behaviour[J].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001, 8(2), pp. 81-90.
[8]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The Moral Economy of Communities: Structured Popu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social Norms[J].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1998, 19(1), pp. 3-25.
[9]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The origins of human cooperation. from Peter Hammerstein, ed., Genetic and Cultural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M]. MIT Press, 2003, pp. 430-443.
[10]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its. The 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 Cooperation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J].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2004, 65(1), pp. 17-28.
[11]Buchanan,James M. and Viktor J. Vanberg.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Radical Subjectivism[J].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002, 15(2), pp. 121-129.
[12]Fehr, Ernst, Dominique J.-F. de Quervain, Urs Fischbacher, Valerie Treyer, Melanie Schellhammer, Ulrich Schnyder, and Alfred Buck. 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J]. Science. 2004, 305(27), pp. 1254-1258.
[13]Gallese, Vittorio, Luciano Fadiga, Leonardo Fogassi and Giacomo Rizzolatti. Action Recognition in the Premotor Cortex[J]. Brain. 1996, 119(2), pp. 593-609.
[14]Gintis, Herbert. Strong Reciprocity and Human Sociality[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000, (206), pp. 169–179.
[15]Gintis, Herbert, Samuel Bowles, Robert Boyd and Emst Fehr. Explaining altruistic behavior in humans[J].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3, (24), pp. 153-172.
[16]Kadushin, Charles. The Motivational Found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Social Network. 2002, Vol. 24, pp. 77-91.
[17]LeDoux, Joseph. Synaptic Self: How Our Brains Become Who We Are[M]. New York: Viking (400 pp.) Jan. 14, 2002.
[18]Rizzolatti, Giacomo, Luciano Fadiga, Vittorio Gallese and Leonardo Fogassi. Premotor Cortex and the Recognition of Motor Actions[J].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1996, 3(2), pp. 131-141.
[19]Rizzolatti, Giacomo, Leonardo Fogassi and Vittorio Gallese. Cortical Mechanisms Subserving Object Grasping and Action Recognition: A New View on the Cortical Motor Functions. in M. S. Gazzaniga (ed.), The New Cognitive Neurosciences[M].2n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0, p.539.
[20]Sánchez, Angel and Jose A. Cuesta. Altruism may arise from inpidual selection[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2005, (235) pp. 233-240.
[21]Simmel, Georg. How is Society Possibl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10, Vol. 16, pp. 372-391.
[22]Simmons, A. John. On the Edge of Anarchy: Locke, Consent, and the Limits of Society[M]. Princeton, N.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3.
[23]Wilson, Edward O..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Morality[J]. The Atlantic Monthly. 1998, 281(4), pp. 53 – 70.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3期,引用请注明出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