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几百万年的生理演化一向以地心引力和一大气压空气为中心。我们顶天立地地站着;我们的肌肉、骨骼不停地接受着重力的千锤百炼,才能维持它们的强度;内耳的半规管依赖重力使我们能辨方位;我们的心脏血管的正常操作也是以地球重力场和一大气压为主轴演化发展出来的。 在过去四十多年太空飞行中,苏俄和美国的科学家收集了一些初步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失重对内分泌、红白血球的产量、内耳平衡器官及骨质的松弛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最明显的生理失重状况,莫过于太空失水及其引起的一些症状,如太空贫血、内分泌降低、双腿肌肉萎缩等。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妥善处理,小至影响航天员的健康,大至引起宇宙飞船操纵失控。 人类的体液在重力作用下,大部分集中在下半身,在失重状况下,下半身的体液会向全身分布,造成脸部充水等现象。人体内两个重要的压感中心(baro receptor)全都分布在上半身,一个在心脏大动脉上,另一个在颈动脉上。这两个中心在失重时传给脑部的讯号,并不是体液重新分布的讯息,而是体液太多的告急信号,这个信号会引起体液大量排泄。aihuau.com 通常在航天员进入地球轨道后二十四小时之内,这种排水的现象就会告一段落,此时体液的分布,和在地表重力环境下不同,基本上是一种严重的失水状态。在微重力下,人类的生理机能平衡在一个和地面不同的基点上,在这个新基点上,航天员的血压与心跳都比在正常重力下约低上5%。血压与心跳的变化幅度降低,应变能力也随之减低,但航天员可以在这个基点上正常地生活与操作。 然而,生存在这个新的基点上,明显地潜伏着危机。譬如说,宇宙飞船突然需要紧急降落,航天员没有时间补充失去的体液,一旦重返正常重力状况,体液重新向下半身集中,造成上半身贫血,轻微状况会造成头晕,严重情况会造成休克。如果发生在正副驾驶员身上,就会造成极度的危险。美国航天员最严重的病例有两起,他们都需要在降落后,马上打点滴,把失去的体液补充回来,才能站起来。 唉!航天员进入太空失重状态后,入厕频繁,大量失水,身体机能已很不爽。有些航天员还得在空间站长住六个月。骨骼和肌肉细胞得此讯息,不胜雀跃,因为它们不必再每天费劲跟重力场拼搏了。别忘了,我们细胞是聪明的,既然不需我们支撑您航天员的体重,那就让我们歇歇,做个懒虫吧! 骨骼和肌肉细胞开始罢工,骨质和肌肉马上萎缩。航天员在太空不用肌肉骨骼,本可置之不理。但六个月下来,肌肉骨骼流失百分之十。返航落地后,不能挺胸昂首地走出宇宙飞船,竟需要救护担架抬着,有损英雄形象。 于是航天员只好绑上橡皮筋,每天在太空舱内拼命做撞击跑步运动,模拟重力场情况,明确照会体内骨骼和肌肉细胞,甭躲清闲耍小聪明,该干嘛干嘛,继续给我制造足够的细胞产量。 在失重的情况下,每天挥汗运动四小时,要消耗大量氧气。于是航天员集体一致要求,饶了我们吧,我们已失去重力场,请别在太空舱的空气方面再剥削我们,给我们一大气压吧,像海平面地球老家那种的空气,101.3千帕,21%氧,78%氮,让我们在太空中至少还能呼吸到哺乳类几亿年来最爱的空气,拜托拜托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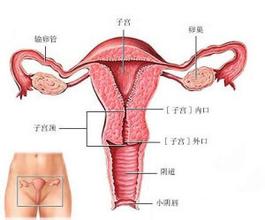
大家对一大气压的概念非常熟悉。但在讨论出舱任务时,工程师喜欢用比较精确的“千帕”来形容。一大气压为101.3千帕,大气中氧的分压为21千帕,氮的分压为78千帕。本文也跟着千帕一番吧。 所以近代太空舱的设计,包括以前的和平号空间站,现在的国际空间站、航天飞机和神舟宇宙飞船等,都是使用人类熟悉的一大气压空气,尽量在失重的环境下,不再增加航天员生理上的负担。 人类也掌握一大气压下所有的物理、化学、医药和生理等科学数据,尤其是有关太空舱所使用的材料和燃烧中间的关系。太空舱着火可不得了。虽然在无重力下燃烧化学和地面有很大的差异,但在一大气压下,我们所拥有的灭火知识最丰富,安全保障系数最高。 关在和海平面相同的一大气压下太空舱内,航天员的生活作息的确愉快了不少。但这个优越的条件,为舱内航天员专享,对要出舱的航天员,一大气压代表的是一堵高大的围墙,增加了出舱的难度。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