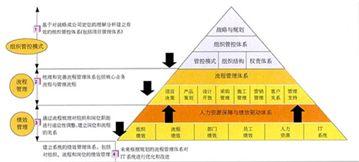之二:经济学的死穴在哪里?
前面有帖说过,经济学其实就是研究交换的,因为交换现象的存在是“经济”一词可以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有人简单明了地说,经济学其实就是研究“利”的。这话一点也不假。然而仔细揣摩就知道,“利”就是“用”,只有“用”过了才有“效”,有“效”就是获得了“利”,而有“用”性也就是“价值”。两种认识,一个是说行为的目的,一个是说行为的方式,侧重点不同而已。
因此,经济学作为研究交换行为的学科,行为只是一个表象,是一个达成目的的手段方法,深层次的方面则是以“价值”为根本探究对象的。故而,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和根本。
然而,价值理论又不是一门经济学所能和必要探究的东西。并非钱皮一人认为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但是持此观点的人在价值概念本身的界定上面却依然是各执一词。事实上,当一个经济学人能够探究出“价值”的真谛的时候,他已经超越经济学科的界线,升华为一个哲学家了。为何又说不必探究价值理论?因为有那么多哲学家孜孜不倦地在做这件事了,何必以一个外行之能和去一大群内行一争高下?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有本事站在哲学高度俯视经济学,那就大不相同了。
然而,传统的经济学脱离了哲学对价值的研究轨道,想自成一体而走向歧途,最终失于迷茫。针对声称不考虑价值判断的经济学思潮,经济学家G·Myrdal(1898~1987)指出:不可能存在没有价值取向的经济学理论,任何(经济)社会理论都包含了政治的、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部分。
既以为核心又不必探究,何解?这就是告诉经济学人,老老实实地把哲学界关于这个命题的研究结果拿来使用就是了,不要试图去创造一个独立于哲学价值理论之外的经济学价值理论体系,除非你要做一个有深度的哲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价值理论重新审视的新热潮当中,“价值物质论”这种陈旧的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又再次沉渣泛起。这种混淆混淆本体与本体的性质、混淆本体的内在性质和外在性质的思想对把握价值理论在经济学上的运用起到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如果不能认识到价值是人赋予事物之上的、因人而异的外在东西,那么,即便是认识到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的基础作用,也依然不可能由此得到正确的经济学结论。
价值理论要解决什么问题?其实,作为自然进化的一个环节,人类本身并不需要一个“价值”问题存在。价值问题,其实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人生的意义”。
然而可以说,“人生的意义”是人类文明史和哲学史上最没有意义的一个命题。这已经成为人类所有社会科学所难以承受之重,更不要说是经济学了。何时人类从哲学层面破解了生命的意义这个千古难题,经济学才能随之走出死穴。如此说来,经济学其实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陷阱之中,既不能放弃,又注定无果。如果有一门“生命意义学”的话,经济学其实应该含于其中。
由于本质上是关于价值的理论,现代经济学总是摆脱不了对“工作——闲暇”关系的研究。但是,经济学人在这个方面实在是太过愚钝了,不仅仅用一个自定义的恒等式(工作时间+闲暇时间≡生命时间)来当作独立的条件方程,而且彻底模糊了两者的关系。殊不知,当人们用生命的一个部分去换取另一个部分的时候,潜意识当中却是将生命的每一个时间段都看作等价的。如果我们问“将两个小时的生命分成两个一小时,哪一个小时更有意义?”,一定让人难以回答。有人说工作是为了闲暇,想多多放假想早点退休以享受生活;而有人说闲暇简直就是浪费生命,退休不久就无所事事郁郁而终。有人说人生要有目标才行,有目标或者才有意义;有人说过程大于结果,不必在意成功与否。对于一个吃饱了就睡的狮子来说,它不会去思考捕猎和睡觉哪样更有意义以及如何分配捕猎和睡觉的时间这种问题,即便是一个生物学家在旁边观测研究,结论也一定是狮子的时间分配方案是最优的。这个无解的问题大概只有人类才会去苦思冥想。
说来说去,人生的时间转换过程,无论是以工作换取闲暇,还是以闲暇舒解压力补充体能以利更好工作。仔细审视人生,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一场博弈,以一段生命历程换取另一段生命历程,是在以被忽视的无穷大成本(命价!血酬!)博取自以为有价值的收获。
一次交易中,对方拿着钞票感慨万分:“国家印这么多花花绿绿的东西让我们为之辛劳奔波。人为何要活得这样累啊?”一向自以为对经济学有所浸淫对人生有所感悟的鄙人一时无言以对。你瞧,当人们试图从拜物教的糊涂状态中挣脱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心灵是多么的迷茫和痛苦?
当人到达生命的终点,蓦然回首,才知道什么叫做“折腾”:人生的追求,终究都是一场正宗的等价交换,原来是以生命的流失换取生命的延续,这是一场零利润的折腾——谁也找不到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如果真正考虑所谓的“隐成本”的话,人生的隐成本其实就是无穷大。其实,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原点。与其说“博弈”还不如“折腾”更精准,毕竟博弈是冒险图利的行为,而这里压根就没有任何利可供图谋。
中国学者爱把孔子和庄子对比评价。有人说孔子是八小时之内,扮演的是社会角色;而庄子是八小时之外,扮演的是个人角色。那么,换用经济学家的行话就是,孔子是关于工作的,而庄子是关于闲暇的。据此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亦孔亦庄。在国人眼里,孔子庄子都是圣贤,由此可见,无论工作还是闲暇,都可以达到人生的极致高度,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都难以伯仲,无能贵贱。因此,无论是“工作派”还是“闲暇派”,其实都是以藐视生命的一部分而追捧生命的另一个部分,都是自相矛盾的心态,都不符合每一个生命的每一秒都是弥足珍贵的这种认知。
然而,从价值理论流派区分,孔子可以说是“客观”价值论流派,而庄子属于主观价值流派。孔子认为有一个不可更改的、人人都需要遵守的道德规范存在(这当然是他自己认定的标准);而庄子似乎认为价值观因人而异、人性自由。
站在哲学层面看待经济学,你就会认识到,经济学其实一直是在“拜物教”思想之下展开的。拜物教很实在,它维系了经济学人对自己行为的价值认同。但是,当有人把这个问题引申到哲学层面,引入“人生的意义”范畴的时候,结果是许多人不愿也不敢面对的——“生命的价值”,这个问题竟然成了生命本身不堪承负之重。
其实,人在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存在着自我矛盾的困惑。一方面,人类具有深深的自卑心态,对大自然充满畏惧;另一方面,人类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自傲自恋的动物,需要从克服自卑的过程中确认自己的中心地位。一个登山家的行为动机是什么?首先他把山峰看得比自己高大,或者说认为自己是渺小的,但是他要征服山峰,从而证明自己并不是渺小的。假如一开始他就把山峰视作渺小的,他就不会去征服山峰,因为征服一个弱者没有意义,胜之不武。但是,当他征服山峰独自坐在山颠之上的时候,他感到的是自身更加深刻的渺小和孤独,而不是位居万物之上的高大,从求胜的寂寞转而变成求败的孤独。而神就不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问题,它已然处于自在状态,它高高在上却不会去感叹高处不胜寒。人不是神,所以才会有一个生命价值问题存在。
“生命的意义”是一个千古难解之题。孔圣人所向往的人生不过也就是“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做到“乐而忘忧”并不难:傻子乞丐像流浪狗一般慢条斯理地在垃圾堆里寻找着食物;神仙悠闲地在山谷石桌上对弈,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地挥霍着时间;商贾为敛聚钞票乐而不疲地奔波……对于大多数不敢面对“虚无”人生的人来说,或许,政治家们以发展经济的口号鼓动拜物教是一种至上的明智。既然多数人不敢面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何必要残忍地让大家面对?拜物教思想把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同定格在哲学家和圣贤看来无意义的时空点上,成功地使人们摆脱了对生命意义思考带来的深度烦恼,用一种固定的欲望使得人们摆脱对万劫不复的无底欲壑的恐惧。
是不是钱皮在鼓吹“淡泊名利”?如果我说“是”那就等于是说“不是”了。说出“淡泊名利”这种君子之言的人得到的就是圣人之名和人人敬仰之利,“淡泊以致远”,淡泊是手段,致远是目的,有目的就是有所求,所求就是利。真正要淡泊名利,就不要说出来,连这个可以因淡泊而得到的圣贤之名也彻底丢掉它。不单单是经济学要面对趋利避害的理性人,一切社会学科都躲不过这个问题。趋利避害之利是广义之利,而淡泊名利之“利”是狭义的金钱之利。在广义的“利”之下,“淡泊名利”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利”,何言淡泊?
这就像宗教教导人们放弃一切,而这个“一切”其实并不是一切,因为还有“得道成仙”“修炼成佛”的坚定信念是不能放弃的。禅定以达净空,禅定仅仅是手段,净空才是目的,“成佛”就是出家人无法抗拒的最大利益诱惑。行为和行为的动机只有生命才会具有,佛永远、已然地处在目的地,不需要再为之付出任何行为,连淡泊都不需要。
“极高明而道中庸”,对吗?高明与否,是有明确的指向的,而中庸是没有指向的。高明是有序,是有;而中庸是无序,是无;极高明者什么也不说,连中庸也不须道。大智者若乎愚,是一种糊涂状态。高明到了极点就是糊涂,即物极必反,有(高明)生于无(中庸)。中庸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糊涂状态,概此,才有难得糊涂之说。
在古典的劳动价值论中,其实包含着人与人的生命绝对平等的理念。我干了一天的活,你坐在那里写了一天的字,大家都是耗费了一天的生命,凭什么你的一天要比我的价值高?但是,价值就是有用性,是按照产品的有用性判断价值的,而不是按照劳动时间判断价值的。现实当中,比尔盖茨和街头乞丐都是爹妈生的,制造成本没有什么差异,生一个盖茨不一定会比生一个乞丐难产,但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尽管我们认为在社会、人伦、道德等层面他们是等价的,比尔和乞丐还是有天壤之别,因为他们的有用性即创造的价值有着天壤之别。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李嘉图和马克思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对涉及到的劳动的本质视而不见,李嘉图声明不考虑字画古董,马克思的《资本论》则声称只针对简单劳动。看来,要想解决“人生意义”这个的问题,还是真有难度!
说跑题了?不像是经济学?要是跑题就对了,跑题即切题,物极必返嘛,说明我说到了点子上了。
经济学的学术霸权是举世瞩目的,也是令人厌恶的。俗话说,一瓶子不响半瓶子晃荡。经济学的语言霸权习惯岂不正是它自身不满浅薄轻狂的表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轻狂吗?不。这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同样因为物极必反,发展到极致是终结,既然极大地发展了经济学,也就等于是终结了经济学。
有道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说这句话的人也真是幽默至极!人既是上帝的创造,它干吗要嘲笑自己创造的这个会思考的人类?这不等于在说自己的创造失败吗?上帝眼中应该没有轻狂和稳重之分。记得在某论坛上有网友提问:万能的上帝如何才能打倒自己?现在似乎有了答案:却原来,创造人的上帝是人创造的——万能的菩萨竟然不会塑造自己!要靠自己用泥土造出的人再用造人剩下的泥土塑造一个泥身以寄托其中。
人类一思考,上帝真的会发笑吗?会吗?
喂!问你呢,发什么愣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