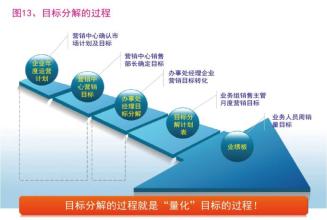两个月前发表了《经济学的缺环》后,写了五期从合约安排的角度再解释,要给同学们打个基础,然后转到复杂的层面去。不是由浅入深,而是由简单转向复杂。处理湛深的学问我可以势如破竹,视若等闲,但复杂的学问想到就头痛。无奈世界上真的有复杂的一面,怎样简化也是一连串的交叉。对复杂有恐惧感的同学不读下去算了。
前文提到的座位票价、捆绑销售等现象,以交易费用作解释,看似湛深,或巧妙,其实是雕虫小技,只要灵机一触,答案信手拈来。熟能生巧,经过数十年的操作,这类课本一般不染指的有趣现象,我可以一天处理一两个。容易,因为简单。有解释力的经济学来来去去都是一条需求定律,一些局限转变,没有其它。前者的阐释与变化的掌握,要花上几年工夫,但有个尽头,到了某一点就可以操纵自如了。局限的转变才是经济解释的学问所在,处理的人要懂得分辨哪些有关,哪些无关,而牵涉到交易费用这项重要局限,要懂得怎样把无从量度的,用推断的方法,转到可以观察的量度去。
回头说票价偏低那个现象,提出了假说,考虑的局限只是监管费用,其它不重要。只要能在观察上处理这项局限的转变,验证的跟进只是几天的工夫。是史德拉一九四六年提出的一点教了我的:解释行为不需要知道总成本,只要知道成本的转变——即是要知道边际成本了。《票价》一文,处理监管费用,与处理成本一样,我只管转变,边际的,而且只是一项。有一点灵气就可以应付了。
可惜世事往往不是那么简单。好些时,一个现象牵涉到几方面的交易费用,而当有关的现象串连起来,要考虑的「边际」相当多。一九七二发表的关于中国婚姻与子女产权的文章,我花了半年时间参考资料,而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断断续续地调查件工合约与思考,花了十三年。
这就带来经济整体运作这个话题,复杂无比,是大学问了。首先,原则上,解释现象我们要从边际看,也即是说要从局限的变动入手。但边际或变动可以小于鸿毛,也可以巨如世界,加上有关的「边际」无数,哪些是重点,哪些要删除,前辈大师也频频失手。在我之前,只四位分析过经济整体的运作:史密斯、李嘉图、米尔、马歇尔。皆顶级天才无疑问,分析力强,老实说,他们创立的理论架构好,实在好。没有他们的架构,西方经济学不会有大看头,与我们春秋战国时代的思维差不多。经济学西方胜出,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架构。几年前写《经济解释》时,这架构我修改了多处,但还在用。
史密斯的架构传统,牵涉到经济整体,广泛复杂,大手简化是需要的。然而,从古典到新古典,大师们选择了或明或暗地漠视交易费用,是严重的失误。说过了,从广义的交易费用看——从鲁宾逊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看——没有这些费用,不会有市场,不会有产权,所有经济体制皆无足轻重。这是说,所有组织问题、合约问题、制度问题,包括市场的存在,皆因有交易费用而起。换言之,所有竞争制度,包括权利的界定与决定胜负的准则,从套套逻辑的角度看,一定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存在的。
这样看,要分析经济整体,我们当然要把交易费用——或广义地说要把制度费用——放进去。问题是要怎样放进去才对呢?不是像座位票价那么简单的监管费用的转变,而是要解释地球经济体制的存在,广义的交易或社会费用要一手放进去才可以满足分析的要求。要怎样放进去才对呢?从一九七三想出那广义交易费用起,我或断或续地想了近三十年,到二○○二写《制度的选择》时才想到自己满意的答案。
有三点,都困难,加起来复杂得很,不容易处理。
第一个困难起自自己的茅塞,想来想去也不知怎样把制度(交易)费用放进制度整体中。二○○二的一个晚上,梦中惊醒,对自己说:「蠢到死!制度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怎还可以把这些费用加进去呢?要把这些费用减下来才对,减下来才可以看到制度的形成!」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从上头减下来的想法可不是突如其来的。一九七三思考七四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时,想到上述的广义交易费用,知道租值消散是交易费用的一种;一九八一思考中国的去向时,知道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不会有市场或任何组织或制度。一九八二动笔写《公司的合约本质》,从减低交易费用的角度入手,处理好几方面的边际转变,不容易,但基本上还是处理座位票价的方法。想得很近,但经济整体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如何减法,还是无从入手。
二○○二年那个晚上的灵机一触,我立刻想到一九六三年在新加坡大学任职的A. Bottomley写的只两页纸的一篇文章。该文分析Tripolitania的公共土地的使用,说原本很适宜种植杏仁树的土地,因为是公用,没有谁种植价值高的杏仁树,大家只在草原上放牧。作者没有说,但杏仁树的放弃显然是租值消散。
消散了的租值怎会是交易费用呢?我想到自己的价格管制理论。有价管,顾客排队轮购,浪费了的时间有所值,但没有产出什么有价值的,所以排队购得的物品的价值,一部分是消散了。另一方面,排队轮购是一种交易行为,时间的费用是一种交易费用。这样,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画上等号,虽然不一定是全部的。

杏仁树的放弃无疑是租值消散,但没有交易,怎可以看为交易费用呢?有两个要点让我们这样看。其一是上文提及的广义交易(制度)费用观——在一人世界不会有租值消散。其二是成本的概念。成本是最高的代价。如果土地的租值最高是种植杏仁树,那么放牧的社会成本是杏仁树的放弃。二者相加,放弃杏仁树是交易(制度)的费用(成本)了。
略为复杂,但要想那么多年,天才安在哉?有了这个领会,经济整体的交易费用不难减下去。也不容易,因为还有其它两点──还有两个大麻烦。
(之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