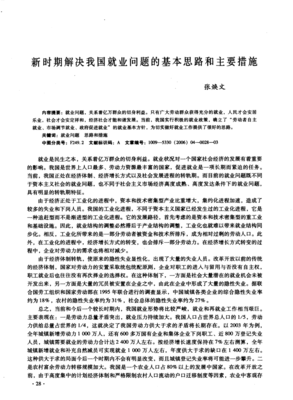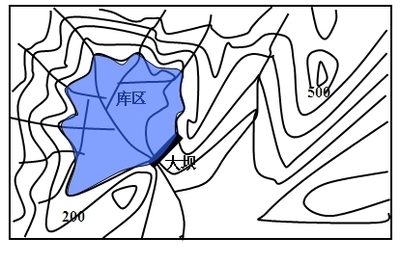(这是一篇1999年秋的旧作,照原稿贴此,供参阅)
一、从一个荒诞的故事讲起 我国经济科学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二十一世纪?新的千年伊始,我国经济学家面临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个虚构但非荒诞的故事: 据说,有三位专家(外科医生、工程师、经济学家)在一起争论:世界上哪种职业最古老?外科医生说:由于外科医生拼接了亚当、夏娃的两根肋骨,创造了人类,从而才有了世界,因此,外科医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工程师说,在外科医生创造人类之前,还没有地球,是因为盘古开天地才有了这个地球,盘古是世界是第一个超级大工程师,因此,工程师才是最古老的职业;经济学家则说,在盘古开天地之前,存在着一个“混沌世界”,而这个“混沌世界”是经济学家制造的,因此,经济学家才是最古老的职业。 这个故事纯粹是个调侃,但调侃中却揭示了某些深刻的哲理。 究竟哪种职业最古老,不是我在此要研究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位诚实的经济学家说了个大实话,是经济学家开创了一个元古的“混沌世界”。 经济学并不是思辨之学说,而是实用之学说。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具有高效率的社会,促进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地发展,实现人类物质精神财富的丰裕和分配的公正。然而,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并非总是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它经常在制造“混沌”,有时还制造一些与经济学应有的目标相悖逆的结果。 比如,亚当·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鼓吹“三自”(自由放任、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却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财富和贫困同时积累的严重社会问题。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政府干预,缓解了商业周期,但却出现了滞胀。斯大林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但凡按这套理论体系及其斯大林模式样板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经济效率都下降了,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 二、走出“固守书本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窠臼 本文限于篇幅,不去广涉历史现象,还是分析一下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我国20多年来最伟大的事件和最壮丽的事业。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需要理论的科学指导。然而,经济理论并非处处走在改革的前面科学地指导改革,要么,是制造“混沌世界”,要么是处在被动的“应战”地位,跟在改革的实践后面“爬行”,形成“实践步步为营,理论节节败退”的局面,“实践中行得通,理论上说不通;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中行不通”的事情比比皆是,经济改革的实践反过来向经济理论提出了勇猛挑战。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传统经济理论“刚性”太强,缺乏改革实践的“弹性”,常常僵化地停留在原来的阵地上,“固守书本成一统,管它改革春与秋”。 作为一个长期从教者,我在这方面感受颇为深刻。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正当改革的早期,我在一个地区的党校作理论教员,学习对象主要是县(处)和人民公社(乡)级领导干部。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学习内容主要是经济学。但并不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研究怎样促进经济发展,而是按照上面的统一要求,学习的是政治经济学,教材还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版本。学员们说,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说“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必然灭亡”,而现实情况是“灭而不亡”;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说“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垂死性”,而现实情况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说“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而现实情况是“优而不越”。学员们反映:“我们在基层是做实际工作的,学这些与实际情况相距万里的空头理论,有什么用?”然而,意见归意见,反映归反映,学习班还是一期期照此办理,教材还是一批批照印、照发、照学。“灭而不亡”、“垂而不死”、“腐而不朽”、“优而不越”的问题,谁也解释不了。这就够混沌的了,但仍然是闭着眼睛照此办理,岂不是混之又沌、沌之又混吗! 后来,我到了大学学习和教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一点都不混沌,提出的问题既尖又锐,差不多都可以戴上“自由化”的帽子,但到考试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腐朽性”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的条条还得要背。对此,我真是感慨万千,难道我们的经济理论就这样“混沌”地指导改革吗?就这样培养改革开放事业的“混沌”人才吗?在几次学生毕业座谈会上,我说:同学们,大家毕业之后要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想真正为改革开放做出贡献,就要把在学校里、在教材里学的某些东西忘掉,忘的越干净越对社会有用。我的这个讲话同学们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过去许多年中,我们的经济理论不仅仅是在制造“混沌世界”,更有甚者,在许多问题的理论认识上头与脚是倒立着的。比如,我们曾经花了很多的精力,并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去对计划经济证实和对市场经济证伪。然而,被理论证实的却被实践证伪,被理论证伪的则被实践证实。理论上的优越性常常被实践蒙上阴影,而理论上的非优越性又往往被实践罩上光环。当然,我国确实不乏有一些先知先觉、敢于创新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理论在整体上,或者说,处于“主流”和“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我曾把此称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基本上都是落后于改革实践的。比如,早在1978年,就有经济学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但提出或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要么长期坐冷板凳,要么是受指责、受批判。记得九十年代初,有关部门编印出版了一大批批判市场经济的学习资料发到基层和学校学习。直到1992年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才扭转了乾坤。经济体制改革向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骤然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些大批判资料才不得不作纸浆,各类学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教学也才有了较大的变化。 好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的改革是以实践为主体,而不是以理论为主体,不是以“主流经济学”为主题。好在邓小平发明了“不争论”的方针,不管理论上有什么说法和争论,改革或明或暗、或快或慢,总是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进展的;好在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在实践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好在人民群众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关注的是“碗里的肉,身上的衣,家里的房子,钱包里的货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切身体会到,越是向市场靠拢,经济越活,市场上的商品越是丰富;越是向市场靠拢,人们自由选择的空间越大;越是向市场靠拢,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是提高。人们心里都明白一个道理:丰盛的餐桌,漂亮的衣服,宽敞的住房,并不是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恩赐,而是改革中放开市场的产物。 由于有了邓小平这样的大人物的首肯,因此,市场经济理论才得以堂堂正正地步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殿堂。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机制的内在情操并不高尚,自发的市场机制会伴随着一系列危害社会和他人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所有国家都要制定一大堆约束市场行为的法律法规。当我们经过十多年的艰难探索走出了“市场恐惧---市场补充---市场本位”的泥潭之后,歌颂市场经济的无比美妙的理论又铺天盖地的涌来。这究竟是矫枉过正,还是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不得而知。
三、几个现实常识性问题的辨析 这些问题,应该说,现在从整体上基本上解决了。由于我们在思想方法上未能深刻从理性上认识这一问题,在许多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又总是时不时涌现出一些“混沌”来。此举几例: 关于如何看待我国不断深化改革中的“旧体制”。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改什么?这当然非常清楚,是改我国的旧体制。但现在一说旧体制,总是“混沌”地说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旧体制。是不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我国改革的对象都还是二十一年前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呢?那就不一定正确了。诚然,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旧体制,是我们改革的基本对象。但如果把旧体制统统都理解为二十年前的旧体制,就会使我国的计划经济旧体制永远成为没完没了的体制存量了,这也就否定了我国改革开放二十一年来的伟大成就。实际上,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连续性的“破旧立新”过程中,每一时点建立的新体制因素,也都存在着对这种“新体制”不断检验的过程。这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就会继续保存和积累下来;第二种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马上就会成为新的改革对象;第三种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了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后来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素,客观上要求再革除这种“新体制”因素。我们把后两种情况叫做“过渡性体制”和“过渡性症状”,如“拨改贷”、“分灶吃饭”、“双轨制”、“审批经济”、“诸侯经济”、“地方保护”、“内部人控制”等等。实际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和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旧体制”分为两个亚类:一个是“旧的旧体制”,既改革开放之前所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新的旧体制”,既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过渡性体制”和“过渡性症状”。这样,改革过程中的“破旧”,就包括破“旧的旧体制”和“新的旧体制”两种情况。随着改革时间的延续和改革程度的加深,“旧的旧体制”逐步减少了,而许多改革对象则是“新的旧体制”。因此,当改革开放有了二十年的经历和经验之后,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研究当前和今后需要深化改革的任务,哪一些属于“旧的旧体制”,哪一些属于“新的旧体制”,探索这两种旧体制的内在结构和特征,以便用不同的方式、举措和途径推进改革。 关于如何看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体制和政策效果,是以“公平”为核心的,而这一点正好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民意识相吻合。这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果,即低效率,从而造成长期贫穷。低效率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更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自改革伊始,我们就坚决地贯彻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市场经济和竞争是激发活力、提高效率的根本性制度和强大机制,因此,我们的政府坚决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推进了竞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很好的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实践证明,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经过二十一年的改革,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还是一般性地、笼统地讲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就未免“混沌”了。世界上市场经济比较发展和法制比较成熟的国家,市场与政府的基本分工是: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我国经过二十一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和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初步形成,竞争的强大机制已经较为广泛的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社会公平问题则日益凸现在我们面前,当前,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公平和与公平有关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到了新的世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就应该及时的加以调整,各自的正常分工就要逐步归位,政府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平、公正、法制、道德、宏观调控、社会秩序和稳定方面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就要及时向“市场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过渡。 关于“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自1996年之后,我国逐步走出“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进入相对“过剩经济”和“买方市场”,国内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为了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提出了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则是一个“混沌”的概念。因为作为政府来说,宏观经济调控永远是积极对应经济形势变化的,其基本对应方式是“逆对风向”行事,即经济“热”时政策要“冷”,经济“冷”时”政策要“热”。宏观经济政策的“热”与“冷”是由“松”(即扩张)与“紧”(即紧缩)的政策手段体现出来的。经济政策本身无所“积极”与“消极”之分,不能把“松”的经济政策看作是“积极”的经济政策,而把“紧”的政策看作是“消极”的经济政策。所谓“积极”与“消极”,是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的:一是政策的灵敏度,是灵活对应,还是僵化赶不上趟;二是政策的实施效果,是达到预期目标,还是带来负面影响。“松”的(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目的是剌激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其负面影响则经常是通货膨胀;“紧”的(紧缩性的)经济政策,目的是抑制通货膨胀,其负面影响则经常是经济停滞。任何国家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推行“消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政府近两年所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典型的、力度很大的扩张性政策,并且已经初步取得了积极效果。但如果把这叫做“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么,如果将来有哪一天,我国出现了通货膨胀,需要实行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我们称之为“消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行吗? 关于“通货紧缩”和“三惜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丰裕和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之“通胀”退位,今日之“通紧”登台。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经济学家都适时转轨,从过去的抑制通货膨胀、压缩需求为主,转向治理通货紧缩、刺激需求和增加就业岗位为主。但在研究“通货紧缩”问题中,又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消极和悲观情绪,并存在着某些片面的和偏颇的分析。例如,有的同志把银行“惜贷”、企业“惜投”、消费者“惜购”,看作是形成“通货紧缩”的、对我国经济绝对有害的主要表现。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免有点“混沌”。诚然,“三惜”现象确实影响了经济的景气,但如同硬币有两面一样,“三惜”的形成也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是改革深化、体制进步和市场主体行为理性化的表现:首先,银行“惜贷”是银行行为理性化的表现,是我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金融监督增强的必然结果。随着银行体制改革市场化、企业化方向的强化,其预算也越来越硬化,监督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放贷的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必然会把提高银行借贷的效果和资产质量作为首要目标。其次,企业“惜投”是企业行为理性化的表现,是企业预算硬化的必然结果。民有企业预算最硬,因而最惜投资;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预算最软,最不惜投资。“惜投”现象的产生,一是表明民有企业增加了;二是表明经过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的预算越来越硬化了,因而投资行为理性化了。国有企业“惜投”表明国企投资从过去的“不负责任”过渡到了“负责任”,从过去的只负盈不负亏过渡到既负盈又负亏,这有利于企业的投资效果和资本形成质量。再次,消费者“惜购”是消费者支出理性化的表现,是消费者理性预期增强的必然结果。过去如家庭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主要由国家长期包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则逐步向家庭和个人转移,大大增大了个人和家庭的支出量,这必然使各个家庭要增加未来支出准备,提高储蓄倾向。这些都表明市场机制的约束–––无论是对银行、企业和个人的约束都越来越大,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三惜”现象的产生,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财务约束硬化的表现,而财务约束的硬化,正是我们的改革所追求的体制目标。因此,我觉得,对“三惜”现象应该少进行片面指责,多进行客观分析,由此寻找进一步深化改革新的切入点。 关于“第一生产力”的思考。当今时代,在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科技因素的份量越来越重。邓小平充分注意到这一情况,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是否深入论证过,科学技术是否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自发地成为第一生产力?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科学技术未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在当代世界上,同样一套高科技的现代化设备,安装在A国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安装在B国则可能是低效率、低质量的生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引进先进设备低效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例如,日本是从“明治维新”逐步走上强国之路的,而“明治维新”并不是科技维新,而是制度维新。战后西德经济的快速繁荣,首先不是来自科技的繁荣,用西德经济起飞之父艾哈德的话说,是“来自竞争的繁荣”。再例如,中国广大的农村,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仅仅一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上例证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比科学技术更为重要的因素–––制度。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发明,还是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从而使它转化和成长为现实的生产力,都需要一个与其相啮合的条件和基础,需要一个内在机制,需要一个“托”,需要一个“总阀门”。这个条件、这个基础、这个机制、这个“托”、这个“总阀门”,就是制度。历史的、现实的大量事实证明,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生产力发展潜在的和必要的条件,制度才是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实现生产力长期提高的充分条件。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石,是最基本层次的、最核心的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总“阀门”。科学技术,只有在相应的高效率制度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现实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以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存在为基础的;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以中国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为前提的。离开了这个制度基础与前提,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就无从谈起。经济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去直接研究科学技术,而是要深入探索和鼎力创造一个科学技术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和环境。 以上几个例证,看起来似乎只是概念辨析,但实际上都是经济学中“混沌”现象的要素,而这种经济学“混沌”现象的要素不胜枚举。我这里把走出“混沌”看作是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不是太过了。经济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科学,来不得半点“混沌”,经济学家理应把此看得过一些、重一些。话题再回到前面的调侃故事,在“元古时代”,“经济学家”曾经制造了一个“混沌世界”,当我们步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再不能制造一个新的“混沌世界”。 [1]写于1999年11月10日,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