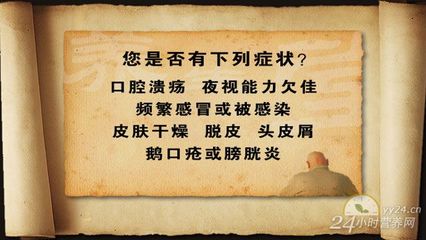一、《圣经》的启示
《圣经》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起初,《圣经》的《旧约》和《新约》分别是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成的。进入中世纪后,罗马教廷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拉丁文是当时欧洲的官方语言,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才会使用。由于教育水平的局限,为了领会上帝的福音,广大教徒必须服从受过教育的传教士对《圣经》的解读。教徒接近传教士,传教士接近上帝,教廷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了自己的控制力。进入16世纪之后,赖于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传播和一些学者的努力,《圣经》被翻译成英文。著名宗教改革人士马丁·路德甚至亲自翻译了德文版《圣经》。当《圣经》被翻译成多种普遍的语言时,广大教徒可以通过自己学习《圣经》来获取进入天堂的钥匙,教会再也无法把守天堂的大门了。
《圣经》的传播过程和现代科学的传播过程在很多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教徒而言,《圣经》就是最权威的教材,传教士就是解读《圣经》的教师,教廷就是学习《圣经》的学校。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中世纪乃至今天,相当多科学成就都是由信仰基督教的科学家发现的。回顾和展望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传播,我们也许可以从《圣经》的传播及其与科学发展的关系中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
二、权威教材的好处
现代经济学在新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大概始于1995年。经由邹恒甫教授和林毅夫教授等人在大江南北的努力,中国经济学子开始接触到北美名牌大学经济系使用的原版权威经济学教科书。与此同时,梁晶工作室也引介了一批翻译的英文权威教材。在此之前,我们只能通过国内学者编撰的教材,例如高鸿业先生的《西方经济学》,了解现代经济学的梗概。如果说国内版的经济学教材有利于本土学生打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大门,那么翻译版和原版教材更有利于将学生引入这座殿堂的深处。
不到十年时间,以Mas-Colell、Whinston和Green(简称MWG)的《微观经济理论》(Microeconomic Theory)为代表的原版经济学教材风靡大陆,一时竟洛阳纸贵。时至今日,学生之间聊起学习经济学的情况,几乎言必谈MWG!流行的东西总有它的道理。归纳起来,我们使用权威经济学教材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准确。权威教材之所以权威,是因为撰写教材的作者本身就是权威学者,从而教材的内容能够保证准确到位。例如,《微观经济理论》的作者之一Andreu Mas-Colell教授本人就是一般均衡理论和博弈论等领域的一流专家,因此他领衔撰写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肯定具有一流的水平,不会在基本原理的阐释和证明上出现错误。特别是对于某些存在一定争议的理论,权威学者的解释往往具有廓清迷雾的指导作用。此外,权威学者往往身在名牌院校,而名牌院校拥有一流的学生。权威教材在正式出版之前,往往先由权威学者在各个名牌大学的课堂上试用。有那些一流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听众,相信绝大多数纰漏和错误都能解决掉。
第二,完整。作为一本好的教材,通常应该具有统一的分析框架,前后连贯的内容,并且附带足够的教学辅导材料,比如习题和幻灯片。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材做到这些比较容易,但是专业课教材要做到这些却很难。囿于水平,国内学者编写的专业课教材,很容易陷入“综述”的套路。国外权威的专业课教材由本领域权威的学者撰写,他们熟悉相关文献,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统一模型的能力。Jean Tirole教授撰写的《产业组织理论》(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就是一个典范。不是简单地将“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堆砌成“产业经济学”,Tirole教授应用博弈论框架将产业组织的内容完美地串连起来,从垄断到竞争,从静态到动态,从完全信息到不完全信息,从短期到长期,循序渐进,深入浅出,融会贯通,这才是真正的教材。此外,好的教材还应该有足够的习题以及答案。就我个人学习经济学的体会而言,如果只听讲而不做习题,那么学习效果最多能达到理想效果的三分之一。
第三,前沿。通常认为,教材是相对成熟的内容,因此不太可能包括前沿的内容,但这要看怎么理解“前沿”。就了解前沿的专题而言,我认为不少权威教材已经努力做到这步了。不必说新问世的专业课教材会涉猎一些前沿主题,更不必说一些教材使用了大量尚未发表的工作论文,就连“经济学原理”这样的通识教材都会根据流行的内容进行修订。例如,Bolton和Dewatripont 合著的《契约理论》(Contract Theory)就不仅包含了从完全契约到不完全契约的内容,而且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动态契约理论。相对于同类教材,这本《契约理论》已经接触了当前该领域研究的很多前沿主题。特别考虑到国内学生仍然停留在研习静态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模型的层次上,这本教材介绍的动态契约理论尤其值得重视。
第四,赶超。我认为这是权威教材对中国经济学进步的最大好处。考虑到实际情况,在通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道路上,真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今天的经济学教师,在数学、英文和专业文献方面未必就比学生强。因此,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师资时,不妨先将一些前沿课程开设起来,让老师和学生一起学习国外权威教材,甚至可以让学生在老师的鼓励下先行一步。我相信,这肯定比没有前沿课程要强一些。作为老师,如果我自己不懂,我绝对不会阻碍学生先懂。这既是中国本土经济学教师的悲哀,也是他(我)们的历史使命。因此,借助权威教材,实行一定程度的赶超战略,有利于推进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进步。
三、权威教材的弊端
“凡事有利就有弊”,这是废话,但如何权衡利弊却不是废话,而是经济学的精髓。作为一个曾经的学生和现在的教师,我有幸经历了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转轨,同时也感受到了权威教材内在的不足。权威教材在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同时,也可能破坏学生的创造力。下面谈谈我对权威教材弊端的认识,愿与所有处于教学一线的经济学教师切磋。
弊端之一,权威教材容易忽视有潜力的理论。一个学者是权威,并不代表这个学者知识面就一定很广,也不代表这个学者研究的内容就一定最正确或者最具解释力,因为权威的作者也有自己的内容偏好。因此,由权威学者撰写的权威教材也可能忽视了一些很有研究前景但是不受重视的“非主流”内容。但是,今天的“非主流”可能就是明天的“主流”。我2006年留校任教后,教授本科生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导论”以及研究生的“契约理论”这两门内容相关但层次不同的课程,因此就以契约理论为例。几乎所有的权威教材都认为,道德风险模型分析的关键是“激励”和“保险”之间的权衡取舍。但是Robert Gibbons教授却坚持认为,绩效评价的不完美证实才是现实组织中的难题。Avinash Dixit也同意这才应该是道德风险的基本问题。[①] 两位教授也都是组织理论的权威学者,都在顶尖的大学任教,因此他们的观点不可小觑。大学本科毕业那年,我曾在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短暂工作,以我个人有限的经验来判断,我会认为现实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或者偷懒问题,主要还是源于绩效考核指标的证实问题,与理论上所谓的“风险态度”关系不大。随便找一个人力资源部门的管理者问一下,如果说无法观察的个人风险态度是决定报酬的重要因素,那恐怕会贻笑大方。[②] 对于高层管理者而言,特别是非业务部门的高管而言,很难找到真正客观的绩效评价指标。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大到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问题就更加明显。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主观绩效评价问题。
假如Gibbons教授的判断是对的,那么权威教材在这个问题上就误导了学生。即便Gibbons教授的观点和主流观点不是完全冲突的,让学生了解一些多元化的理论也是有所裨益的。但是,作为一本权威的教材,在篇幅上、逻辑上都不可能完全容忍那些非主流和异端的观点。没有一流教师的指导,没有广泛的文献阅读,没有清晰的辨别力,学生难免在学习中因循守旧,甚至迷失方向。由于权威教材的光环,即便学生怀疑主流观点的解释力,可能也缺乏质疑权威教材的勇气和能力。说句玩笑话,“研究什么就喜欢上什么”的现象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一旦对权威教材有了路径依赖,想跳出经典或主流理论的窠臼进行创新,可谓难于上青天。
弊端之二,过于成熟的内容让学生永远被动。打个比方,面对一块璞玉,艺人可以对它精雕细凿,创作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但是如果面对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再高明的艺人恐怕也只能望玉兴叹,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创作空间。更因为完美的艺术品让你应接不暇,最终你就疲于审美,连创作的欲望也会泯灭。因此,真正高明的艺人不会停留在对完美作品的欣赏上,而是去探求完美作品的创作过程,通过重构来学习创作的灵感、源泉和技术。权威教材的理论就好比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一个理论能够写进教材,说明这个理论已经比较成熟了,并且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但是也意味着这个理论已经没有创新的空间了。你可以学习它,模仿它,但是却不可能超越它。如果要继续发掘其价值,或者通过它创作出新的理论,就必须像重构艺术品一样,对权威理论追根溯源,阅读权威理论诞生过程中的诸多原始论文,这样才可能发现新的研究线索。
还是以契约理论为例吧。我们今天看到的权威教科书上的道德风险模型是非常标准化的,一个委托人的目标函数,加上代理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求解的方法是借助拉格朗日方程或库恩-塔克定理的一阶条件。但是,早期的道德风险模型比较复杂,也不精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在1975年的一篇未发表的手稿中指出,当时的道德风险模型可能无法使用一阶条件求解。[③] 幸运的是,Sanford Grossman教授和Oliver Hart教授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将效用函数设置为努力成本可分离的,并且要求努力的分布函数是凸的。[④] 今天,一些权威教材在介绍道德风险模型时通常不会对一阶方法的适用性加以说明,学生当然也不会有所怀疑。但是,假如效用函数不是加性可分离的,或者努力的概率不服从凸分布,我们是否有可能探索出新的解法呢?当我们的学生捧着权威教科书,踏着阳光大道走向科学的光明顶时,不要忘记,那些被湮没的山间小路也可能是通往光明顶的终南捷径。
弊端之三,权威教材缺乏联系中国的案例。我们说的权威教材是指由权威学者撰写、为北美名牌院校所使用的主要教材。问题是,权威人士未必关注中国问题。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因此作为最大和最复杂的经济,中国理应为经济学贡献理论源泉和应用场景。在这点上,我赞同林毅夫教授的看法。权威的经济学家通常出生、成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于像中国、印度这样巨大的转型经济和欠发达经济缺乏深入了解。毫不奇怪,我们看到纯理论的经济学模型越做越复杂,也越做越精细,因为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能够提供的学术营养是边际收益递减的。反观中国这样的大国,面对如此难得的人类实验,我们却常常浑然不觉,真有点“坐在金矿上找金子”的感觉。
以新制度经济学(NIE)为例,它在欧美肯定不是主流,因为制度变迁不是欧美面临的主要问题,但它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当1990年代初期NIE引入中国时,立即在中国经济学界和其他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产生了广泛的应用。如果认为权威教材很少涉及NIE(科斯定理除外),就认为NIE不重要,没有研究前途,从而老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那么我们很可能错过了中华民族赋予我们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也会与理论创新的良好机遇失之交臂。
四、我们的努力
现在回到开头提及的有趣现象。为什么信仰基督教的科学家有激励从事科学研究呢?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不管是在政教分离之前还是之后,教廷的权威都是有界的。教皇只能对《圣经》的内容进行权威解读,但无权干涉《圣经》之外的内容。正是利用这种权威教科书之外的不确定性,宗教庇护下的科学才能与宗教“水火”相容。这告诉我们,如果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我们就必须在利用权威教科书的优势的同时,摆脱权威教科书的束缚,为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一种不确定的环境。我不是要刻意批评和挑剔权威教材,而是希望国内经济学教育不要顾此失彼。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尚需时日。
为了避免权威教材对有潜力的理论的忽视,欧美名牌院校通常举办大量的研讨会,让许多知名学者或者青年学者来介绍他们的前沿工作。经济系的博士生在通过资格考试之后,要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参加各种Seminar。权威教材就好比主食,研讨会的工作论文就好比粗粮。没有主食会吃不饱,但是没有粗粮就会营养不全。此外,一流经济系的导师通常是本领域的学术权威,因此对于相关理论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知道什么值得做,什么不该做,这就避免了学生对成熟理论产生审美疲劳。但是很遗憾,我们国内的高校基本上不具备这些条件。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第一,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让学生尽可能吃透教材,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特别要强调做习题,讲习题,否则学生很容易犯夸夸其谈的毛病。第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让学生多了解一些本领域的工作论文,知道前沿的问题是什么。有时候,与其让学生从经典论文去找研究脉络,不如让学生反过来从前沿论文往回找,这样方向更明确,发现好问题的概率可能更大。第三,要充分利用读书会。要让老师在课堂上详细地回顾一个成熟理论的所有经典文献是不太现实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让学生组成课外读书会,利用课余时间讨论一些经典文献,了解理论模型的发展过程,试图发现一些被遗漏的“蛛丝马迹”,说不定就那些就是新理论发展的线索。第四,鼓励学生与海外学者开展国际合作。据我所知,很多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的转型和制度变迁非常感兴趣,他们也非常关心其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和拓展。我们的学生有可能通过国际会议或者互联网与海外学者合作,逐步提升中国问题的重要性,进而对现代经济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当老师的必须不懈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总之,任重道远。
《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1辑(总第33辑)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感谢shenji和江艇为本文提供了专业的评论。
[①] 参考Gibbons, Robert, 1998, “Incentives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4): 115-132以及Dixit, Avinash, 2004, Lawlessness and Economics: Alternative Modes of Governa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分析,涉及农业契约与公司契约的环境差异和激励工具差异,因为太专业了,此处略去。
[③] 这篇文章在20多年后终于正式发表了,参考Mirrlees, James, 1999, “Theory of Moral Hazard and Unobservable Behavior: Part I”,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 3-22.
[④] 参考Grossman, S. and O. Hart, 1983,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Econometrica, 51(1): 7-45.

供稿:白鲨在线_聂辉华官方网站_契约与组织理论学习平台niehuihua.com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