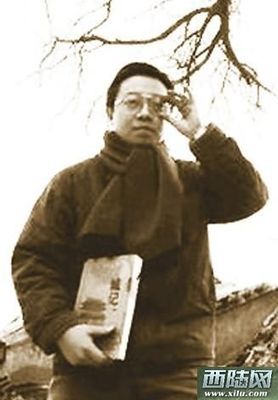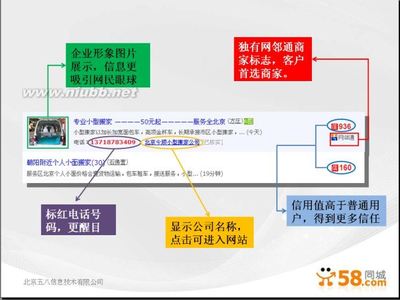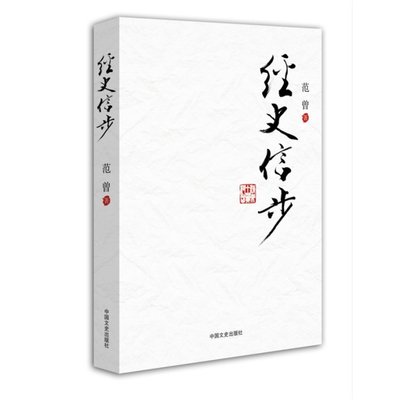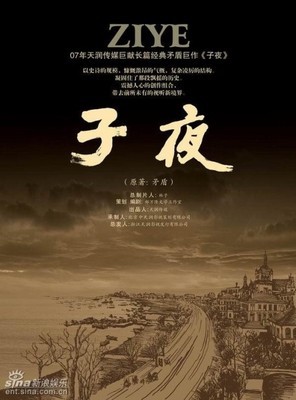从诸暨的枫桥翻过一座“虎扑岭”,便来到书法圣地兰亭。王羲之《兰亭序》中的“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得到了印证。 我第一次去绍兴,大概是1973年,只是路过兰亭,从公交车里远远望去,只隐隐约约看到在竹林之中有蓝色亭子,虽然亭子有翘角,但是隐在竹林之中,显得沉静而庄重。如果这个亭子建在高岗上,便会“有亭翼然”,好像要飞起来的味道,极适合魏晋时期的那种思想和文化的飘逸及逍遥。 1987年我在诸暨县委宣传部任职后,才有机会陪同外来的客人到兰亭。不过那时的兰亭还较为简陋和幽静,兰亭、竹林、鹅池、曲水,以及临水相伴的陋石,我总以为那种气氛才适宜于喝酒、吟诗,放荡不羁,如果像如今这般的商业氛围,大概当时的王羲之们是不可能撰写得出“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种清澈亮丽的语言和骈文的。后来,又去过几次兰亭。我们的一些景点,老是画蛇添足,灯红酒绿,断绝了游者的联想空间,是不是应当记取古人的逸趣呢? 一篇《兰亭序》,可以说是历朝历代书法的高峰。在我同一些书法家的交谈中,对《兰亭序》中的书法之华美灵性、章法参落高格、布局洒脱秀逸是一致推崇的。“书法称绝于世,秀逸清朗,洒脱到了极致。一点一划尽现晋人风神,通篇笔墨清爽伶俐,雍容典雅;体态闲雅超逸;章法尤其绝伦,字与字之间毫无牵连,却又倚侧多姿,顾盼生情,一气呵成之痛快淋漓尽现其间,真是妙不可言!”我以为,这样的艺术神品,得益于当时远离朝廷的绍兴兰亭之小气候,得益于“暮春之初,群贤毕至,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绍兴兰亭之小环境,得益于用鉴湖水酿造的绍兴老酒为之推波助澜。崇山峻岭,远离宫廷可以敞开思想;天高气爽,同好论道可以尽情抒怀;临流唱饮,似醉非醉才可以走笔龙蛇。当时盛名的竹林七贤,在河南山阳的竹林之中,也没有写出流传千古的作品。所以,我一直认为,有绍兴,才有《兰亭序》。 一篇《兰亭序》,是当时文人思想的高峰。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是典型的动乱文人思想。政治家们打来杀去近三百年,文人们要适应战乱,适应朝代更迭。他们在战乱中感受到人生的短暂,生命渺茫,世事难以预测,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人思想的消极色彩,从而沉迷声色。这种思想的消极色彩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比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是,在《兰亭序》中,一反魏晋文风,“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完全背离了汉代独尊儒术的正统思想,追求与天地、宇宙、大自然为一体的积极自由的灵魂空间,文人的思想达到了另外一种高度。 一篇《兰亭序》,也是当时地域性文学作品的相对高峰。综观全篇,文章朗朗上口,韵味非常。像“惠风和畅”“群贤毕至”等,是经常用来装点门面和书房的,篇中修辞上追求华丽完美,声律、用典、排比尤其出彩。且文章洞察时空,比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作者不但抒发了对生命短暂的叹息,而且又表现出了作者寄生命与文学艺术,以无限的不朽艺术替代有限的自然生命,真可谓“诗酒岁年,山河大地”,八千岁为春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