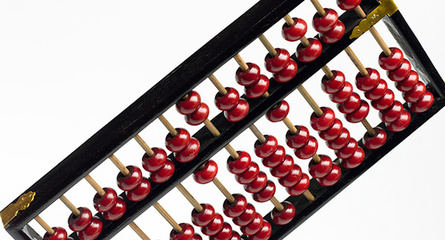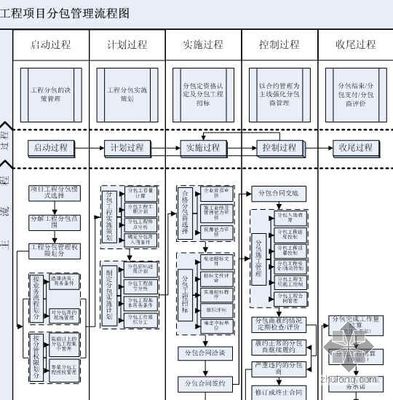通常来说,农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一方面,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有着较强的依赖性,而受制于技术条件的自然条件又变化莫测;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及农产品产量和价格决定的“蛛网”特点,进一步强化了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由此,农业成为弱质产业。农业生产经营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民对风险的高度敏感性。
在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减弱了市场不确定性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农业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稳定性,其间自然成长起一系列应对自然风险的技术安排和制度安排。前者如土地的分散经营,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及间种、套种的选择等;后者如公用土地制度、互惠制度、保护人—被保护人制度等。在斯科特对上个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国家农民行为的研究中①,市场化成为传统农村社会风险化解和生存保障机制的瓦解力量,从而成为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重要来源。由于市场化的深入,农业生产的生存伦理让位于利润伦理。为实现规模经济,土地分散经营被集中的大规模种植所取代;具有重要的化解风险功能的多样化种植及间种、套种被单一品种种植和标准化经营所取代。公地已经被圈为私地,互惠已经让位于互相利用,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也演变为金钱利益关系。在自然的暴虐面前无能为力的农民完全暴露在市场风暴之中,更加无能为力,更加如履薄冰。斯科特对市场化初期的东南亚农业研究的结论是,市场强化了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加剧了农村的分化,将广大农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斯科特的研究中,市场化似乎是一个恶魔。正是市场冲击,撕裂了传统农村自然形成的社会保障体系,割断了人与人之间基于传统的天然联结;也正是市场冲击,农民被挟裹进商品洪流,被抛入无边而诡异的风险之中。从此,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失去了基本保障,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市场的淫威下挣扎。撇开斯科特研究的特殊背景而言,对市场与风险关系的这种简单化判断显得有失偏颇。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这种必然性源于人类欲望的自然成长。如果人类欲望停留在基本需求上,农业就将成为唯一的产业,也就不存在工业化和市场化。但是,人的欲望在自然成长,工业化和市场化也因为服从和满足人的欲望的成长而具有进步意义。因此,即使市场化果然强化了农业经营风险,果然使农民在转型阶段陷入水深火热,也只能将其理解为社会进步的代价。
况且,市场化也不仅仅意味着风险,在一定意义上,市场化本身也蕴含着化解风险的机制和力量。风险固然是不确定性的表现,而市场,由于聚合着无数随机决策的人们的无数随机决策,同传统社会相比,会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更多更广影响更深远的不确定性。但是,市场毕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而且,在市场作用之下,借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为人们提供了决策的纠错机制。于是,市场使人们可以不被最初的选择所套牢。当然,选择不仅意味着对影响决策的各种参数的取舍,也意味着对决策的各种可能结果的筹划。在人们经济行为的整个过程中,人们都可以适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当然,市场本身就意味着更普遍更深刻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于市场背景下人们更加灵活多变的欲求以及更加丰富多样的策略行为),市场的纠错机制及人们基于市场的行为调适既不可能消除不确定性也不可能消除风险,但是,市场的灵活性却可能使风险的分解成为可能。由此,市场提供的选择性成为化解风险的一种机制或力量。
具备化解风险功能的市场其实只能是理想的完全市场,如众多的交易参与者从而无论买方还是卖方都无力操纵需求和供给;交易参与者具有完全充分的信息从而任何参与者都无法利用信息优势获取利益;资源具有充分的流动性从而不存在影响交易效率的交易成本;……但是,现实的市场并不具备理想的充分性。或者说,不同的市场具有不同的完全程度——这既取决于市场的成长历史,也取决于市场的技术和制度特点。市场的不完全程度越高,其所提供的选择性越低,其风险也就越大或者说利用其化解风险的成本就越高。在农业生产中,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对市场具有不同的依存度,从而面临不同的市场风险。而不同市场不同的完全程度又进一步影响交易参与者面临的风险,从而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结构的重要因素。
据笔者暑期在云南省东南部山区村落岩村的调查,市场的不完全程度对农民的种植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市场面临较大风险时,农民可能选择风险程度相对较低从而收益也相对较低的生产结构。岩村的主要的生产物是玉米和烟叶。按中等水平计算,种植玉米每亩收益600元左右,加上套种瓜豆,合计收益1000元左右;而栽植烟叶的收益在1800左右。栽植烟叶平均每亩比种植玉米加瓜豆可以多出800元左右。但是,在全村139户中,仅有40来户栽植烟叶。总的来看,尽管烟叶栽植有着较高的收益,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并没有充分的积极性。
按照目前的生产经营体制,烟叶栽植由烟草公司驻各乡的烟草站(或者委托乡供销社)规划组织,首先制定乡一级的生产计划,再分解到各村组。烟草站或者供销社根据规划向栽植户统一提供烟苗,统一组织初烤,并统一评级定价。纳入计划的农户才能栽植烟叶,并接受随后的生产服务,最后按照协议向烟草站或者供销社出售烤烟。烤烟是云南重要的财政来源,各级政府对烤烟栽植都高度重视。烟草公司为了保证优质烟叶的供应,也在生产各环节进行了大量投入。比如,在岩村所属区域,烟草公司在适于栽植烟叶的地块出资建造水窖,每座水窖投资2500元。在栽植和初烤环节,烟草公司还在各村安排具备相应技术的烤烟辅导员提供技术支持。农民栽植烟叶的成本由此降低,收益由此提高。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农户对栽植烟叶并不踊跃。

根据笔者入户调查了解的情况,部分农户对栽植烟叶持谨慎和消极态度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对于玉米种植,烟叶栽植要求的劳动投入过大;另一方面,相对于玉米生产,烟叶生产面临更大的风险。
相对于玉米生产,烟叶生产的环节更细,而且各环节都需要更为精细的管理,从而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虽然目前烟草公司帮助建立水窖大大节省了浇水环节的劳动投入,烤烟辅导员的技术援助也大大提高了烟叶生产的效率,但是,对于那些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而留守劳动力主要是老人和妇女儿童的家庭而言,烤烟所要求的劳动突入仍然难以应付。
烟叶生产相对玉米生产的更高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个与技术结构有关,另外一个与市场结构有关。烟叶生产和玉米生产面临的自然环境一样,从而所面临的自然风险没有太大区别。区别在于生产的技术结构。就玉米生产而言,即使栽种环节气候异常,但由于可以套种和间种黄瓜、南瓜、红豆、绿豆等辅助作物,主要作物生产的风险可以得到化解。而烟叶栽植所要求的环境较为苛刻,一般不宜套种和间种。由此,烟叶生产比玉米种植面临较大的风险。
烟叶生产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市场结构,来自具有垄断性质的烤烟收购环节。按照现行烤烟政策,烤烟必须严格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在当地交售,跨区运销被视为走私而受到严厉打击。烟叶种植户一旦签订合同进入烟叶生产环节,就陷入垄断陷阱之中。即使现行政策对保护烟农利益有着详细的措施,但对于在交售环节缺乏讨价还价能力,缺乏用脚投票机会的农民来说,进入就意味着套牢。况且,鉴于烟草公司与收购人员之间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被套牢而失去抵抗能力的烟农最有可能成为被敲竹杠的对象。在国家烟草收购政策中,为不同质量烟叶规定了详细的等级及相应收购价位,但不同等级之间的价差仍然很大。如一价区中级烟的最高等级与最低等级之间收购价每百公斤相差达900元。即使相邻两个等级,价差也可能很大。如X1L和X2L之间相差200元,B3F和B4F之间相差330元。现行的烟叶评级,采用的是人工方式,即使对烟叶质量与等级评定有着详尽的技术标准和要求,仍不免主观性。利益驱动之下,加之缺乏有效的内部约束,收购人员往往通过操纵评级谋取私利。有经验有关系有势力的“强势”烤烟户可以一定程度上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没经验没关系没势力的“弱势”烤烟户则只能任人宰割。于是,垄断的市场结构及收购人员对评级定价的操纵成为烟叶栽植户面临的最大风险。对于那些“弱势”农户来说,放弃成为一种选择。
市场的介入总是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增强,意味着风险的增加。根据斯科特的考察,市场不仅强化了不确定性,增加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而且,由于市场化破坏了传统社会化解风险和保障生存的机制,因而成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农业生产及农民生存面临的最大风险的来源。但是,市场本身既是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场所,也是人们实现选择的一种有效机制。如果市场具有充分的完全性,人们通过市场提供的纠错机制和选择机制,可以使风险的化解成为可能。不过,现实的市场并不具有完全性。在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在存在市场垄断的背景下,市场的风险化解功能必然受到损害。岩村部分农民选择回避烟叶生产,其实不是在回避市场,而是在回避由于市场垄断而增加的风险。
农业生产经营风险,既可以来自市场化,也可以来自市场化的不深入。如果市场化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那么,市场的深化应该成为化解风险的一种选择。
附:该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10月10日
①参见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