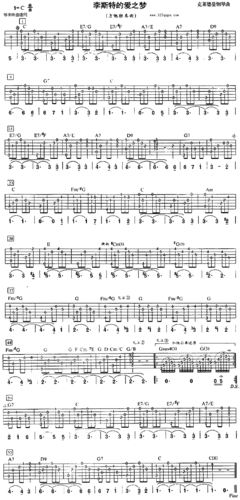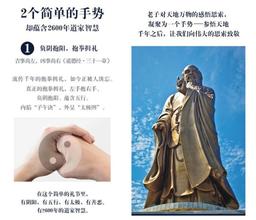迷笛音乐节首次登陆深圳 青春、躁动、活力、荷尔蒙、反叛、疯狂……代表着人们对摇滚乐迷根深蒂固的印象,都能在今年首度登陆深圳的迷笛音乐节上见到。5月17-19日,音乐节入场人次近10万,大多是脸上洋溢着激动表情的年轻人。在重金属的催动下,现场经常性地陷入集体的狂欢。尤其是入夜后,在专门演唱摇滚的“唐舞台”前,几乎每一首歌都能引起全场躁动。在第二日夜晚,“痛仰”乐队压轴表演时,几百人一起在台下“开火车”向前跳跃;陌生人被抬起,在空中接力。如果不是台上仍有乐手唱着歌,这样的情景倒更像是集体骚动,而非音乐节。 这样的场景,会令一些老摇滚乐迷想起1986年,崔健唱着《一无所有》的年代。随后几年,中国摇滚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至今的摇滚论坛上,仍不时可见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乐迷的怀想。 1974年出生的高虎,就是在这一时期迷上摇滚,更因此只身到北京学习摇滚。随后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却是另一番景象:商业化的步伐加大,理想主义渐远,物质欲望开始膨胀。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摇滚乐却带着浓厚的“精神至上”的味道。高虎在1993年组建的这支乐队就叫做“痛苦的信仰(痛仰)”。

“摇滚是一种精神追求,如果社会在为物质生活奋斗,它当然很难被接受。”高虎称。在他进入摇滚乐坛的同时,中国人对摇滚的热度却正开始锐减,包括那些曾高唱《一无所有》的理想主义者和知识青年。“痛仰”所经历的,正是所谓的中国摇滚乐衰落期。 不过这一说法至今仍存争议。“摇滚乐一直在发展,没有衰落,但是存在一个冷静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饥渴的中国社会造就了摇滚乐坛的泡沫。泡沫破碎后,它才回复到一个冷静的生长期。”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痛仰”乐队的作品基本来源于高虎的生活体验。“从1993年到2006年,我的创作基本来自于生活,包括对社会的看法,”高虎说,“那时候没有钱,坚持做摇滚,也想过很多次自己为什么来北京。那是一些来自于底层,对这个社会的一些体验。” 这些亲历的“城市的底层体验”,触动了一些人的心声。在这一时期,尽管摇滚的商业运作还不成熟,“痛仰”也收获了稳定的听众,到2003年,“痛仰”与“夜叉”、“病蛹”等乐队渐成新一代摇滚偶像,之后“痛仰”更成为中国摇滚乐坛的领袖。可是从地下摇滚乐队聚集的树村,到后来的霍营,他们的生存状态持续低迷,被称为“穷摇一代”。“这个圈子每天都有人出出进进,成百上千。生存压力是很大的问题,最后能坚持的人不到一半。”高虎表示。 “在中国,真正的底层,一般音乐修养、教育水平不够,因而玩摇滚的人往往不是真正的底层出身。”作家周国平也对此提出过质疑,中国的底层文化不成气候,摇滚真的能够为“底层”发声? 与“痛仰”的风格截然不同,目前人气极旺的“逃跑计划”是2004年才成立的摇滚乐队。由于主唱毛川及其他乐队成员,全都是名副其实的“北漂”,因而理想、思乡、孤独等“北漂”的困惑,成为他们创作素材的重要组成。 相比“穷摇一代”,“逃跑计划”要幸运得多。2008年起,中国摇滚逐步走向成熟的商业化。经过十多年的表面安静,摇滚乐的受众群体像是一夜壮大。“其实并非是‘复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摇滚听众有限,产业有限,乐队数量有限,经过20多年发展,现在全国有上千支摇滚乐队,摇滚产值远远大于20年前,受众群的组成也更丰富,数量远远高出从前。”张帆告诉记者,“周晓鸥在《我是歌手》里说自己要为摇滚留一个位置,我觉得摇滚乐不需要通过选秀节目留自己的位置。它早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同样是在2008年,“痛仰”推出了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与2006年以前的作品相比,新作品的风格被认为是对早期作品的“颠覆”,音乐形式由“重型说唱”变为柔和吟唱,歌词亦没有了早期的愤怒批判,更多的则是个人思考。 中国当代摇滚乐风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底层精神”,正在随时代的流动而历经变迁。“中国摇滚在很多年里,一直接受沉重的东西,包括我们,一开始也是把它作为宣泄口。可是慢慢沉淀后,都开始找一些理性的东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