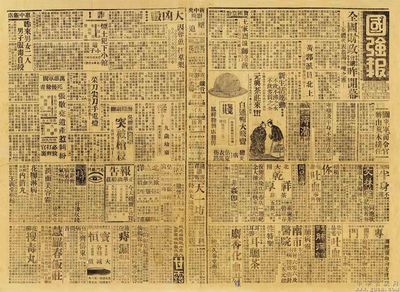本轮资本深化与90年代中后期完全不同 时代周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尽管投资率持续上升,但经济增长率却表现出了持续回落的迹象。与目前一样,当时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甚是悲观。今天的状况与当年有何区别? 张军:我觉得区别还是很大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概四五年的时间里,经济出现一定的减速。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减速可能与“资本深化”(相对于GDP的增长,投资率增长得更快,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有关。但是,2000年以后,资本深化不再像之前那么严重。事实上,投资率并没有大的改变,而经济的增速也开始回升。 个人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与发达国家很不同的现象,就是资本深化极容易在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了人均收入比较高的阶段以后,投资率已非常低,换句话说,就是投资机会非常少。可是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机会还很多,比如说基础设施,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比较短缺。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已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按照人均计算,总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资本深化是一种常态,发生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而今天这个局面,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不一样,很大程度上由2008年“四万亿”这个投资政策造成的。吴敬琏等经济学家批评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主要针对的就是2008年开始的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 如果没有外部金融危机,政府便不会过度反应。那么,中国经济自2007、2008年以来,应该不会大起大落。2007年,经济过热,包括房地产、基础设施投入等,通货膨胀开始抬头。因此,政府在2008年年初采取紧缩政策。但是到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突然决定不能再收了,应该要放,而且不是小放,是大放。因为之前一个月,美国出现了次贷危机,国务院认为次贷危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应该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提出了四万亿的政府开支规模。当然,中央政府拿出1.2万亿,其他都是地方政府出的,地方政府并没有钱,所以地方政府只能向银行举债来达到四万亿的规模。 根据审计局的审计2008-2010年,大概有十万亿的货币放出来了。这些钱要进入到经济实体,必须有一个渠道。银行的钱不是空中洒下来的,必须要以贷款的方式支持项目。要在短时间内找那么多项目,不容易,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发改委批准以往积压的大项目。大项目无来源有二,一是各级地方政府早先上报、迟迟未批的发改委投资项目,二是打着国企招牌的那些项目。而且这十万亿下去,究竟有多少投在基础设施上,与90年代中期不好比,现在看来可能是房地产以及虚拟的东西更多。 在“四万亿”政府投资政策下,实质上是鼓励了在短时间内让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大量投资项目得到发改委的批准,得到银行的贷款。于是,导致了从08年以来到今天的新一轮的资本深化。这次资本深化,与90年代中后期那次完全不一样。这完全是政府在特殊环境下使用的特殊办法。此次资本深化是典型的人为现象。需要好几年的时间,靠生产力的提高来消化掉这么多超量的货币。 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 时代周报: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你认为,这种分析模式有什么问题?中国存在过度依赖投资的问题吗? 张军:这得分短期和长期来看,现在流行的看法是把短期现象解读成长期现象,我一直不赞同。中国经济增长不是一年两年,是30年的增长,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20年增长,这是一个持续的增长。在如此长时间的增长过程中,不应该用需求来解释,需求只能解释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中长期增长是一个供给问题,应该用生产力提高来解释。 “三驾马车”理论中,总需求决定总产出的凯恩斯理论只能用于分析短期的宏观经济周期问题,而不能用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而长期增长的因素还是投入,没有投入何来增长?光有需求,没有投入是不可能增长的。所以,中长期来说,真正的增长是来自于资本形成、生产力的提高。 关于投资,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处在高速增长期,投资都是至关重要的,其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所谓投资,就是不断增加生产能力。它表现为改善基础设施,改善生产设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不但包括物资方面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也非常重要,中国政府把教育投资等计算在消费内,而不是生产投资。但它依然是一个投资。所以,如果没有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未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的。 短期内,可能会存在资本深化的现象,过几年就能消化掉。但是,如果持续过度投资,经济的持续增长便不可能。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出现持续的资本深化,这是有问题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也是这样,就是不吃饭,也要发展重化工业(剥夺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要大炮不要黄油”的经济是难以为继的。 如果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资源配置主要靠市场,哪怕在一段时间里投资增长快于GDP,出现资本深化的现象,问题也不大。因为更多的投资可能是为了将来更快的增长。中国不是发达国家,投资率不可能只有10%左右,达到40%、50%很正常,因为投资机会多。只要投资回报率没有持续恶化,还能保持相对比较快的回报率,对经济有一个向上的拉动,就说明投资还是有效率的,还是健康的。 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是一种误解 时代周报:还有一种流行观点是,中国投资过度导致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递减的规律日渐显现。因此,需要通过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或投资与消费平衡驱动)的经济转型来阻止经济增长的持续跌落。是否存在此种经济转型的可能? 张军:某些产业或者产品的产能过剩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过去20年里,几乎每年都听说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恰恰在这20年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 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是一种误解。经济增长的驱动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来就没有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现象。如果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可能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假设政府明年宣布将国民收入GDP中的消费率提高到80%,根据人均GDP计算,给每个家庭换算成一个数字,然后给老百姓发消费券,让大家消费。GDP是铁定的,消费要占到80%,投资率就要降到20%(假设贸易盈余、贸易顺差是零)。结果会是什么?商店的东西被抢光,不够,还要大量进口。这个经济在当年也许没问题,可是第二年商店里的这些东西怎么再生产出来?要增加投资不可能,GDP已经分光,一增加投资20%就突破了。一个国家经济不发达一定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不肯消费,如果消费能带来增长的话,世界上就没有穷国和穷人了。 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是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人均产出从而向发达国家靠拢的一个主要推动力,而人均产出的持续增加才是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现代增长理论表明,投资的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消费的增长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另外,把消费和投资看成是对立的,也是理论上的误解。比如,政府投资搞基础设施,可理解为是一个投资现象,可是基础设施改善了,消费自然也会增加。投资和消费并不是消长关系,而是双向关联关系。遇到经济萧条期,大家对经济没有信心,不愿意花钱,政府可以用一些政策去鼓励消费,比如对消费者进行一定的补贴、信贷上降低贷款利率等,但这并不等于消费可以驱动经济增长。用这种政策,只能在由于受到外部原因导致消费水平下降时将其拉回到正常。总体来讲,消费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现象。这就好比人要吃饭,不管吃好吃差,量还是稳定的,除非遇到胃不舒服了,需要去看病,调理一下或者吃点药把这个拉量回到正常水平。 过去二三十年的投资不是政府主导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投资在其间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张军:“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各方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比如“比较优势论”,它告诉世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因为劳动力对资本的比较优势被逐步地矫正。在计划经济时代,资本便宜、劳动力贵,政府出于保护工人的目的出资补贴资本。只有重工业才能挣钱,因此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一到市场经济,变成资本稀缺、劳动力充沛。劳动力市场定价后,也就必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再比如“市场化”也可以解释过去30年的增长,与比较优势论在逻辑上一致,一旦生产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中国这样的巨型人口国家劳动力必然便宜,资本一定会贵。也可以用“制度变化”来解释30年增长,所谓市场化就一定需要政府进行市场体制改革,不改计划体制,市场何来?所以我们就采取双轨制、增量改革这种方式让市场逐步地活起来。我曾经撰文从产权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奇迹”。因为,要素市场定价无非是把产权还给要素的所有者。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农民只能呆在原来的土地上,那么,农民工这种劳动力价格就不可能导致由市场决定的低工资。综上所述,只要逻辑上一致,以上所有这些解释角度其实是在讲同一个故事。 毋庸置疑,过去30年,投资在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不可替代的角色。经济发展,本质是个投资现象。放眼全球,将经济增长快的国家放到一起,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这些国家的储蓄率很高,这就意味着投资率很高。很多欠发达经济体,面临着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把消费率降下来,把投资率提上去。也就是说,要在为数不多的国民收入里面,要能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去做投资,去搞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阶段,基础设施要走到最前面才行。人们老拿中国和印度作比较,认为印度的“制度资产”胜过中国的“硬件”改善。但是,今天的印度,其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并不说明印度可以很快赶上中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限的根本原因也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一谈起投资,就觉得是非常坏的现象,是因为将投资理解为是由政府在主导。表面看起来,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是因为投资,而投资主要是政府在做,其实这是一个误解。30年中的历次改革,包括1993年、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1997、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这些改革都是在让市场逐步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让出更多的资源配置空间留给市场。从计划经济走到现在,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一直在不断缩小。即使在今天, 很多地方政府建立的投资平台、融资平台也是非常市场化的。没有这些平台,基础设施不可能做得那么好。所以,我认为30年的高速增长,归因于“有效投资”。如果投资在总体上是无效的,经济早就垮掉了。 时代周报:你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在你看来,在整个投资结构中,进而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政府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认为是否存在政府过度干预的问题? 张军:短期来说,在某些出现外部震荡的年份,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政府一般会用干预主义政策去干预经济。于是,在未来几年,先前过度干预经济的政策会出现负面效应,导致大量的投资浪费。但从过去20年、30年的经验来看,这不是主流。如果这个是主流,那肯定是经济学错了。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大量的投资是没有效率的,就会出现投资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投资边际报酬递减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率递减,这是解释不通的。 没有谁会相信政府投资会比市场投资更有效。但我并不认为过去20年、30年中国的投资是政府主导的,实际上它是由市场主导的。大家看到的政府主导投资的现象往往是发生在商业周期遇到下行区间,也就是出现外部震荡的时候。把出现外部危机时政府主导投资等同于过去20年、30年的投资由政府主导是错误的。 要维护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 时代周报:你曾撰文指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有经济学家则认为,分税制对经济增长作用有限,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而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你如何回应? 张军:首先得搞清楚,中国经济在1994年以前与1994年以后,其增长机制是不一样的。我是从增长机制这个角度来解释分税制的重要。1994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机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地方地政府与中央政府不一心。地方要隐瞒生产力,有很多东西不愿意让上面知道。中央政府看不到真实的生产能力,一旦发现地方漏洞,就会下力气惩治。地方跟中央之间博弈不断,后果是,94年以前,整个经济一往上加速增长就产生通货膨胀,于是,中央政府就把经济压下来,就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尽管平均增长率有9%,但增长极不稳定,增长率高的时候达到14-15% ,低的时候将至负3-4% 。这表明增长机制是有问题的,地方与中央在目标上不一致,经济学把这称为激励不兼容。 到了1994年之所以要搞分税制,就是因为朱镕基看到上述问题必须要解决,宏观经济必须要稳定,只有稳定中国经济才能有好的增长。因此,必须解决激励不兼容的问题。如何在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同时,又让中央政府摸清真实的地方经济,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让地方不再跟中央政府躲躲藏藏了。分税制的设计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制。中央拿中央的税,地方拿地方的税,地方政府不需要再给中央钱,也就没必要躲躲藏藏了。分税制度其实就是让地方政府分得经济增长的一杯羹。因为在这之前是承包制,中央是按一定的比例收多少钱,地方政府不愿意,会说我没挣那么多,没法给你那么多。有了收税疆域的划分,央地之间就不存在博弈了,宏观经济也就稳定了。自那以后,要多少货币,中央就知道了。原来是不知道,所以总是货币超发,加之中央政府手上没钱,因为下面都藏起来了。中央政府拿不到钱、征不到税,要进行宏观经济方面的管理、想拉动经济增长就很困难。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把地方跟中央的激励方向调整一致,这样也就有利于国家的整体改革。我是从这个角度上说分析分税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 时代周报:在目前财政分权的体制中,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地方政府在过去十多年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已是负债累累。如何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同时,又能够使地方政府在未来持续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张军: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还是要维护,关键是要解决融资渠道问题,有两方面工作需要做。其一,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要改革,把一些外部性比较强的公共品的供应收到中央。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通过卖地或者以其他政府基金的形式给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融资,是因为其财政支出的项目在金额上面远远大于收入。财政收入没有这么多钱,支出责任又太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地方政府现在负担的很多支出责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统统上升到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埋单。过去五年,基础教育(义务阶段教育)已上收到中央政府,接下来医疗、养老等也会同样如此,相信这是接下来改革的既定方向。如此,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现象就会大幅度地扭转,扭转以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自然就会减轻。其二,要让地方政府有发行地方债的自主权,这比向银行贷款更透明。地方政府一旦有问题,金融市场可以对其进行抨击,这样就形成金融约束,地方政府就不敢胡来。金融约束很重要,信誉差的地方政府发债就会没人要。我认为地方债的试点应逐步向全国推广。 中西部要追赶沿海,只有通过投资 时代周报:90年代后期,投资效率的恶化和资本密度的急剧上升可能与当时的鼓励基础设施和基建投资的政策有关。事实证明,进入新世纪之后没有几年,随着政策的调整,令人担忧的过度投资和增长减速问题得到了纠正,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的10年能够再续快速增长的记录。如此看来,吴敬琏等人提出不能继续过度依赖投资的观点,是否开出了避免中国经济持续回落的正确药方? 张军:如果是针对2008年以后来讲,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是对过去20年来讲,我认为是个误判。 另外,地区之间还要差别对待。过去20年来,中国基础设施的水平表现出沿海与内地之间显著的落差,尤其是中部地区的相对“落后”地位除了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之外,基本上没有改变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西部一直得到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持,而改革开放使东部更好地进入了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显著的“追赶效应”。只要中西部地区的政府继续作为,这个差距就会逐步缩小。因此,广大中西部地区不能减少投资。

时代周报:你提出,中国还有20年左右的高增长潜力。那么未来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何方?政府投资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否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张军:我觉得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来讲,投资还是第一位的。投资的规范语言是资本形成,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本形成的现象。资本形成就是形成生产能力。而技术进步是中国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处于第二位。 对发达地区而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像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几率逐步减少,不可能像90年代开发浦东时那样有20- 30%的投资增长率,能增长10%就已不错。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经济增长靠什么?只有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上海,一个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可能是中西部地区的3-4倍。所以,我们常讲,劳动力减少没关系,因为最后决定经济增长的是劳动力的素质而不是劳动力的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什么刘易斯拐点。 中国沿海和内地差别巨大,人均GDP差别两倍以上。中西部要追赶沿海,只有通过投资。而投资机会已经饱和(投资率很低)的沿海地区,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只有向高附加值产业、高端服务业进军。而这有赖于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积累。人的素质、技能提高了,所创造的财富自然就高了。 未来,政府投资的相对比重会越来越低,主要集中于公共基础设施。沿海地区已经饱和,政府投资会逐步淡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还有大量的机会搞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投资在这些地区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