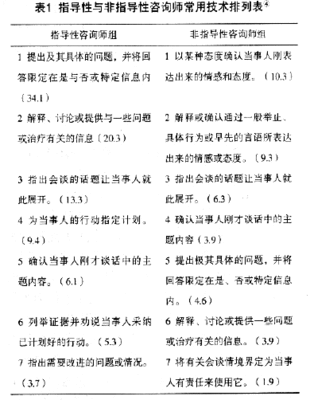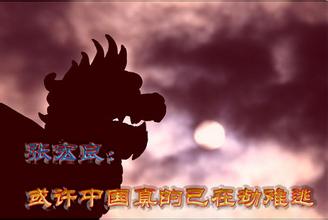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自来就是一对冤家对头,你争我夺,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实难调合。
我曾经反复论述过,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视野来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历史,是一个“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反复争斗,此消彼长,不断轮替掌控经济的历史。往往是,自由主义将经济大推进的同时,问题也积累起来,一当危机暴发,便是国家主义接管权杖的时刻。政府干预,举国抗御危机,渐渐将经济社会的大船驶出危机地带,令经济重新复苏,同时另类问题也叠加沉积,这断然成为自由主义“还乡团”的机遇。
最新的例证是:格林期潘执掌美国经济二十年,将自由主义的技能使尽。而今天的保尔森与伯南克,祭起的法宝不是别的,就是国家主义。在我看来,这是现代国家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移情别恋的新脚本。这还不是第一次它们俩这么干,自东西方经济社会形成阵营对垒以来,这种事情就没断过。
在这里,给各位要讲述的是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次移情别恋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七十多年前,主角:一个是凯恩斯,一个是兰格;一个是西方社会的思想代表,一个是东方社会的思想代表。
如果说1936年J.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大变革,以至出现堪称“凯恩斯革命”的话,那末O·兰格于1936-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则使东方经济学发生了新转机,从而出现了“兰格革命”。早在本世纪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与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经济学,就形成了两种极端的经济理论观:前者反对中央计划化,主张完全的自由市场经营;后者则反对市场调节、自由经营,排斥商品货币关系,主张完全的、大一统的计划管理。在东方经济学的阵营中,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力排众议,在考茨基的社会主义货币思想(参见考茨基《劳动革命》,1925年英文版)和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启示下,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中央计划和竞争市场相结合的思想,初步建立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导入市场机制的经济模式。
兰格的独特和创造性在于,他不仅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行得通,而且认为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照样行得通。这与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独特认识是分不开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并不是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实物经济模式。他虽然承认消灭私有制和实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但他认为,公有制本身并没有决定消费分配与就业制度的固定程式,也没有规定指导生产的原则。兰格把消费者偏好的最大满足作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标准。因而社会资源使用的最优效率存在于供需的一般均衡之中,这与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竞争的均衡条件是一致的。由此出发,兰格在他的社会主义模式中,首先假定消费品的分配与劳动力就业是由市场机制所决定的,但不存在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市场,自然资源与生产资料的价格是由中央计划局确定的“会计价格”。所以,他认为这一构想既满足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公有制,又能解决人们的消费需要问题,从理论上解决了资源最优配置问题。
在社会主义基本框架和资源最优配置前提不变的条件下,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也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集中的,还可以介于二者之间。于是他便提出了著名的“五模式”理论。几乎产生于同时,在东西两个世界中,又都是针对各自社会经济疾病而酝酿掀起的理论“革命”,受到了截然相反的待遇。关于凯恩斯革命从理论到实践获得的成功、受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礼遇,已为世人熟知;问题在于,兰格革命以来不仅受到漠视、冷淡,而且在当时的苏东经济学界一开始就将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视为“反动”,视为洪水猛兽,持久地对其讨伐、批判。[参见C·哈维娜《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和改良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批判论文集)1917-1945》第2节,莫斯科1975年版]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对兰格的批判差了半拍,但人们对任何社会主义市场化取向的理论观点都是极其警惕,就连孙冶方的“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与 卓炯的“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这样的观点都未能放过,而大兴鞭笞。“如果”兰格的理论当时得到与凯恩斯同等的命运,“如果”市场社会主义从30年代起步,那末社会主义的历史无疑将改写,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无疑胜于现今。事隔半个世纪,我们才艰难地“再发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这笔账无论怎么算,都说明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当然,一种揭示真理的理论的观点之所以未能为人接受、进入实践,恐怕既存理论的排斥、传统观念的抑制是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而一种经济社会的发育还达不到有机吸纳某种理论则是社会生理机制方面的根源。
尽管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比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还不彻底、不成熟,但究其理论渊源来讲,前者正是后者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