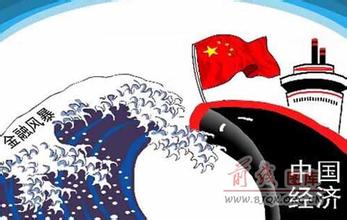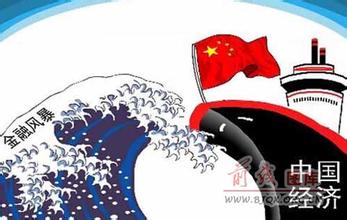所以,针对所谓“人民专制”可以均贫富、因而优于“富人的民主”之说,普列汉诺夫们的反驳是:与其说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毋宁说在缺乏民主条件下的“平均”或专制条件下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更要虚伪得多。因为“‘人民的政治上的专制’绝不保障他们得免于经济上的奴役”。专制下的所谓村社“平均”和劳动组合,所谓“共耕制”,无非是那种最反动的普鲁士式“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尼古拉一世时期靠刺刀和鞭子强迫农民实行的‘共耕’”,或者甚至古代印加帝国式的“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俄国人在这种制度下分裂成“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因此普列汉诺夫说,如果拿有民主但贫富不均的英国和专制但有“公社”的西伯利亚相比,毫无疑问英国要比西伯利亚进步。早期的列宁也同样驳斥过那种均贫富比民主更重要的妄言,认为“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
针对所谓“政治自由只能使资产阶级掌权”、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的工具”、高居于穷人和富人之上的沙皇比“选举”出一些富人来统治穷人要好等谬论,马克思主义者更是痛加驳斥。在这方面早期列宁比普列汉诺夫还要积极,他曾经严厉抨击“西方民主虚伪论”和“俄国公道论”:
“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8943;8943;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总之,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态度是:“资产阶级民主”是有局限的,而“人民专制”则是“反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与自由主义者有区别,但可以结盟反对专制(沙皇专制和“人民专制” ) —— 普列汉诺夫说是“ 分开走, 一起打” ( в р о з ь и д т и , в м е с т е бить);而社会民主党人与民粹主义则完全敌对——普列汉诺夫引克雷洛夫名谚“敌人的主意一定是坏的”。社会民主党人把是否为自由、民主而战看作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普列汉诺夫声称: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会说为了实现“平均”和“人民统治”“无论用怎样的手段都是一样的”,争取自由民主是我们“完全确定的政治纲领”,“社会主义如果反对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就失去了它那种迂腐的天真,而成了政治的与社会的反动势力的工具”。普列汉诺夫尤其痛斥了那种只有“先进阶级”乃至“领导革命的先锋党”才能享有自由的民粹派主张,他大声疾呼:“在自由的国度中,每个人都应当有爱怎样想就怎样想、怎样想就怎样说的权利,而8943;8943;在社会主义的政党中间,这种权利竟被人怀疑,这是可能的吗?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既在原则上承认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并把这样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他们就不能只让那一自命为在当前革命运动时期有领导权的‘党’派来享受这一权利”。
列宁把马克思的“专政”偷换成了民粹派的“专制”

然而,在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列宁可以说是个另类。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各种理论都能掌握而且娴熟地见机而用,很少考虑学理上的一贯性。因此他早年一方面跟随普列汉诺夫对“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会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进行过口诛笔伐,大讲议会民主的好处,并把民粹派的“人民专制”理论斥为“警察民粹主义”。但另一方面,列宁深受其兄、民意党烈士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影响,与民粹派传统的决裂是很不到位的。他对民粹派“亲农民”的倾向确实深恶痛绝,但同时对民意党的集权倾向情有独钟。在“英雄-群氓”说的启发下,列宁很早就提出“灌输论”,不时表露过先进者应当对落后的“多数”实行强制的观点。早在1902年他就曾明确地说: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俄国是个农民国家,而落后的农民、即俄国国民的大多数是靠不住的。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用不着说‘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绝大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必要了”。亦即:俄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因不是沙皇的专制使革命者需要以暴抗暴,而是因为多数人即农民的“落后”使民主不利于无产阶级。
列宁在这里把“专政”和民主(“获得大多数”)相对立,这是合乎“专政”一词之本义的。但他因此认为我们应该实行“专政”,却是此前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有过的观点:尽管“农民落后论”是马克思以来的传统看法,并非列宁首创,但是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农民落后论得出的结论只是在农民国家搞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行不通,必须先经发达的资本主义改变农民国家、使无产阶级成为多数后才有可能。而列宁的说法隐含的结论却是:可以用先进少数强制落后多数的“专政”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观点显然与特卡乔夫的“人民专制”论一脉相承。
应该指出, 把“ 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引进俄国的不是列宁,而是普列汉诺夫,正是他把这个词写进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个纲领草案,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一系的左派政党正式文件中出现“专政”一词的先例。但是普列汉诺夫这样做的出发点仍然是俄国作为当时欧洲最专制的国家无产阶级不能不以暴抗暴。因此,可能为了使纲领更有长远性而不仅仅是谋划革命的一个策略性文件,普列汉诺夫又把这个提法从第二个纲领草案中删除了。当时讨论者中只有列宁坚决抗议这一删除,他说:“在草案中,把初稿中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字样漏掉了。即使这是由于疏忽而偶然发生的,但是,有一点毕竟还是不能怀疑的,这就是‘专政’这个概念同肯定地承认他人支持无产阶级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的确肯定地知道小资产阶级(即指农民)8943;8943;一定支持无产阶级,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的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正像‘批评家’(指普列汉诺夫)想要别人相信的一样。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列宁为此引了《宣言》中关于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等语,并断言:从《宣言》发表至今的半个世纪中其他情况有了重大变化,“然而恰恰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在对草案的又一处意见中,他对“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提法不满,认为它对“小生产者的不彻底性和半反动性只字未提,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要想有权谈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甚至阶级专政,必须首先把这一个阶级划出来”(以上着重号为原有)。
可见,在当时的列宁看来,能够获得多数人支持就不需要“专政”,需要“专政”就是因为他认为无法获得这种支持、至少是无法保证这一点,而这又是因为占俄国人口多数的农民落后、保守和“半反动”。当时有人批评这种观点为“恐农症”。这的确是列宁“专政”观念的鲜明特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