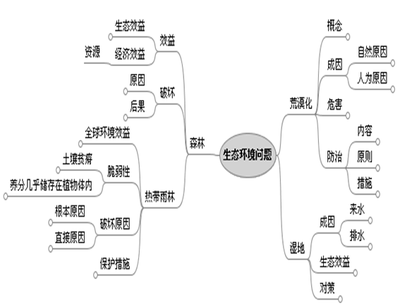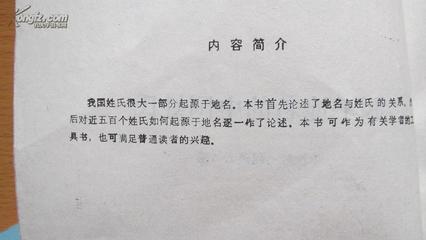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这种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一方面铸就了中国经济神化,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为此,本文尝试引入“泰坦尼克定律”,并以此为向导深入剖析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相关表征及其成因,并沿此解释框架探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规避路径,希冀对当前“风险社会学说”提供新的借鉴价值和思维模式。
关键词:“泰坦尼克定律”;社会风险; 规避。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and avoid risk analysis
——A "Titanic law" explained framework
He Feng1 Ni MingSheng2
(1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2 Public policy and loc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domain is facing restructuring and the transition of the system of "dual-mode" chang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a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as well as the restructuring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ransformation. This ki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molded deified, while China has entered a high-risk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community. To this e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Titanic‘s Law”, as the wizard in-depth analysis of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risk-related causes, and explore along the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transition path of social risk aversion, the hope on the current “risk Sociology said”, provide a new reference value and mode of thinking.
Key words: “Titanic‘s Law”; social risk; avoidance。
一、“泰坦尼克定律”及社会风险内涵
(一)“泰坦尼克定律” 释义
“泰坦尼克定律”一词是清华学者景军在研究艾滋病时作为分析框架而引出,其渊源于泰坦尼克沉船事件,主要阐述社会等级与伤害程度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性。
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是西方航海事故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事故,其引发的社会学思考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对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中的幸存者研究中,学者发现乘客的社会等级差别与其生还几率高低是息息相关的。由于历史的久远及存留记录的不完整,不同的学者计算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中乘客、死亡和幸存者的具体数字也有相当差异,下面引用的一组数字(见表1)是清华学者景军取自一个参考了不同历史档案和几个不同数字来源的综合性样本研究。
表1:泰坦尼克定律的依据――舱位等级与死亡和幸存的关联
景军从表中分析,泰坦尼克号的舱位的分类可视为社会等级的标志,当时泰坦尼克号的一等舱有319人,幸存数为220人;二等舱有269人,幸存者117人;三等舱有669人,幸存者172人。虽然一等舱舱位人数不及三等舱人数的一半,但是一等舱幸存者人数却比三等舱的幸存者多了48人。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泰坦尼克号一等舱船票最低价格是30英镑一张,最高价格为870英镑一张,相当于当时一辆豪华轿车的价钱。二等舱最低票价是12英镑一张,三等最低舱票价3英镑一张。以各舱最低票价计算,一等最低舱票价几乎是二等舱最低票价的两点五倍,同时等于三等舱最低票价的十倍。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乘客人数虽然最少,但只要坐入头等舱,其生存几率显然最高,高出二等舱乘客存活几率的20个百分点、三等舱乘客存活几率的39个百分点。虽然二等舱乘客比三等舱乘客少一半之多,但其生存几率比三等舱乘客的生存几率还是高出18个百分点。[1]不难发现,乘客的舱位等级与生还几率是直接相关的,社会等级差异在巨大的突发灾难降临之时仍然决定着人们的命运,社会等级决定着风险的差异并决定风险降临之后的伤害差异,作为社会等级标志的舱位显然在这里成为生命的重要筹码。
(二)社会风险内涵
“风险”概念在17世纪的英文中似乎已经出现,意思是遇上危险或触礁。随着现代社会的演进,社会风险有了更多的涵义。现代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风险意指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及对人类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
随着当前中国体制的变迁和政策的转轨,当前中国社会的风险主要呈现“风险共生”的表征。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结构转型与体制转型,这其中不仅要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还要进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在经济目标成为社会运行的支配目标的同时,政治行政系统日益偏离原有的社会管制轨道,更多的是指向市场、服务社会。由此,社会的组织原则也从先赋性与政治诱致性原则转向获致性原则。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转型,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在政治原则指导下形成的社会平衡状态,致使这些“人造风险”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中以不同方向、不同速度积聚和叠加起来。因此,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风险状态既不是纯粹传统的,又不是传统现代的,而是一种混合状态。除了前工业社会的传统风险,如自然灾害、传染病等依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全构成威胁外,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失业问题、诚信危机、安全事故等工业社会早期的风险正处于高发势头,同时,现代风险的影响已超越国家疆界,如国际金融风险、环境风险、技术风险、生物入侵等随时可能对我们的安全造成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在社会风险的治理中应承担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对社会居民的政府责任应如何界定,值得我们探究。
(三)“泰坦尼克定律”下的社会风险内涵
景军建构下的“泰坦尼克定律”在社会风险理论中隐喻的内涵是社会等级决定风险的差异并决定风险降临之后的伤害差异,即社会等级越高,受到的社会风险伤害越小,社会等级越低,受到的社会风险伤害越大。“泰坦尼克定律”下的社会风险分布不仅遵照社会等级进行分配,而且还可以转移支配。从相关资料记载来看,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中,救生艇的分布和下水安排保持了一个相同的逻辑,即舱位等级优先,而不是后来盛传的“妇女儿童优先”,在活下来的三等舱乘客人中,许多人是迫不及待跳入水之中被打捞到救生艇上面才得以生还。[1]因此,“泰坦尼克定律”下的社会风险分布、承担与社会等级不仅密切相关,而且是可以转移支配的。对于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泰坦尼克定律”下的中国社会风险总体上是依据社会阶层的划分来予以分配。
在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为特点的现代化变迁和经济转型中,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社会阶层关系变迁中的非均衡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紧张”现象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社会阶层体系中除了传统的工人、农民外,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首先是原有社会角色内涵发生变化,企业中的国家行政干部变成了企业管理人员,工人由原来的“铁饭碗”变成了“合同工”,大量的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农民工”。其次是新的社会位置与角色大量而迅速地增加,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
管理人员,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根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为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是人们利益的多元化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2]中国在这种利益多元化的进程中,强势阶层的权力过多过大,而义务过少过小,存在着强势阶层剥夺弱势阶层利益的一些的情况,对于弱势阶层来说,权力过少过小,甚至不存在而义务则过多,弱势阶层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这必然容易滋生劳资矛盾、两极分化、失业、腐败等社会风险,从而引发社会紧张和社会矛盾。在这种阶层结构、权力、地位的不均衡的转型社会形态中,要缓解和消除相应社会风险,需要对其表现及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合理、合法与高效的风险规避机制。
二、中国转型期“泰坦尼克定律”下的社会风险分析
(一) “泰坦尼克定律”下的社会风险表现
(1)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增加。近10年来中国社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以及参加人数和规模,都呈现不断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从1993年到2004年,全国的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从8709起增加到近7万起,涉及人数也从70万人增加到300多万人。[3]对这些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以产业工人和农民劳动者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了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社会骚乱性事件或有组织犯罪事件也有所增加。这些社会骚乱型突发事件中很多都是“非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对社会不满、恐慌的累积只有在寻找一个共同的目标事件,形成“挂钉式共同体”来发泄不满,行动方式也经常突破法定的限度,因此社会影响十分巨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危害到社会公共秩序。

(2)社会各阶层间贫富差距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主持的2001年全国问卷调查中,与1995年相比,中国十大阶层体系中地位越高的阶层,有越高比例的人认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好了很多”;而地位阶层越低的人,情况恰恰相反。[3]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风险更多地被转移到了社会低阶层人员的身上。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处于社会中上水平的中产阶层在数量与实力上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态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而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产阶级力量薄微,弱式群体数量庞大,主要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进城的农民工及城市下岗工人等等。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2006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另一来自世界银行报告的分析数据:中国家庭中最贫困的10%人口(日收入不足一美元,约1.3亿人) 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2]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因而也是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由于2007年宏观经济过热,使得我国基尼指数即将由此及2006年的0.47攀升至0.48,0.01这一数值虽然看似不大,但已相当于2003-2006年三年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同时,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超过0.48,意味着80%的城乡居民占全民的收入比重会下降到50%,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128,在不到20多年时间里,贫富差距发展之快,实属罕见。贫富差距形成的利益矛盾正在向外扩散,从而形成了社会地位、声望、政治影响力以及文化倾向、价值观念和生态要求等各个方面的矛盾,极易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
(3)社会阶层间界线越来越明晰。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人们的致富欲望被极大的激发,但是,改变生活的手段与方式并不是均等分配的,在十大阶层体系中,农业劳动者阶层收入增长缓慢,创收渠道和手段越来越少;工人阶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甚至失去收入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社会地位显著下降;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从政策和制度上看,私营企业从“试试看”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再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再到“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阶层最后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乃至今日一些人成为劳动模范,社会地位发生了本质性的提升等等。[3]社会阶层体系中各个阶层收入状况、政策保障、社会地位的不同,使社会阶层体中的界线越来越清晰,不利于阶层运行体系的活力运转。
(二)“泰坦尼克定律”下的社会风险成因
(1)转型期现代化建设的迅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利益分配不均和阶层分化加剧。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推进市场化建设的进程,国家与社会在结构与功能上分开,社会分层体系不再通过“单位”来实现权力与资源的分配,社会分层体系伴随着利益分化而产生, 人们在阶层定位中也主要是以经济状况为标准, 经济利益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中轴,中国是后发展国家, 现代化战略一直实行的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使广大劳动人民都享受到了胜利果实,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利益成果向强势阶层倾斜,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弱势群体被“制造”出来,造成公民利益分化加剧、利益分配不平衡,利益矛盾不断突显。在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作用已十分有限,有限的耕地资源无法承载过多的农业人口,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其他的产业转移,靠天吃饭和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的开发弹性已很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也越来越困难。那些涌进了城市的农民工们,其命运也不可能有本质上的改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农民工从一开始是就以一种极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的,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甚至拿不到钱,没有任何福利与保障。在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大量的工人阶层失去了岗位,据有关专家的测算,实际下岗失业人员数已达4000 - 5000万,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昔日令人羡慕的城里工人也逐步丧失了主人翁地位,并逐步沦落为弱势群体。社会阶层利益分化加剧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和缓解,就会增加社会风险,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
(2)社会转型期的制度转轨导致成熟的社会阶层利益保障机制缺失。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增加,在社会转型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制度转轨,缺乏成熟的、合理的阶层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这更加剧了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改革分配规则就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必然引起社会群体地位的重新排序。随着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社会已经分化为两极,一极是由政治、经济、知识等精英组成的强势群体,另一极是由农民、工人及体制外的普通劳动者构成的弱势群体。一方面高收入阶层试图影响政府政策和决策的利益偏好,另一方面, 低收入阶层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达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表达与保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体制内的调整,无法从深层次上解决农村贫穷问题,农民工阶层缺少合理的户籍制度、开放的社会流转机制的保障,使农民工即使已经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但他们依然无法进入城市的主流社会,真正成为城市中的一员。社会教育、医疗和住房体制改革的失败,更是使老百姓“雪上加霜”,高学费的壁垒将穷人的孩子阻挡在校门之外,每一个普通百姓都能享有的医疗保障权利也被市场化进程所剥夺,日益飞涨的房价让工薪阶层只能望房兴叹,社会转型期的“新三座大山”,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利益分化。重建科学合理的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就成为改革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打破传统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的过程中,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并没有迅速形成,使得各阶层不仅对已有的制度性规则不信任,同时不能有章可依,这种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缓慢的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形成过程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3)社会转型期各阶层的主观认识与地位张力摩擦所产生的社会紧张。社会分层体系是一个复杂社会用来鼓励人们去获取对社会运行和均衡所必需的不同职位的机制,来满足社会运行的功能。在形成社会分层体系的同时,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一套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来解释其分层体系的合理性,如果社会阶层体系发生了变动与更新,但缺乏系统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舆论来形成主观认识上对社会阶层体系的认可,就会产生社会紧张和非均衡问题。当前中国阶层关系中存在着以下几方面主观认识和地位之间的张力。第一,意识形态的解释不被认可,比如工人阶层在意识形态上仍然认为自己是领导阶级,但是在客观地位上并没有体现出一点,这种不一致的后果使工人阶层以意识形态解释为依据,来对他们的阶层地位低下表达不满,国有企业的工人对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下降越来越不满,各种上访、静坐、请愿等活动就会不断发生。第二,意识形态对已经分化的阶层缺少全面的解释,特别是对新阶层的合理性认识不足。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农民工阶层,农民工阶层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城市农民工不仅没有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还在意识形态受到各种歧视,与城市居民“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很普遍。第三,一些阶层的相对剥夺感甚至相对剥夺感有所增强。各个阶层的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利益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分层导致了人们过度的利益欲望,固化了人们的求利意识,放大了经济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利润、财富等目标的重要性不适当地扩大使人们被鼓励着用任何方式来获得它们,以实现自己“暴富”和进入上层社会的梦想,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更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和谐所需要的健康文化环境。[3]
三、中国转型期“泰坦尼克定律”下的社会风险规避
(一)加快各阶层利益保障机制建设,夯实社会风险的防范基础。
建构健全的利益保障和利益协调机制,对于适时化解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各社会阶层矛盾,巩固原有社会风险的防范基础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首先,加快社会各阶层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建设与落实。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到,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这样的总体纲领指导下,国家公共政策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题中之义,不能仅仅止步于“兼顾”,更不能以牺牲公平换效率,从实际情况出发,不仅要加大对弱势群体在政策、资源与资金上的支持,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同时对高收入群体实行征收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逆补偿机制。两种补偿机制双管齐下,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3]既要补偿社会弱势群体的物质损失,同时还要补偿他们对公平的心理诉求,由此来增强社会风险机制的预警建设,从利益矛盾的源头解决社会阶层的差距,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其次,加快具有补偿性质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建设与落实。创新社会保障思路,探索适宜中国转型期国情的社保体系,重点建设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议将最低生活保障与救助从城镇居民扩大到包括农村在内的全体居民,将失业保障从城镇居民逐步扩大到进城的务工者,将医疗保障建设成为城镇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农村的合作医疗。[4]此外,还应鉴借发达国家的经验,建设较为系统的养老保障体系及住房保障体系,加强弱势群体的抗风险能力。
再次,加快科学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的建设与落实。衡量社会是否开放的一个重要尺度,主要看有无社会流动及流动的程度。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有了地区之间、职业之间的水平流动,而且有了城乡之间、体制内向体制外的垂直流动。总的看来,水平流动基本没有阻力,但垂直流动还是阻碍重重。如城乡流动中的户籍限制、体制内外的不同待遇、干部的单向流动以及终身制、机会垄断、身份固化、人为强化等级差距等表面开放而核心封闭的社会结构,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政治宣言中的民主诉求格格不入。不平等则要求有流动,政府应该创设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使所有社会成员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都能够有机会改变先赋命运,顺利地实现个人地位的跃升,而不是人为地制造或强化等级差距。事实上,只有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才可能使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看到前途与希望,才不至于因绝望铤而走险。因此,对社会风险的基本评估,和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优先排序,给了我们一个在目前条件下如何用好有限资源来最大地减少和分担社会风险,为人民群众提供社会安全保障的路线图。[5]
(二)加强公民能力建设,提高社会化解自身矛盾的抗风险能力。
政府应改变传统意义上“包揽一切”的执政理念,适当合理地向社会“分权”或“还权”于社会,应强调和重塑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同时,积极引导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 通过多种纽带如家庭、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将人们联系起来,建立沟通渠道创设,如各种兴趣组织、民间俱乐部、听证会制度、任免公示、网上论谈、媒体披露、热线电话、心理咨询等多种让人们表达不满与紧张的合法方式、场合及机会,允许不同意见与对立情绪得以适时宣泄与表达, 降低社会成员的孤立程度,防止矛盾的过度积累与压抑。
(三)加强各阶层话语沟通体系建设,提高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性。
传统风险治理体制强调科学知识和专家系统的重要性,认为依靠人类的“工具理性”就足以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但转型期中国的“风险社会”不仅是一种事实概念,也是一种文化概念。在社会阶层体系的矛盾化解时,必须充分考虑文化、社会和价值因素,使社会阶层体系得到认同。因此,应通过政府牵头、学者研究、媒体推广、公民共同参与而建立一套人们普遍认可的阶层话语沟通体系,树立科学价价值观与发展观,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加强社会各阶层的阶层认同性,完善社会阶层体系,防止人们社会意识秩序上的混乱,使得处理社会关系有规则可循。
参考文献:
[1]景军:泰坦尼克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2]邹小蓉: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失衡与风险成本[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王春光: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变迁中的非均衡问题[J],《社会》,2005年第5期。
[4]刘庆珍: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防范机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6卷1期。
[5]吴雪明、周建明: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布与抗风险机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何枫(1983— ),女,浙江诸暨人,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领导力及其公共事务治理;倪明胜(1982-),男,湖北鄂州人,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与公共事务治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