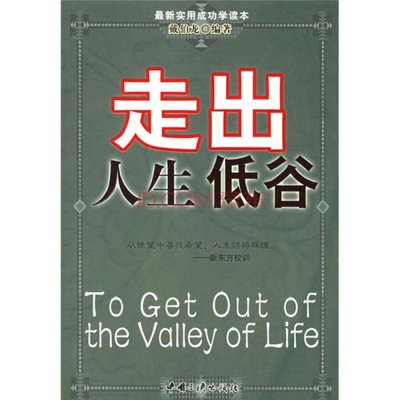本文最早发表于12月8日出版的美国卡蒂弗珍尼丝韩森联合投资顾问公司内部出版物《经济与财富通讯》
走出危机的必经之路--战争或是创新
作者:韩和元
凯恩斯主义的现实意义-- 造箭伤自身
《经济与财富通讯》:按照您的危机本身具有不可避免性,而人为因素只是在对危机予以加强或弱化的观点,那么可以说,当前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的政府的举措,都只是在将这种破坏力人为的加大化。
韩和元:是的,历史会告诉我们,看看罗斯福总统上台伊始是,信誓旦旦地拿出一系列重振经济的宏观政策,可却得到一个“1938年的美国,消费者购买力薄弱令美国经济因消费者需求不足陷入困境”的下场。
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同样如此,这十年里,内阁如同走马灯似的更换,每一个首相上台也是信誓旦旦地拿出一系列重振方案,可无一不黯然收场,病却越治越重。1992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首次动用10万亿日元巨额财政资金作为景气对策推出,实施以减税和增加公共事业投资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使政府公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以上。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高于美、德、英等发达国家。巨额债务不但使财政不堪负担,而且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操作空间也非常狭窄。
日本银行也不断推出以降低官定利率为中心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超低利率水平也导致货币政策选择余地丧失,央行已经很难有所作为,“零利率”政策已使扩张性货币政策黔驴技穷,虽然目前日本国内的短期利率仅为0.001%,但银行贷款额却已连续45个月下滑。凯恩斯的主张却都“造箭伤自身“,只是伤到的不是他自己,因为他已经死了,死去就原知万事空的,伤到的却是他的一般信徒,是信仰他的主张的日本,是日本经济的发展,是那些无辜的日本国国民。银行坏帐据统计,如果将灰色债务计算在内,日本的银行坏帐相当GDP的35%,东京大学的西村青彦教授说的很明白“金融界面临瘫痪,根本看不到一点光明”。
结合1930年代的美国和1990年代的日本,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企业经营恶化-债务不能偿还-银行坏帐增加-银行处理坏帐(催逼企业还债)-破产企业增加-社会消费下降-企业销售额下降—经营进一步恶化……
创新停滞才是本轮危机的根本原因
《经济与财富通讯》:但这一切仅仅只是症状,而不是病因?
韩和元:是的,完全可以这样理解。

《经济与财富通讯》:那么病因呢,病因何在?
韩和元:的确绝大多数的事件,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就像当前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一样,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的积合,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就如同古巴格达不是一天建成的,也绝不是因为某一突发的厄运而将其毁灭。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古巴格达的毁灭是多种多样的因素---重要的和次要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那些寻求科学精确性的人来说,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难以令人满意,而且要确定和分离出那些诱发因素是极为困难的。但不幸的是,这恰好是事件的本质,同时它也使得我们又必要不停地去寻找更全面的信息,以便能了解这些诱发因素的大概轮廓。全球化,已经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在这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中东的战争已经引发了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是证明,而引发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初始能量---倒下的第一张牌—正是美国的金融危机,那么世界经济为什么会衰退呢?我们知道,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达到32%,而因为他的拉动效应而带动的GDP总量则无疑更高,高到多少,应该不会下于45%。比重太大了,在公司破产方面很有研究的比尔.麦齐先生曾经就告诫过我们的企业家,当你过度依赖于一个客户或者供应商时,那么你就已经步入破产的境地了。而拥有巨大消费力的美国正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产能的客户,而这个客户一旦出现问题那么,这些为它服务的产能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具体到今天的局面,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创新的停滞:这轮繁荣始于1996年,因互联网这个生产要素新组合的出现,的确刺激了全球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当互联网这个新组合出现时,老的生产要素组合仍然在市场上存在。新老组合的共存必然给新组合的创新者提供获利条件。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新组合的技术在这十几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散,被大多数企业获得,现在是不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了,我不能够下这个结论,或许是互联网技术的第一代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吧,——但事实上这轮创新早在2001年就已经停滞了,在停滞阶段,因为没有新的技术创新出现,因而很难刺激大规模投资,理论上来说,那么世界都难以摆脱萧条,特别是火车头美国,这种情况直到新的创新出现才被打破,才会有新的繁荣的出现。
政府的人为干预政策将危机的人为因素最大化了
《经济与财富通讯》:但显然,没有哪个政府愿意什么都不做,他们总认为他们应该做些事情,并且也自信他们能够做些事情。
韩和元:对,这就是建构论的唯理主义指导原则下的必然。哈耶克曾对法国启蒙运动为代表的“建构论的唯理主义”者的批判一样:现代文明受到的威胁,并不在于毁灭世界的非理性主义的狂热,而在于建构论的唯理主义者的滥用理性。试图有意识地设计现代世界,计划经济、政府干预,都是过度迷信理性的结果。布什政府显然也不例外,于是他开始发扬拿来主义,把凯恩斯的积极干预需求面的圣经念了起来,人为压低利率就是他的功业。
《经济与财富通讯》:我有点迷糊了,布什政府的确是在人为干预需求面,但按照传统的做法,比如罗斯福总统的做法,应该是政府很主动的采取干预才是,但事实上从2001年来,政府对市场的政策性干预却是越来越少的。
韩和元:这就需要动用马克思的辨证论来解释了,在这里我很赞同霍里特先生的信用论,罗斯福总统接手的是个烂摊子,那个时候利率政策已经失效了,再低的利率也刺激不了人们的借贷热情,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叫信用僵局的东西,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在这个时候恢复信用是最重要的,在当时,最大的不信任对象正是那些贪婪的、获取着垄断利益的银行,没有人肯在那时节把钱借给银行,他们对它不信任呀,银行借不到钱他怎么可能借钱给企业呢?而同时人们认为危机的源头在于银行体系的全行业运作,是企业的垄断行为所导致,要想恢复人们对银行的信心,就必须从这里着手。
《经济与财富通讯》:于是就有了格拉斯—斯缔尔这样的法案的出台。
韩和元:是啊。这样一来,人们对银行体系的不信任感是要减少很多了,这点可从法案出台前后,美国银行的储蓄率看的出来。而到了2000年代一个信心满满,彼此互信程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曾经采用过的人为刺激手段,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人为干预需求面的阻碍物绊脚石了,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凯恩斯的门徒们为自己找到了一张很漂亮的画皮---新自自由主义的放任原则。这就是中国人经常讲的此一时彼一时了。
《经济与财富通讯》:布什政府担心因为创新的停滞而产生严重的经济衰退问题,于是通过人为的压低利率,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来达到他们的干预需求面的目的。
韩和元:是的,美国经济的变坏是多种多样的因素---错误的利率政策,但我认为这通还只是次要的直接的诱发性因素,其真正的重要的但却间接的因素,我认为还是在于创新的停滞,创新(Innovation theory)是奥地利经济学家J·熊波特提出用以解释经济波动与发展的一个概念。所谓创新是指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的一种“新组合”。生产要素新组合的出现会刺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当新组合出现时,老的生产要素组合仍然在市场上存在。新老组合的共存必然给新组合的创新者提供获利条件。而一旦用新组合的技术扩散,被大多数企业获得,最后的阶段——停滞阶段也就临近了。在停滞阶段,因为没有新的技术创新出现,因而很难刺激大规模投资,从而难以摆脱萧条。布什的政策只是把这个早在2001年就
应该让他全面爆发的危机,暂时的压制了,纸包不住火,终于今天烧的很大了。
《经济与财富通讯》:布什们把这种危机予以加强了。
韩和元:对。
走出危机的必经之路--战争或是创新
《经济与财富通讯》:那么如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
韩和元:我想再强调一次,经济危机是一种周期现象,是一种规律,它是不可能随人的主观意志而发生转移的,所以它是无法克服的,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尽量将人为因素最小化而不是最大化。
《经济与财富通讯》:哦,或许是我表达的不准确,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走出危机呢?
韩和元:两个办法,要么创新要么战争。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因为它的到来,令我们损失的仅仅只是金钱,但因为他所衍生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民族信任危机才是最可怕的。但讽刺的是有时候战争的确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好办法,1930年代凯恩斯把美国经济害的几乎破产,大量的政府投资,加剧了原本已经恶化的供需结构,使得产能严重过剩,为此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1938年的美国“消费者购买力薄弱令美国经济因消费者需求不足陷入困境!”但罗斯福很幸运,凯恩斯也很幸运,随着战争的扩大,各交战国的物资需求,终于让美国的那些过剩产能得到了应用,深陷战争的英国、法国、中国和日本(日本之所以要与美国交战,原因就在于美国拒绝再为他提供物资,日本认为美国的这一行动伤害到他的利益)的购买力取代了美国国内那薄弱的消费力而令美国经济因消费者需求增强而走出困境!
很多人被假象蒙蔽了,他们认为那是凯恩斯之功业,但殊不知,救了美国经济的命的不是他凯恩斯,不是它凯恩斯的干预需求面的胜利,而是破窗理论的胜利,而希特勒、昭和天皇、墨索利尼们则是那个打破窗户的坏孩子。
《经济与财富通讯》:这种方法显然有些不人道。幸好还有一个办法,创新。
韩和元:哈哈,但创新却很娇嫩,他需要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时间,如果因为时间拖的太久,社会的民族的矛盾将会加剧,战争也就不期而至了。
思想及物质的自由是创新的基础
《经济与财富通讯》:第二个呢?
韩和元:如果我们不依赖于应用任何人所给予我们的知识,而是鼓励人与人之间思想的交流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更好的知识就会产生,那么我们就能够更为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哈耶克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信念,这里我们姑且抛开自由主义不说,单就我们现在最热情的予以研究和展开的创新来加以谈论。哈耶克说:正是源自人们不同经验的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和相互批评,被认为推动了对真理的发现,或者说,至少达到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接近真理的程度。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要求马虎不得,因为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易犯错误的,因此人们只能期望通过由自由争论所维护的,对所有信念进行的不停检验来发现最好的知识。或者,换句话说,对知识的发现与其说是来自于个人理性的力量(对此,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不加以信任的),还不如说是来自于人际间的争论和批评的结果。这是一个向人们所期待的真理稳步前进的过程,即便是个人理性和知识的增长也被认为只有当个人成为这一过程的一部份的时候,才是可能达到的。由思想自由所保护的、知识或进步的发展,以及人们实现自己目标权力的相应增长,是格外吸引人的,基于上述:我们认为这也构成创新意识的必然假设之一。
然而,所有关于支持思想自由的争论也同样实用于做事的创新或者说行动的创新的情况。各种各样的经历导致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是知识发展的源泉,而不同的经历反过来又是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人采取不同行为的结果。无论是知识领域还是物质领域都一样,竞争是最有效的发现途径,它将导致为了人类的目标而发现更好的道路,只有当数不清的办事方法能够被尝试时,世上才会存在种种不同的个人经历、知识和技能,这种对最成功者的不停选择将会导致稳定的进步。当行动成为个人知识的主要来源后(这种个人知识是知识进步的社会过程的基础),行动自由的事实就和思想自由的事实一样强有力了,而且在以劳动力和市场分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新的行动类型是在经济领域内产生的。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行动自由,尤其是在通常表现得相对次要的经济领域中,事实上对创新是同样重要的。如果正是思想选择了人类行为的目的,那么目的的实现就取决于所采取的方法的可行性,而任何使得权力超越了方法范畴的经济控制,最终也会使得权力超越目的范畴,而达不到目的。哈耶克曾举例说明道:如果出版机构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就不会有言论自由,如果所需的场所由政府控制,就不会有集会自由,如果交通方式由政府垄断,就不会有迁徙自由,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经常空怀着为达到所有经济目标提供一个更充分手段的徒劳希望,而对经济活动进行的指导却都毫无例外地对个人所能够追求的目标造成了严格的限制。这也许是20世纪的政治发展中最鲜明的教训,即对物质生活的控制已经使政府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得到了如此广泛的权力,而这正是我们学来用以称呼极权体制的特征。
请记住,正是思想和物质的自由才使得我们能够选择自己愿意追求的目标。这就是创新的真正的基础。
重新思考理性主义的遗产是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经济与财富通讯》:又回到人类中心主义上来了,又回到人为因素将危机更大化这个问题上来了。
韩和元:对,正如同哈耶克所批评的,人们在启蒙心态中呆了这么久,以致我们假定它的总体思想推动力是合理的。不言而喻,现代人都同意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它造成现代人的心理倾向:人不仅是万物的尺度,还是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源。尽管启蒙心态对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信仰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已经受到一些智者的挑战,但它仍然是激励全球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的准则。很难相信,任何一个国际项目,包括生态科学中的,不同意以下这些观点:人类的生存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以理性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是众所渴望的,个人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启蒙运动唤醒了人类,使人类发现了转变全球的潜力,实现了人类渴望成为万物尺度,做万物主人的愿望。它一直是现代政治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伦理论述。几十年来,它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和文化精英的毋庸置疑的假定,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
对启蒙心态的公正理解,需要直率地讨论现代西方的黑暗面。那“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unboundPrometheus)象征着急剧发展的技术。它是人类智慧在工业革命早期获得的巨大成就。尽管受到浪漫主义运动的反对,遭到人文科学前辈的批评,启蒙心态在浮士德精神(一种本能地去开发、了解、征服、压制的精神)的鼓舞下,一直是现代西方的主导意识形态。如今它正被拥戴为毋庸置疑的基本发展理论,这正是凯恩斯主义之所以颇得市场的文化基础。
然而,对启蒙心态进行现实的评价,将揭示出现代西方与“理性时代”(The Ageof Reason)的形象有很多不协调的方面。现代西方霸道的论述认为,进步必须诉诸所谓的理性和个人能动性。他们的梦想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相当多不同意识形态的人都有同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学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也如此,人顶可胜天。今天的危机正是这棵树上结出来的果实。
对此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紧迫任务,即重新思考启蒙运动的遗产。鉴于启蒙心态给生命支持系统带来的始料未及的负面后果,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它的内在逻辑,然而我们又不能拒绝它在当前和未来与我们知识界自我定义(intel1ectua1selfdefinition)的联系。我们面临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脱离并独立于启蒙心态,建立一个彻底不同的新伦理或新价值观体系,既不现实也不真心。它要么是愤世嫉俗的,要么是吹毛求疵的。我们应该开发这样的精神资源,它可以帮助我们扩展启蒙运动的视野,深化它的道德敏感。如果必要的话,还要创造性地改变它的天生束缚,充分发挥它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潜力,改善人类整体的生存条件。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