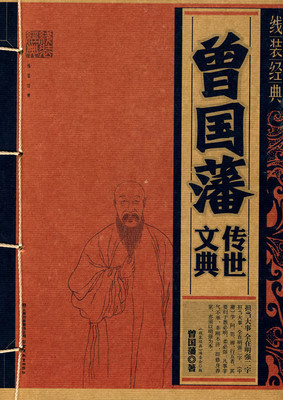昨晚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上与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户籍”,其中当然会涉及到近来相当惹眼的“上海户籍新政”。一段时间以来,见到不少同行或媒体人士对此发表了颇为积极的评价,诸如:“上海户籍政策已在全国率先破冰”、“上海户籍‘新政’为户改开了个好头”、“上海‘户籍新政’带来积极信号”…… 说实话,乍一见媒体报道上海“居住证转户籍”的“新政”,也立即产生相似的兴奋点。尤其是上海的官员在与网友在线互动时卖了个关子:只要等到某月某日,一打开网站,就可以了解到“居住证转户籍”的详细政策了。在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屏着呼吸等待这样的“政策包袱”抖开,煞是兴味十足。不由得随手写下一篇评论的标题:《上海户籍新政:迈出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然而,到了“东风吹梦到沪上”之时,包袱抖开,见到的却是一道令人沮丧的“脑筋急转弯”。原来传说中的“七年为期”是有附加条件的:其一是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持证期间依法在上海缴纳所得税,这是经济条件;其二是在上海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这是身份条件。 虽然上海市的官员在谈及600万“长期居住在上海”的“非户籍人口”时是充满感情的:“他们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新政”反映出来的残酷事实却是,600万“非户籍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仍然会因“条件”限制而不具备“转证”的资格。 现在官场上常拿国际惯例来说事,于是也有人以所谓国际经验来解释上海的“转证”条件。可是,他们所举出的“经验”都是国与国之间处理国际移民问题的,拿来对付国内的流动人口或“非户籍人口”,这合适吗?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各国之间进行贸易,是要征收关税的,我们能以此国际惯例或国际经验为由,在国内各省市之间也征收“地方贸易保护税”吗?——内外有别啊! 再者,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些国际经验可用,上海的规定也更为苛刻。譬如,瑞典规定,在瑞典居住6年就可以入籍。我知道一个个案,移民到瑞典后,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但满了6年,照样可以入籍。在国际惯例中,除了“坐移民监”,还有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但那都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只要符合条件,立即就办手续。而现在的“新政”,从文字上看,似乎是必须同时符合所有的条件才行,这比国际移民还要严格得多。 近年来,吸引流动人口比较多的沿海发达地区,时不时地发出“人口超载”的惊呼。以上海为例,挂在嘴边的就是1300万户籍人口,600万非户籍人口,哇噻,非户籍人口要占总人口大约1/3,言下之意无非是上海市快承载不了了。试问,当前这1900万人口不是正常地在上海工作、生活吗?再问,上海的发展还离得开这600万非户籍人口吗?既然承认“他们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实际上就意味着上海市政府要对他们负起责任来。借用一个广告语的句式:制定一个政策,要配得上非户籍人口用青春、汗水甚至热血换来的赞誉。 讨论中,有代表、委员提出,在全国都在淡化“户籍”的限制作用的今天,上海的“新政”却在逆势而行,试图强化户籍在社会群体间的“阻隔”作用,所以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在全国一片“取消户籍制度”的呐喊声中,过于理想化的“一砍了之”自然不可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政策滞后也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再强化、固化这种不合理的制度。那怕就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他们也同样在“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户籍制度全面消亡之前,当他们的生活基础——工作、住房(可买可租)等等——已经全部落在上海的时候,也应该让他们有“入籍”的选项。

很多人会认为,大城市一旦开放户籍,外来人口就会大量涌入,其实未必。现如今,国人的经济理性越来越强,其实农民工更会算计。另外,从某种程度上说,该来的已经来了,因为没有户籍并不能够阻止外来人口进入上海,对此不要作鸵鸟状,可以预计,上海市的人口突破1900万是早晚的事(可能现在早已不止此数),但这与户籍毫不相干。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玩“户籍政策”,只是上海市官员的一厢情愿,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那些与户籍挂钩因而造成不平等的“政策”被一一摆平了,“国民待遇”人人可以享受了,那么,老百姓自然会选择。举一个例子,即使在现在这样很不理想的政策环境中,据说已经有十万户籍在北京的退休人员将河北涿州选为他们的养老之地。上海市的“新政”,无非是想把上海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工厂”。其实政策好了,老年人肯定会自愿离开喧闹的大城市去寻找山清水秀的养老之地,而将城市中的位置留给正欲发力拼搏的年轻人(这并不以学历、学位或职称为前提条件)。这不是一个纯粹胡思乱想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美好愿景。但这不靠强权,而是靠理性选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