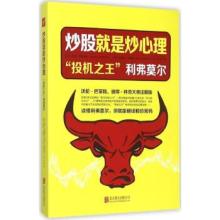我长大成人的地方是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北部最为贫困的地区,我熟悉这里的每寸土地,而且这里也成就了我孩提时一段还算幸福的时光。当时的左邻右舍正如电视里演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样,以至于后来的几十年似乎也定格在这段时期里,没有太多变化——这里不乏经常一起玩的伙伴们,还有不同年龄层的人聚会热闹的场所,再有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小商贩,最不缺的是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当时唯一能在电视上见到的黑色就是名牌黑皮衣,而在我住的地方,至少在来到世上的头12年间,我只在电视和警车里见过白人。我那些幸福时光的主角都是自己的家人,首先要提的就是我那三个倔脾气舅舅。威利和亨利舅舅双双退伍之后,去过遥远的海岸,后来两人回到路易斯安那呆了好一阵子,才不约而同的决定要尽可能远离南方,两人计划去加拿大,可车子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抛了锚,于是索性就地留下来,没再继续他们的旅程。勤勤恳恳的加德纳兄弟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很容易就落下脚来,他们就选在密尔沃基和与密歇根湖交汇的地方安顿下来,这里土地肥沃,适合耕作,水路四通八达,适合工业和贸易,绝对是他们的理想生存之地,为适应酷暑严寒,在这里生存需要内心的坚韧和顽强,以及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而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优良品质都是从不同地方移民到威斯康星的人们身上并不或缺的品质。相信在密尔沃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身上,也不乏同样的优点,如温尼巴哥和伯塔瓦托米部族就是这样的实例。还有些当地的特性也感染了这些外来移民,无论是黑人、犹太人、意大利人、东欧人,还是来自德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的第一拨移民潮以及当地的原住民,都受到这里极度乐观精神的鼓舞和感召。所有这些雄心勃勃又不失实用性的梦想有时竟能催生一些超级成就。比如,仅有一个啤酒品牌大卖是远远不够的,密尔沃基响当当的啤酒品牌可以有若干。这里不仅奶制品闻名于世,它的奶酪产品甚至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可圈可点的支柱行业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十个八个,造砖、制皮、酿酒、造船、肉食品加工、钢铁(这里有美国的内陆钢铁公司、艾欧史密斯),以及诸多汽车巨头(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逐渐衰落)。其实主要是钢铁厂和汽车厂使得很多黑人从路易斯安那、阿拉巴马、密西西比、佐治亚等南部诸州纷纷移至密尔沃基、底特律、芝加哥、克里夫兰这些北方城市,这些体力工作比起南方农场里挥汗如雨的田间耕作相对要好上很多,当时南方的农场主要采用分成制,而不到一百年前,干脆就是奴隶制。很多这样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家人都沿袭各自家乡的习惯和做法,似乎这些东西已经和他们密不可分。姐姐奥菲丽娅生父的一家就是这样,他们来自路易斯安那,最后也在密尔沃基定居,崔普雷特一家人来自密西西比,很难找到像他们家那么好的人了,但弗莱迪绝对是家中的败类。日复一日,大家都在努力的工作,但在周末,大家则尽情嬉戏,还专心祷告,至少我家的这些邻里是这样的。我们这附近绝对没有酗酒这种事情发生。每到周五傍晚,美国内陆钢铁公司下班的哨音一响,派对聚会就开始了,而且会一直持续到周日的早上,然后人们就纷纷赶到教堂做礼拜,祈求主的宽恕。我的三个舅舅都在内陆钢铁公司上班,阿奇和威利舅舅一直干到退休,亨利舅舅则干到自己生命最后一刻,不过那一刻来得太早了些。

我四五岁的时候,和阿奇舅舅和缇缇舅母一起生活。我逐渐喜欢上了家里人每天上班的这种日子。舅舅和舅母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家里总是洋溢着其乐融融、祥和的气氛。舅母缇缇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要我们也完全信奉她的信仰。每个礼拜日,我们一整天都呆在会幕浸礼会,夏天的时候,我们白天参加圣经学习班,平时一旦有什么特殊集会,我们都会陪着她一同参加,同一教堂的教友若有故去,无论熟识与否我们都去参加葬礼。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欣然前往,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街坊邻里,现在都换了庄重的衣服,和平时判若两人,这本身就非常有趣。我也喜欢大声唱歌,这让我感到兴奋和激动,特别是当我不大确定自己的母亲是谁,身在何处的时候,和大家在一起会让我产生一种归属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