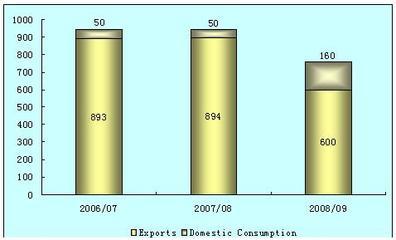世界各国实现跨越的速度各有不同:美国跨越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用了20年,联邦德国用了13年,法国用了17年。规模偏小的国家,韩国人均GDP在1977年进入1000美元关口,到1987年达到3171美元;泰国仅从人均GDP2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就足足用了14年。
国家统计局发布《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初步核算值为30.067万亿元。相较于2007年我国GDP最终核实结果25.73万亿,一年多出了4万多亿元。《报告》还公布了2008年底我国的人口数量,13.28亿。依次计算,人均GDP达到了2.26万元。若按2008年12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的基准价6.83计算,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315美元。
2004年我国开始执行新的GDP核算和发布制度,年度GDP核算按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三个步骤进行。这就造成了每次公布GDP都会有所差异。再加上每5年一次的全国经济普查,国民总产值因而有了更多“跳跃”的机会。2002年,我国GDP才突破10万亿元,7年后就突破了30万亿元。其中,2004年的全国经济普查统计一下子将GDP提升了2.3万亿元。 不管统计方式如何,21世纪初的几年里,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财富爆炸。以美元为坐标,直到2003年,我国人均GDP才刚超过了1000美元,随后,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跨越却只用了5年。历史上如此短的时间实现这一阶段性跨越只有日本,用了4年,但那时的日本人口还不足1亿。GDP意味着国民财富,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积累如此多的财富。另外,现有的数字可能还嫌保守,全国范围内的第二次经济普查正在展开,据权威人士透露,从目前掌握的单位清查数目看,全国法人和非法人单位较2004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个体规模上都有较大提升,最终GDP结果可能还会上调不少。 在2007年世界银行的全球人均GDP排名上,全球约一半的国家超过了人均3000美元的水平,世界各国实现跨越的速度却各有不同:美国跨越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用了20年,联邦德国用了13年,法国用了17年。规模偏小的国家,韩国人均GDP在1977年进入1000美元关口,到1987年达到3171美元;泰国仅从人均GDP2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就足足用了14年。增长的差异性使得对增长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按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说法,主流经济学家仍解释不了中国奇迹。比如说,在这轮强劲增长之初正是海外经济学家全线唱空中国的时候,包括市场经济必须先有制度保障,政府应是小政府,乃至休克疗法等等。 经济增长的动力包括三个方面,要素投入、制度变迁和生产率,解释世界各国国家经济的增长机制促生了宏观经济学一个分支——经济增长理论。这一学科中新古典理论的建立就是基于美国长时期稳定的增长。索洛的增长模型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石,这一模型说明,长期中,一个经济的储蓄率决定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规模,也就决定生产水平。对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观察结果显示,日本、芬兰和新加坡等投资率高的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持续高水平,保障了经济总量的持续高涨。 美国1909~1957年年均实际产出的年增长率为2.9%。新古典理论另一个巨擘丹尼森在1961年发表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书中经过计算发现,在美国年均2.9%的增长率中,有1.575%来自于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剩下1.325%是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的增长所不能解释的。经过进一步分析,他把这部分的增长率归结为劳动力质量,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这52年的数据,他系统分析了教育、健康和公司培训等与劳动力质量相关因素的投资成本,并把投资成本转化为劳动力素质的指标,结果发现,在美国年均2.9%的产出增长率中,有2.25%来自于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及其质量的增加,其余0.65%则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丹尼森的工作确立了人力资本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不过,不同的时代,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也有不同,上世纪60年代,技术进步扮主角,随后的技术匮乏时期则是劳动力起主导作用。 我国的增长模型显然与具有先发背景的发达国家不同,增长的源泉更多来自后发优势,类似于日本和韩国追赶模式下的增长。1962年阿罗在其《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知识变化模型,阿罗认为,学习只有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尝试时才会发生。对厂商来讲,最主要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尝试便是生产,是投资,技术进步是投资的非故意副产品,也就是说,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由资本积累所决定的。但“干中学”显然更有利于学习者——不仅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经验而提升其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生产率了。技术不仅为创造技术的企业所有,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技术或知识还为全社会所共有。有关“干中学”,经济学界曾经找到过一个完美的例证,美国多家船厂在“二战”期间生产一种货轮,3年间共生产了2400余艘同规格的船只,结果是随着累计产量每翻一番,不同厂家每建造一艘这样的船只所需工时数下降率在12%到24%之间。 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2年出版的《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里,比较了菲律宾和韩国在20世纪后半期的增长差异。1960年,韩国和菲律宾的各项经济指标几乎都相似,人口总数都是2000多万,都有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人口,城市化水平接近,教育状况相仿。可1960年到1988年间,菲律宾年均GDP增长率为1.8%,韩国人均收入以每年6.2%的速度增长,以这样的增长速度,每11年收入翻一番。增长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是,30年间韩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倍。“干中学”当然也有它边际效用递减的一面,小范围内的技术最终扩大到大的范围,被更广泛地应用,也就没有了生产率优势。卢卡斯注意到,几乎所有创造了奇迹的国家劳动力都不断向更尖端的产业转移以不断获取“干中学”的利益。 在经济学家的解释中,对人力资本的积累甚至与一个国家自身原有的知识水平无关,而只和自身的努力程度和世界知识的现有水平有关。在一个知识自由流动的世界,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尤其互联网的出现,更可拿来解释我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而学校教育对GDP的影响相对要弱,丹尼森的估算,在美国只有0.9%的增长归因于学校教育,另0.5%归因于其他因素。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更是这样,即使把入学率提升了一倍,也只意味着每年的劳动力里多出很小比例的高技能劳动者,很难与动辄双位数的增长率匹配。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解释经济奇迹的模型都以小规模的经济体为对象,建立在资本和货物的自由流动上。尽管劳动力的流动受到相当限制,但知识的传播却是自由的。资本和货物之所以追逐劳动者,除了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还应该是因为当地人力资本在迅速提升,从而给资本带来超额收益。这样的逻辑链条下,“干中学”,也就是在职学习就成为最重要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方式。在职学习若要持续不断地发生,管理者和工人就必须不断地接受新任务,并且是技术水准不断升级的任务,这又只能发生在外向型经济里。外向型经济虽给这些国家以巨大增长空间,却隐含着危机,因为贸易的单向流动从长远看是零和的,双方只是短期收益,就像现在的信贷危机,资本和货物不能双向流动,结果是经济危机。这样的思路下,也只有一些经济规模小的国家能通过这种方式超速发展,若整个第三世界国家都采取出口战略,很快就会触发危机。 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经济学家的解释可谓林林总总,除了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成功,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是市场经济提高了效率,一种观点则是政府对产业的扶植。无论哪种解释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却不免以偏概全。实际上,无论是日本还是“四小龙”,其发展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发展随时因国际环境而调整。起初多个国家选择了赶超战略,一旦发现资源不足以承受发展重负便改变了战略。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东亚国家都能够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进行赶超。并且,随着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以这样的思路考察,我国的经济增长也从未有过想当然的模式,而是随时因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调整,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中释放出制度变迁的红利。 对经济的超常规增长,如果说存在着一种“万能”的解释,那就是基于技术扩散的全球增长模型,该模型假设世界各国在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每隔若干年一批国家被“放出”,加入增长的行列。这一个模型里,首发国家肯定是增速最慢的,后发的则因技术扩散的因素每一批速度都会有所提升。我国作为最近一个起飞的国家,受益于先发国家技术的一层层积累,于是有了最快的增长速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