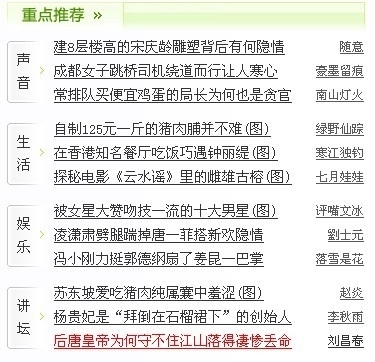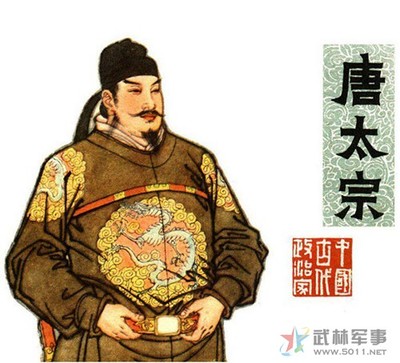那时候巴地的边缘地区,就是用盐和布匹充当货币的。巫峡一带,则用水银、朱砂、象齿、彩绸、头巾等等充作货币(见《唐会要》)。汉中一带的风俗,就更具有乡土气息,不但现钱极少用,布帛也很少用。老百姓到市场,都是物物交换,比如要买盐的话,拿一斤麻或一两丝去换,再不然鸡鱼鸭鹅也都行。这样的“原始贸易”,虽然看上去换算好像很复杂,但老百姓却觉得很方便(见《元稹集·钱货议状》)。云南地区,在唐代那个地方叫做“南诏国”,也就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小王子”段誉的家乡。南诏国就一直不用金属货币,用的是贝币和绢帛。 虽然大唐的货币五花八门,但是政府却没把金银正式算在货币序列里。中唐元和三年(808年),还曾一度下诏禁止开采银矿。可是金银即便不再是法定货币了,它们在民间还是具有货币的功能。在岭南,因为外贸发达,人们甚至只把金银看做是货币。 晚唐诗人韦庄写的著名诗篇《秦妇吟》,也说黄巢起义时,长安城里“一斗黄金一升粟”。看来在特殊情况下,黄金也可以用作支付。这没有疑问:金和银,永远是和“财宝”连在一块儿的。有的东西,虽然号称是财富,但是很虚。比如股票、基金、期货、股指期货,那只不过是账面数字,你把钱投进去,它要是给你“虚”掉了,你是无论如何也搞不懂是怎么被“虚”掉的。 可是你买银行的金银币,即便价格再跌,也没有一种是跌到面值以下的。如若不信,你今天就可以到银行去确认。 不是有一首歌说“太阳是一把金梭,月亮是一把银梭”么?那我们不妨也可以这样理解:金银之价值,就如日月之永恒。 在古老的钱币上,铸有日与月的标记,其意义也在于此。这是古人在向你暗示一个真理——钱,永恒也。 五代的货币政策各有高招 我们该向辉煌大唐挥手说再见了。读史,这大概是最不忍释卷的时刻。华夏民族古代的面子,全都在大唐这里。 各位读者即使没到过日本、韩国,总该吃过日本料理或韩国料理吧?看到那种精致、那种彬彬有礼,我就能感受到大唐之风。就更不要说那些衣袂飘飘的女性服装、那些白墙黑瓦的清雅宫殿了。 这本来都是咱们的。 “礼失求诸于野”,我们现在还能说什么?好好的大唐,被无数的野心家你一榔头我一榔头,给敲打完了。毁坏自己的国家,就像毁坏无主财产似的,不知这些人脑袋是怎么长的? 唐一亡,果然就是乱纷纷的五代十国。就算是霸主、枭雄、草头王,也免不了人头滚滚,直闹腾了半个世纪。其间出了无数的皇帝与“国主”,但没几个是雄才大略的,都是能玩一天算一天。华夏这个经济上的务实民族,在政治上为何又如此虚无?还真是值得研究。 现在,我们来看五代十国的钱币。 先弄清五代是哪五代,我们好心里有数:按顺序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些国名之所以都有一个“后现代”的“后”,是因为从周朝起,这些国名都有人曾用过,加个“后”是以示区别。这些朝代的首都,除了后梁是在洛阳外,其余的都建在开封。 五代的各朝,都铸过自己的“元宝”或“通宝”,形制和重量一般都仿照开元钱。 唐朝遗留下来的缺钱的问题,在五代仍然存在。其中后唐也曾经效仿唐朝,下过禁止蓄钱的诏令,同时还禁止商人携带钱币出境。后唐明宗时,还进一步规定,商人不准携带500文以上的钱出城。有钱,你就在城圈里可着劲花吧。 这样的限制,简直没法让人做生意了,超出500文价格的城乡贸易怎么进行? 以往在唐朝,因为钱不够用,所以官方认可“省陌”的做法,不过有规定,一般是800文到900文为一贯。到了后唐,每贯钱“短”得越来越厉害,朝廷不得不下令,必须维持在800文一贯的标准上。市场稽查员一旦查到在交易中以“短钱”支付的,所有钱币一律没收。政府为什么要管“短钱”的事呢?——不涉及它的利益它怎么会如此热心? 原来,民间流行用“短钱”,实际上是市民自发地把手中的货币升值,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皇家和政府的财富就会缩水。所以必须采取强制措施,让足够数量的货币在市面上流通,以抑制货币升值。缺钱缺得各朝皇帝都抓了狂。 到了后晋,钱币发展史上还出了一个小小的逆流。后晋太祖皇帝、也就是那个著名的卖国贼石敬瑭,大概被缺钱现象困扰得太苦恼了,就颁布了允许自由铸钱的法令,当然他不是傻瓜,同时也规定了严格的标准,要求重量一定要与开元钱相同。 但这个法令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各地都缺铜料,你让民间铸造足值的钱,怎么可能?结果法令颁布一个月后,就不得不放宽限制,说铸钱也可以略轻一点。

咱国的法律就怕没弹性,只要有弹性,咱国的人就能钻空子。这个口子一开,各地豪门富商就开始动脑子啦,铸的钱,简直五花八门,轻重不一,大小不一。贪心之徒更是往钱里狠命地掺铅掺锡。后晋的钱币样式,成了万国博览会,在流通领域引起极大的混乱。石敬瑭的自由铸币政策,得不偿失,实行了还不到一年,就只好匆忙收场。 这样儿戏似地治国,国运想长久那是太难了。后晋传了两代就完了,接着的是后汉。 在“省陌”问题上,后汉有一位宰相王章很有创意,他规定了一项官库出纳制度,就是百姓缴纳官库的钱,以“八十为陌”,而凡是官库支付百姓的钱,则以“七十七为陌”。比值上虽然只有小小的差异,但官府就是要占你这一点便宜。又来这一套。这样与民争利争到如此斤斤计较的政权,怎么能长得了?后汉也只传了两代就完了。 五代的最后一个朝代是后周。后周的第二个皇帝,是一位有名的明君——周世宗柴荣。他是后周开国皇帝太祖郭威的内侄和养子,后人习惯称他“柴世宗”。柴世宗文治武功都有一套,所做的事当中,也有一件与钱币有关。那就是他也学唐武宗灭佛。他下诏废止了全国3万多所无皇家执照的寺庙(非敕赐寺额者),从这个数字来看,他要比唐武宗狠得多。考虑到各州县已经有好多年没铸钱了,而民间却大批销毁铜钱造器皿、铸佛象,于是柴世宗限令被撤销的寺庙,在50天内把所有铜像铜器拆毁,送交官府用来铸钱。民间百姓有藏铜的,也要在50天内上缴,官府照价给予补偿。过期匿而不送的,要重罚,五斤以上的死罪,一斤以下的判徒刑二年,还要株连邻里和“居委会”的负责人。 铸钱缺铜,害得佛寺屡屡遭殃,看来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尖锐了。当历史再也无法负荷一个沉重的包袱时,甩掉这个包袱、变通一种做法的可能性,也就随时会出现了。 接下来再看十国。这十个小国,大都算不上什么像样的国,也没有统一中原的志向,割据一方,混一天算一天。先混个皇帝或国王做做,等到哪天天塌了再说。 这其中,有六个国家有自己的铸币。我在这儿给他们点一下名。不过即使点了名,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它们是在什么方位,那我就连它们的“首都”也一起点出来,这样就能明白个八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