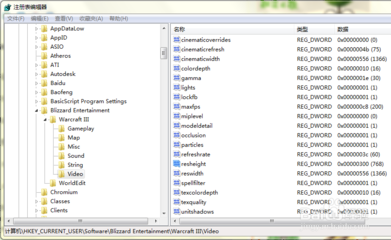在3天后5月2日的苏富比春拍上,虎首的底价升至320万港元,易苏昊同样代表保利竞拍,以1400万港币胜出。易苏昊回忆说:“当时的心理压力实在是太重了……毕竟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各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有人甚至还提出反对。但当时既然决定让我来做这件事,我就只有一个念头,把它拿回北京,拿回故乡,别的都是次要的。当保利公司最终将它们拍回时,整个竞拍现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许多人眼里含着泪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站起来鼓掌。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完满的结局。”
三件兽首铜像最后的成交价共3300万港币。易苏昊也不止一次地被记者追问,当时是否不管价位多高,都志在必得?他说,当时还是有一个心理价位的,用超过底价一至两倍来拍得,对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来说,是很正常的。更何况,“这表现了一种中国人抢救中国文化的决心”。易苏昊反问:“中国人民的情结难道能用钱来衡量吗?”在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赵榆看来,2000年首批三件兽首回归有其特殊性,“其‘身价’还包含了爱国的感情价值”,“从文物本身的角度看,这个价格已经到了上限”。 可到了2007年,圆明园马首出现在10月9日的苏富比秋拍时,估价已经高达6000万元。在各方抗议和斡旋下,这次马首终于没有出现在拍卖场上,因为9月19日,何鸿燊以6910万港元的成交价购回马首铜像,并捐赠给国家。而现在,鼠首和兔首的估价,在皮埃尔·贝杰的个人拍卖行和佳士得的共同运作下,再创新高,分别为800万至1000万欧元。对于这个离谱的价格,赵榆认为“兽首的价格应回归文物本身的价值”,“应根据它的历史、科技及艺术价值衡量它的经济价值”。可在精明的拍卖场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对于海外流失文物的重视,文物背后蕴涵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显然已经成为各种竞价把戏求之不得的操控砝码。 一波三折的变局
鼠首和兔首的露面,重新点燃了刘洋的激情。当他的诉讼想法再次被媒体传播后,意外地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法国华侨的电话,对他表示钦佩和支持,并建议他组一个律师团。“这个想法一下子点拨了我。”刘洋觉得,其实当他走出第一步之后,慢慢地就开始有各种力量汇拢过来,推着他往前继续走。 刘洋通过博客发表了他热情洋溢的起诉书,希望组建律师团队。他也很期待地每天去查看点击率,当点击率到了2万的时候,终于出现了第一名主动和他联系的律师。接了一些电话之后,刘洋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可以主动出击,于是又自己在网上搜索寻找伙伴。他有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小通讯本,上面也有不少被划掉的电话,那些都是拒绝的。被拒绝多了,刘洋也慢慢找到了规律,“如果一接电话就表示原意参与的,基本都没问题,而那些表示要考虑,让我先寄材料的,多半没戏”。就这样,在2009年1月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这个通过网络和电话组建的律师团队成员已经超过60名。 牛宪锋一直关注着刘洋的行动,海外文物追索的圈子其实不大,在民间组织方面,目前只有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牛宪锋当然知道刘洋,也认同他的热情,只是回到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两人还是分歧严重,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牛宪锋觉得,有一个原意扛起大旗的人总是好事,先把舆论声势造出来再说,这样才可能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1月17日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牛宪锋也去了,同去的还有圆明园管理处的几名工作人员。可是热情洋溢的只有刘洋一个人,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还是觉得心里没底。牛宪锋也发现刘洋面临着和洛阳龙门石窟诉讼一样的问题——缺少合适的原告。
这个刘洋也知道,他试图说服圆明园管理处,但对方也给了明确答复,“自己级别太低,不能做主”,建议他找国家文物局批示。他希望基金会能出面,但却又无法从法律的技术层面说服牛宪锋和他的同事。这场新闻发布会,其实开得也让他有些憋气。他甚至觉得,有些人是故意来给他拆台的。但不管情绪如何,原告问题必须解决。新闻发布会后他也有一些意外收获,有一些社团组织主动跟他联系,但并不算合适,其中有一个就是在香港注册的“全球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现任会长叫州迪,持香港身份证,目前定居广州。
州迪在2005年的时候也曾经是个新闻人物,因为他经常以黄袍马褂长辫的扮相出现在广州街头,言谈举止都异于常人。他自称是多尔衮的后裔,甚至还在“春运”高峰的时候跑到广州火车站办公室静坐,要求以皇室的身份获得车票。虽然他的身份受到了广泛质疑,但他高调坚持可以比对DNA,只是没有人能找出多尔衮的DNA来和他一辨真伪。特立独行的州迪在电话中向刘洋承诺,如果能追索回来国宝,一定捐献给国家。州迪的出现并没有让刘洋格外欣喜,他觉得这个社团作为原告,还是有些牵强。只好在1月23日的时候,又通过博客在网上发文章,寻找原告。可他的热情还是无法打动心目中理想的原告主体。时间一天天过去,刘洋终于还是绷不住了。大年初三,刘洋在从新疆返回北京的列车上终于下定决心,给州迪打电话愿意接受他的授权,让他成为这场诉讼的原告。至于州迪,虽然经历了等待,热情倒也没有受挫,还是欣然答应。 文物诉讼其实是个复杂的事情,走一步看一步的刘洋也越来越发现了这一点,他的团队中出现了一些更专业的人员,有留学法国的律师,也有在法国的访问学者,为他提供了语言和资讯上的更多帮助。比如留学法国的律师告诉他,如果外国人想在法国打民事官司,必须视立案标的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以2亿元计算,两件兽首的保证金就是40万元,而这不过是以后必须陆续支出的庞大费用中的一笔。说起来刘洋自己也有些唏嘘,他觉得自己做律师这么多年,也算有些傲气,没这么求过人,四处告借。2月1日,他通过快递拿到了州迪的委托书,但钱还没有着落。刘洋苦笑:“在40万元来之前,我其实非常愤怒,那时候就有新闻说我们会草草收场,网友跟帖说我们炒作,我们炒作什么了?律师团那么多人,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 最后还是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朋友给他提供了40万元。2月9日,在给佳士得和皮埃尔·贝杰发去了律师函后,刘洋意外地发现,团队中的公关顾问擅自把给对方撤拍的最后时限改成了3天。这让他有些担心,前期的很多准备工作其实并没有完全到位。意外的是,2月11日上午,也是约定采访的这天早上,刘洋突然接到了电话,有朋友告诉他,海外媒体已经发布了消息,说佳士得迫于中国舆论的压力,决定将两件兽首撤拍,改成私下交易,待价而沽。这电话让刘洋很兴奋,他觉得舆论攻势和自己的律师函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他也欣喜地不断在电话中转告其他的朋友,那的确是一种真诚的和物质无关的理想主义的喜悦。 可事情急转直下,2月13日,佳士得向求证的各媒体发布声明,撤拍属于不实传闻。而藏品主人皮埃尔·贝杰始终没有正面应对公众。刘洋的情绪当然被极大地拨动了,作为律师,他很清楚,没有稳赢的官司,但如此努力把事情推向法律层面,他希望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就是阻止兽首拍卖。在这一点上,研究者们都与他持相同观点,海外流失文物的公开拍卖,等于二次掠夺。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也在这一点上与刘洋达成一致,“一定要反对拍卖”,“先阻止拍卖,至于回归的方式,可以再从长计议”。 刘洋打算亲自飞赴法国,使馆方面也与他取得了联系,可临时却发现护照已经过期两个月,只好买了2月15日晚上回海南的机票,赶着去处理护照问题。但法国方面愿意参与这场公益诉讼的执业律师已经出现,据说将在2月16日在法国提交诉状,申请禁制令。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刘洋说,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法律的困惑 已经出现的7件兽首铜像中,除去鼠首和兔首,目前唯一没有拍卖公司介入,而是以公益方式回归的只有猪首铜像。2003年初,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美国寻访到猪首铜像的下落。经过努力争取,美国收藏家同意将猪首铜像转让给该专项基金。牛宪锋记得,在2000年3件兽首就已经拍出了3300万港元之后,兽首的估价已经大大提升,但经过他们的斡旋和运作,猪首回归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总共才花了85万美元,不到600万港元”。这笔钱同样来自何鸿燊。 这些圆明园兽首也被视为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劫掠、盗凿、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流失文物大多数散落民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海外流失文物被更具体的界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战争、劫掠、盗凿等各种原因流失海外的文物。我国追讨海外流失的文物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叫回购,就是自己花钱买回来;第二种是回赠,就是爱国人士花钱买回来再赠送给国家,但花的也算是自家人的钱;第三种就是通过外交或者民间组织的沟通协调,把文物给要回来。但是要实现这三条都非常难,因为这些文物数量庞大,如果仅仅依靠回购,需要的是不可想象的庞大资金,至于回赠,也是可遇不可求。所以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们也考虑过通过法律追索的方式。 既然选择打官司,单凭爱国热情和一腔热血当然不够。遗憾的是,尽管文物追索几年前就引起各方关注,却一直没有人列出跨国法律追索的有效途径,甚至很少有人据此发表学术文章。事实上,通过诉讼跨国追索文物,在法学领域也是一个边缘议题。在国内,法学学科一向以部门法为界,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很少有人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而跨国提起文物诉讼,却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文物保护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多个领域。一般说,国际法学者多只熟悉国际公约或国际组织,很少有人精通国内法上的诉讼技巧。国际公约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但真要打起官司,靠的还是各国国内法。至于民法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也是各有侧重,即便有人熟悉在国内怎么打官司,但一旦出国诉讼,涉及的多是其他国家的法律,如果是在英美国家,连打官司都会是与国内完全迥异的一套程序。因此,尽管有人解读了国际法上的文物保护公约,有人提到了民法上的善意取得或诉讼时效,但到底该由谁作为原告起诉,事先如何进行财产或证据保全,原告如何举证,判决后如何执行,这些问题始终没有人认真研究过,或者给出一个权威合理的结论。 牛宪锋说,基金会也通过自己的法律顾问和国外的专业律师接触过,发现文物官司很难打,“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也就只能观望。可刘洋刚好相反,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坚持一步步走下去,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总可以慢慢解决,而如果不做,只是空对空的讨论,只会全部都自我消解了。不过刘洋自己也承认,进入这个领域后,才深刻感受到“法律上的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但不管怎样,在混乱和焦灼中,虽然他的律师函除了激情之外并不能从专业角度得到更多的认同,但刘洋始终没有放弃法律这条需要有人尝试的路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