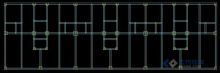作者:汪丁丁
其实,人性始终是一个问题。首先需要讨论而且始终没有讨论明白的,是善与恶的界定问题。终于,大约100年前,摩尔在《伦理学原理》的前言中一锤定音:善是一个基本概念,它不能如复合概念那样被展开为由其他一些语词组成的定义。换句话说,善是无法定义的,它可与其他语词组成一些复合概念的定义。例如,我们常说,舍己救人是一种善行。由于善的这一性质,我们似乎只能讨论具体的善,即出现在特定情境之内的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常是善的,但也可以有例外,因为我所不欲的,未必是人所不欲的。 不善的,只是不能称为善而已,它未必就是恶。关于恶,我们似乎可说得更多一些。例如,卖假货以牟取利润,古今中外莫不斥为“恶行”。一般而言,损人利己的行为是恶的。虽然,这样的恶,仍需要在具体情境之内才可定义。例如,处于癌症晚期的痛苦至极的病人请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我们根据这一出自他的自由意志的请求,足可相信医生结束他生命的行为不是恶的。 发生于具体情境之内的行为,不论它是善的、不善的或是恶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证,我们对行为的判断必须以“充分知情”为前提。例如,我们常以酒会友,但若我们劝朋友饮一杯毒酒,那么我们这一行为的善与恶,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知道酒有毒以及毒性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与那位朋友的福利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因果联系。诚如摩尔所言,这些因果联系的链条无穷无尽且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是人类理性可以完全洞悉的,它们的各种效应互相抵消之后的“净效应”的善或恶的程度,只在漫长的实践检验之后才可能被人类理解,并由此而确立一些伦理的“信条”——只因信而服从。因此,这是休谟和哈耶克的看法,我们人类能够生存到今天,几乎完全得益于被认为是群体理性的载体的社会习俗,而不是我们可怜的个体理性。 不错,社会习俗是群体理性的载体。图腾禁忌、宗教规训、祖训及规范,都是习俗的一部分。就行为方式而言,习俗构成了文化传统的主要部分。善和恶,于是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斯密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在一些民族那里是善的行为,被另一些民族视为恶行,反之亦然。
符合群体理性的未必符合个体理性,因为有利于群体的行为可以是不利于个体的。有鉴于此,哈耶克相信,今天的人类社会,必是“基因演化”与“文化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文化的演化,大致而言总是朝着保持或强化“互惠性”的方向发展的。对诸如诺贝尔奖得主弗农·史密斯这样的经济学家来说,互惠性不仅意味着个体与个体或群体与群体相互之间的好处,更重要地,它还意味着每一个体或群体对那些违背了互惠原则的个体或群体给予惩罚的义务。此外,还有由政治科学家埃克斯尔罗德的仿真实验揭示出了重要性的“高阶互惠性”——即个体或群体对那些不惩罚违背了互惠原则的个体或群体的惩罚。诚如佛家所言:“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 这就涉及另一类的恶,即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里面多次提到的战争之恶对于人类各国的健康发展,犹如树木为争夺阳光而相互排斥可迫使树木向上生长,是一种必要的恶。换句话说,为了最终的或更高的善,我们有必要容忍甚至实施某些作为手段的恶。显然,这是一种极易引发争议的见解。 仔细辨认,我们生活中还存在着第三类型的恶,它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恶(badness),它被称为邪恶(evilness)。邪恶的特征在于,它与康德所说以恶的形式诱使我们向善恰好相反,是以善的外表诱使我们尽力发展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恶。例如,我们承认,市场交易是实现互惠性的一种常见形式。交易于是可以拓展到我们行为的许多方面,包括“出卖灵魂”的行为。所谓诱使,就是不易被察觉地发生着的行为,从符合伦理的到不符合伦理的,再到有意识违背伦理的行为,往往是一个连续的谱系。我们在由不恶向恶的曲折路径上走着,每一步都有理由——至少我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理由,直到某一步,在那之后再也没有理由,我们无可挽回地堕落。邪恶的人,就是自认有资格诱使我们走到那无可挽回地堕落的最后一步的人。真正困扰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邪恶的人,是为了什么目的实施邪恶的行为呢? 我仔细想过,没有答案。因为,凡有目的的行为,要么是为了私利,要么是为了公益。这两类行为,尤其是前者,可以是恶的,但通常不会是邪恶的。很久以前,我是这样界定“邪恶行为”的——它必以“邪恶”本身为目的。换句话说,邪恶之人之所以邪恶,是因为他们只能通过邪恶行为本身来获得幸福感,哪怕为此而害了他们自己。这一类型的人,佛家称之为“魔”,必斩之而不能渡众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