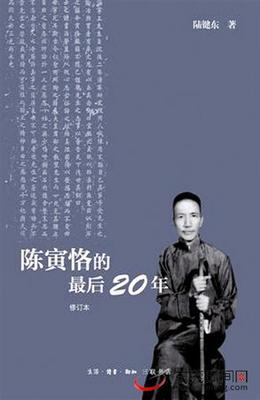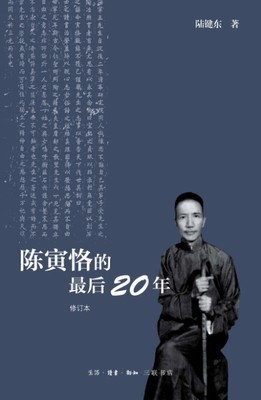系列专题:《贡献者:怀尧访谈录》
吴怀尧:最近,你的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北京晚报等数十家媒体连载,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聊它,各方面的评论也是此起彼伏。透过你开启的历史门缝,我们得以领略民国初年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落的命运剧变,请你谈谈这本书的创作初衷。 岳南:我上中学的时候,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人与事就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号称“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报纸刊物上开始宣传知识分子与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信念与追求等等,比如像数学家陈景润,“文革”时期独自猫在北京中关村一间小屋里,默默地破译“哥德巴赫猜想”,这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典型,是我心中的偶像。还有事业加爱情的,如《第二次握手》主人公的生活与凄美的爱情故事,通过《中国青年报》连载,让我知道了原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和事。

当然,真正产生要为知识分子写点什么的想法,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了。随着政治不断解冻,一批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并在我眼前晃动,当我静下心来较为详细地研究一番时,这批自由知识分了的人格魅力与渊博学识,令我深受感动,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这就是后来你所看到和我正在创作着的自由知识分子系列作品创作的初衷。 吴怀尧:在20世纪初叶的学术大家中,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寅恪、傅斯年、赵元任、李济、陶希圣、钱穆、顾颉刚、郭沫若……个个大名鼎鼎,许多人的成就至今都无人能及,你为什么对知名度并非最大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情有独钟? 岳南:写作这种事,不能说谁的世俗名气大就写谁,也不能说写大总统就比写小人物更有意义和更受读者欢迎。主要还是看作者与所写的传主是否在感情上有所共鸣。心是有弦的,没有拨动你的心弦,再伟大、重要的人物也激不起你创作的欲望与冲动。这一点我想你能理解,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莫伯桑的《羊脂球》等等,他们所写的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应该说大多都是些社会中的小人物,甚至是在世俗社会看来最低层的妓女。但就是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感动了一代代人,这些作品也在世界文学史上放出了不朽的光芒。 我对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自由知识分子情有独钟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学识特别是人格魅力,比之前面列举的其他几位更能打动我,更容易令我的心弦为之跳动。或者说,在潜意识里,我觉得这两个人更能使我产生一种亲近和温暖的感觉,心灵更容易沟通。就这几个人论,梁启超的色调有点冷,也就是给人冷冰冰的感觉;王国维有点软,有的时候你看他处理的那些公事私事,我都替他着急,真是像鲁迅所说的“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人物,对于这种性格的人我不喜欢;胡适与鲁迅嘛,此前写的已经够多了,我不愿意再去炒别人的剩饭,或者是在混水里摸鱼;赵元任与李济的专业有点深奥,要解释起来难度大,读者不容易搞清楚,一时还不好动笔;陶希圣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政客,可佩的地方不多;钱穆与顾颉刚学问当然是没得说,但总觉得缺点什么,要写一部传记,兴趣不大。至于近几十年在大陆政学两界名声显赫的郭沫若,一生翻云覆雨的事太多,鲁迅当年对郭沫若等人指斥为“才子加流氓”,或许有个人恩怨,不可当真。前些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对郭氏也有过一个评价:对自己的为人为学“没有自信”,所以没有自信,是缺乏“自约”精神。关于郭氏其人其事,我研究的不多,弄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在上面列举的人中,我最喜欢的是傅斯年,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很称我意,这可能牵涉我与傅公同为山东老乡的地理关系,骨子里都有一点山东响马与梁山好汉遗风的关系吧。 吴怀尧:对于傅、陈而言,他们各自的历程都跌宕起伏,可独成专著,你把他们放在一起写的原因是什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