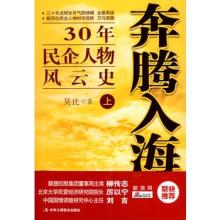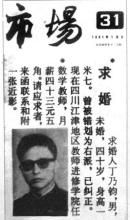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7日发文《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30日,又发文《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两个文件口气严厉,措施细密,均被要求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进行刊登报道。一时间,“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度最重要的经济运动。不幸的是,决策层做出打击“投机倒把”的决定,竟然出于这样一种判断: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新兴的私营经济正以无孔不入的姿态,与国营企业争夺有限的资源。由此,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打击。在这种局面下,众多在改革开放前3年事业小成的私营经济业主们被“纷纷错杀,并引发桩桩公案”。有的案子闹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典型性的一件是淮南市谢家集贸易货栈起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执法不当案。3月,这家货栈从内蒙古购进葵花籽3.5万公斤,经主管部门批准以批发价每公斤1.48元、零售价每公斤1.68元出售。但当地区工商局经市工商局批准,以货栈擅自提价支持职工搞“投机倒把”为由,进行罚款。货栈不服,四次向市有关主管部门及市财办报告,要求处理,均未获结果,最终提起诉讼。此时,与私营经济举步维艰相对应的是,投资数百亿,正在建设的上海宝钢项目即使承担着来自各方面的指责,但也自然不会因为非议而停下脚步。被错杀的小私营业主中有个叫严介和的人。从78年底开始,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让体制和出身的壁垒逐渐消融。严介和意识到改变命运的途径不再局限于读书和教书这一条道路上。当时,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的他,成功地挤进了一所中学的民办语文老师队伍。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改革大潮风起云涌的同时,体制遗留下来的思维惯性对人的影响还是无法短期消除。僵化滞后的教育体制成了一道难过的关卡,严介和想要把民办老师的身份转正似乎机会渺茫。而那时民办教师工资只有十几元钱。这位白天在讲台上意气风发的年轻教师,晚上回到家中却内心沉重、辗转反侧。明天该怎么继续?下一步该向哪里去?突破限制,有可能获得成功,也有可能面临危险。更好的事业是严介和想要的,丢掉教师饭碗却是他不希望的。前途,成为摆在严介和面前一道艰难的选择题。对于害怕危险的人,这个世界总是危险的。当了解到附近烧砖的窑厂需要大量的柴帘子搭盖砖坯挡雨时,严介和心动了。一张草帘子卖出去能赚一两毛钱。利用闲暇时间,他边骑着自行车到周边窑厂联系销售业务,边组织同村的青年收购芦苇编织草帘子,一个月轻松能赚几十块。不久,他搞起家庭手工作坊搞编织,编一些草帽、斗笠、簸箕等在集市上卖。做大了一些后,他又陆续组织一些人编草帘子,自己收购,再卖到窑厂。良好的经济效益在翻番,严介和成了淮安有名的有钱人、万元户。可是,在村民的举报下,严介和变成当地部门眼中“资本主义”色彩的典型,有关执法部门取缔了他的家庭作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