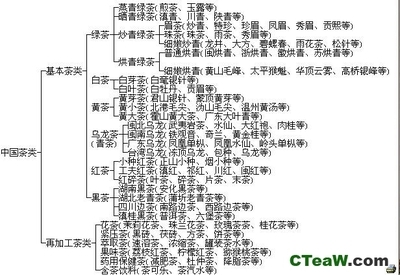2005 年是郑和远航 600 周年,官方和民间都热闹了一番,纪念活动引发了怀旧情绪和民族自豪感。中国曾经有能力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一部世界史最终却以另外的形式写成,令所有现代中国人唏嘘不已。
永乐至宣德年间(1405~1433),郑和七下西洋,探索印度尼西亚水域(南洋)和印度洋,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斯时,明朝国力臻于高峰。但是很快,明廷不再主动向海洋发展,而欧洲却在这段时间大胆进取。
欧洲在商业上和政治上扩张到印度洋和东亚的历史,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即: 假如当初不曾是那样,又会是怎样。假如印度当时不曾沦于各土邦与土库曼入侵者之间的战争,假如中国当时不曾奉行孤立主义,假如亚洲在 16 世纪不是处于那样一个低潮,从而让自己暴露于欧洲入侵者无情攻击的面前,那又会是什么情形?
在所有的“假如”当中,中国的“缺席”这一点尤其事关重大。郑和的船队在气势上远远超过后来者葡萄牙的小舰队。船队的船名列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据文献记载,郑和一号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它的排水量达 14,800 吨,载重量 7,000 吨,有 9 枝错开的桅杆和12 张以红丝料制成的方形大帆。这种宝船并非战船,而是为了装载各色宝物、安置天子使臣和外国贵人而设计的。其他船只满足另外的各种要求: 8 桅杆的“马船”将马运往南亚,船上还载有建筑和维修材料; 7 桅杆的补给船,主要运输食品; 6 桅杆的军运船; 5 桅杆的海战船; 与海盗周旋的快船。船队还包括运水船,以保证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淡水供应。每艘船都有数百水手与士兵,证明中国在造船、航海和海军组织方面技艺高超。
对中世纪的欧洲而言,这样庞大的船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中国向大海和全世界开放的这一番努力最终化为乌有,实际上是故意把它化为乌有。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再多做一点努力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大西洋?为什么欧洲来访者到达中国海面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仍然没有中国的船只抵达欧洲港口(第一艘到达欧洲港口的中国船是一艘外交船,参加 1851 年伦敦的大博览会)?像通常那样,原因是多方面的。
经济史学家戴维8226;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分析说,中国人当年缺乏足够的眼力和目标,特别是缺乏好奇心。“他们的航海活动是为了炫耀天威,而不是开眼界和学习; 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留驻; 他们接受尊敬与进贡,而不是去采购……与欧洲人不同,他们并不为贪心和激情所推动。”
在路易斯8226;利瓦塞斯所著的《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对郑和航行的丰富、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利瓦塞斯说,这些航行与贸易的关系并不完全清楚。这些船只带著宝贵的商品如丝绸和瓷器,目的在于交换,但交换显然不是在自由市场进行的,而是通过礼物赠送的方式进行: 蛮夷进贡,中国恩赐。如果贸易是目的之一,这样做成本就太高了。
中国的贸易冷漠是与儒家传统相联系的。重农抑商是正统的儒家观念,明朝秉承这种观念,对内陆的贩货商人制定了复杂的规定,外出贩货要申请人数、行程路线及货物种类数量。明朝开国时,名义上允许中国船舶出海贸易,事实上处处限制。一艘出海贸易的船只,通常申请不到准许出海的“票号文引”。不仅如此,明朝还把对外贸易中的若干重要输入品和输出品一概列为“禁榷”,除了政府专营,他人概不允许涉及。商人们在对外贸易中还要负担一笔很重的赋税,即所谓“报官抽分”。
在朝廷内部,一批儒家士大夫认为农业才是惟一真正的财富源泉,他们憎恨那些筹划和实施出洋远航的宦官。两派争权夺利达数十年之久,有时这派得势,有时那派占上风,但国家的财政状况和传统道德观念却站在儒家士大夫一边。航海的庞大费用使帝国财政捉襟见肘,而且不得民心,因为赋税和徭役已榨尽老百姓的血汗。
此外,贸易冷漠也与王朝法制有关。寻求贸易就意味著中国需要外来的货物,而这种需求的表达与龙座的威严是不相符的。研究者认为,唐、宋的朝贡体制是相对理性的,在礼仪之外都留有大量的空间允许纯粹的贸易,而明朝把朝贡体制完全礼仪化,变成了一种怀柔远人的东西。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航海活动是官办的。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它的脆弱性─今天还在执行,明天就可能被停止。在欧洲,即使探索通往印度的海上之路等皇家项目也有个人倡议的缘由,这是参与集资和确保理性的源泉。在中国, 民间的商业力量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这种背景下,明帝国终于决定: 不仅停止海洋航行,而且抹去过去的任何记忆,以免后代受到诱惑而恢复蠢行。自 1436 年始,选派新工匠造船的请求遭到拒绝,外国要求恢复习惯性恩赐的要求也被驳回。由于缺少船只建造和修理,官家和私人的船队都衰微了。未被守卫的海岸海盗猖獗(倭寇尤为猖狂),中国更进一步依赖内河运输。1500 年,建造两桅以上的帆船者有可能被处死。1525 年,沿海管理当局命令销毁所有出海船只,逮捕船主。最后,在 1551 年,乘多桅船到海上从事贸易也是犯罪。郑和航海活动的档案被销毁,英雄一时的郑和被人遗忘,其航海史被遮蔽了四百多年。
兰德斯以一种历史学家的悲悯写道: “中国选择了孤立主义。天朝帝国又呼呼噜噜数百年,对外面的变化无动于衷,不受影响,保持圆润、完整,似乎安详而和谐。然而,世界却越过了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