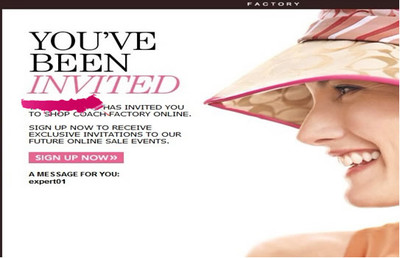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体验一直是好坏参半:一方面,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在二十年时间里,年年保持差不多 10%的增长;另一方面,官僚习气、贪污腐败、文化差异、中美关系的磨擦、法例上的模糊、通信条件不好、外汇短缺等等,差不多想得起来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存在。一般而论,在中国办企业比在别的典型的地方要多花四倍的时间,可是,一旦办成,所得利润常常又大得不成比例。约有一半的西方和日本在华企业报告说他们有赢利。根据卡尼公司(A. T. Kearney)的一份小型抽样分析报告,40% 的外资企业有赢利。问及日本公司在华赢利情况时,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的一位官员估计,约有一半是赢利的。哪一半呢?他说,中国南方,靠近香港的那一半一般有赢利,而北方离北京近一些的地方一般是亏损。在大陆的数万个港台企业的成功率高得多。而那些久经世故的西方公司,因为有了在第三世界的丰富经验,经常也有巨额利润。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雅芳、宝洁、摩托罗拉、IBM、康柏、柯达、强生和其它许多公司都表明,中国市场还是大有钱赚的。
哪怕成功的公司,也都经历过痛苦的投资酝酿阶段。IBM 公司历经多年亏损,最后给该公司中国经理最后一年时间:明年再不挣钱我们就走。那一年挣了一点,但接下来的几年利润大增。麦当劳在香港的经理花了两年时间才说服了广东省政府:让麦当劳进来会提高全省的食品加工技术。后来,他们又不让进口非用不可的爱达荷土豆,而这种土豆是制作炸土豆条所必需的,那是麦当劳的看家绝活。在随后漫长的几个月里,这位扛着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博士头衔的经理,坐火车从香港把一皮箱一皮箱的爱达荷土豆拎到广州去。最后,爱达荷土豆业在广东的山岭上生根发芽了。这次拎土豆的结果,是在这里产生了全世界最忙碌、最赚钱的麦当劳快餐店。
向总部解释在华业务,有时候也要用一点实用主义的办法。麦当劳香港公司的那个人,他是怎样在中国大陆创办起业务来的?“请记住,麦当劳在美国的那帮人是芝加哥人。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我对他们说,广东是香港的一部分。”(广东省的面积相当於法国,人口是香港的十倍。)
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生磨擦的时候,有时候会弄出火来。在典型的大型合资企业里,当地的业务领导人基本上是政府官员,年薪只有四千到五千美元。外藉负责人有美国加州式的房子,有探亲假,有辛劳津贴,孩子们都上私立学校,年薪远高於5,000 美元──一般来说,聘用一位外藉负责人的总成本是五十万到一百万美元。当地负责人知道这些后会说:“这些西方帝国主义者完全是在中国抢劫,就跟一个世纪以前一样。”由于要得到任何额外的大笔补偿是非法的,因此,为了平衡一下,他要求公司分配一部梅塞德斯 500 轿车给他家人用。外藉的负责人大摇其头,说:“这些中国人都腐败得不行。”
不管严重程度是否逐渐减轻,无处不在的贪污行为使美国人甚为恼火,他们得担心美国国内的“外国人贪污行为法”会帮助亚洲和欧洲的竞争对手,这些人当中有些还可以从纳税申报表上扣除掉贿赂费用。中国人在毛泽东的时代曾享有最干净社会的好名声,他们认为,贪污腐败是西方资本主义带进来的一种堕落。当然,事实上,把资本主义的财富与社会主义复杂的规章制度和收入低廉的官僚放在一起,贪污腐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不过,中国的腐败情况虽然普遍存在,比起印度尼西亚、泰国或者菲律宾,那还算不得大问题。在中国,最高层领袖(邓小平、江泽民、朱 基)都清白得无可挑剔,这在亚洲是罕见的,因此也使中国免于沦入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或差猜时代的泰国等因贪污腐败而引起的社会动荡。

中国首次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时是如此神秘莫测,只有一些香港人才能成功渗透进去。港商经常夹着大卷的印花塑料北上进入广东,租一处东倒西晃的小地方,教当地的农村姑娘把塑料剪、折和钉成漂亮的购物袋,上面都印花花绿绿的著名国际品牌徽标。微不足道的资本,没有技术,一点点技巧,有限的风险。当地政府还经常不能供应许诺的水电,因此,一家人从香港出发时,往往带着一台便携式发电机和成罐的煤油。不久,数万种这类的生意开办起来了。而纽约和法兰克福来的那些人,他们带着厚得象书本一样的合同、复杂的进度表以及精确到毫米的工厂规格,那个时候却都一事无成。
但是,哪怕是只有简单要求的香港人,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对中国工人来说,质量简直就算不上一件事。说什么衬衣扣子必须正好钉在那里,一英寸也不能偏,说什么扣眼必须正好与扣子一般大小,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就好象是外国人奇特的怪僻。当时,人们对服装的考虑长期以来只在于布料够不够长,能不能盖住人体的一些重要部分。把事情办好需要培训、纪律、激励措施和工作实践。一家制造玻璃的公司把事情摆顺并赚到钱以后,把全厂的工人都拉到海南岛去度假。那家美国公司的总裁说,那些工人一辈子都没有挨近过飞机,看到他们热切但又有些害怕地钻进飞机的情景,那是他一生最激动的时刻。中国开放改革才不到十年的时候,许多声望甚高、一丝不苟的西方名牌公司就已经在中国生产他们最好的产品了。走进纽约的布鲁明戴尔连锁店,许多最有名的服装上都有“Made in China”的标记。在中国制造的柯达胶卷,化学药水的涂布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均匀些。
对于许多更著名的公司来说,几乎跟管理工人一样麻烦的一个问题是处理好有关劳动力的政治关系。一方面,美国人权活动者和工会谴责这些公司剥削“奴隶劳役”,而同时,中国政府又担心其最好的工人和文职人员都被工资更高的外资企业所吸引,因此把大部分津贴都取走,又从法律上限定外资企业付给员工的报酬。可是,一般来说,外资企业工人的工资还是比当地工人高出一倍,对西方公司的工资标准抱怨最小的是工人。後来,出现了很大的有利变化:允许工人自由择业,允许外国公司选择雇员,这是对资本主义跨出了一大步,对人类自由也是跨出了一大步。
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神秘莫测,这迫使几乎所有的早期西方投资者只好办合资企业。有过硬关系的合资伙伴就象成功了一半。选择合作伙伴非常困难,因为人人都宣称掌握着想要的某种关系。拿着一纸意向书之类的东西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子里转一圈,你会吸引 25 个与外经贸部部长沾亲带故的人。今天,关系仍然起作用,但打通关系的程序已经明了许多了。中国的部长,包括朱总理在内,现在都非常容易接近,完全独资的外国公司也很常见了。
虽然外商在中国做生意有很多困难,可是,外商的条件在许多方面还是比当地人的条件好。早年,外商一般只交当地人一半的税,也没有国营企业的养老金、医疗、教育等等负担。因为差别悬殊,因而造成很多中国人所说的“假洋鬼子”,指的是一些中国公司把钱汇到国外,在国外某个地方(通常是香港)注册,然后作为外国投资者回中国投资。这使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字上涨数十亿美元。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对这种现象加以整顿。
早期的香港投资者建起生产线生产塑料购物袋的时候,在中国的投资几乎全都为了出口。当时中国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基地,某种意义上现在仍然是。全世界大多数的鞋子、玩具及自行车都来自这些外商企业,中国生产的服装足以让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穿一件。可是,进入 1990 年,国内市场已经成熟,现已成为外资企业的最重要目标。摩托罗拉在中国开了一个十亿美元的工厂,生产专供出口的手机,可是,后来发现,中国客户不仅买走了全部产品,还将摩托罗拉设在中国之外其它工厂的余货也买走了。今天,国内市场开始滑坡,可是,它对外国投资者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外商来华投资的早期日子中,最大的头疼问题是“平衡”外汇(进口和将利润汇回本国,必须由该公司的出口支付),以及必须使用由中国政府机关派遣的劳工。外汇和劳工问题现已少多了,但也没有完全消失,并改为依法律原则办事。
大陆的中国人对合同的理解与西方人大异其趣。外国投资者差不多异口同声地抱怨说,真正的谈判往往在合同签署之后才开始。中国人对不可抗力的理解非常广泛,市场状态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包括在内。虽然中国的仲裁深孚众望,美名远扬,可是,仲裁庭的一切几乎都需要改进。法官训练不足,官气严重,办事都需要费用。一名年轻律师描述了中国一家极有声望的法律事务所遇到的一件事,最后因此而丢了最大的客户。该事务所按老一套办法行事,然后把贿赂法官的帐算在这名客户头上,同时还依例把一半的贿赂拿出来为高级律师的妻子买一件礼物。对方律师事务所则把全部的贿赂款花在法官本人身上。因此,这个官司输了,客户也丢了。除开这些问题之外,如果有人真的得到了有利的裁决,经常也是不可能执行的。所有这些问题在第三世界都司空见惯,可是,有关中国市场的宣传使这一点特别令人失望。江泽民和朱 基已把改进法治列为头等大事,可是,他们要完成这项任务绝不轻松。
尽管有这么一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几乎每年都有增长,达到 450 亿美元。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远超过亚军巴西一大截。这样大笔的投资源源不断地流进去,表明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经验证实了中国的确是值得争取的一个市场。
但是今年是个例外。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 1999 年将有大幅下降。中国的增长放缓了,尽管仍然有可能达到 7%,可是,那大都是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假洋鬼子今年什么钱也没有了。香港是最大的投资者,但现在处於严重的衰退中。而且,在 1999 年,双方都要重新评估外国投资的目的和准则。中国正经受一场怀疑浪潮的冲涮,认为外商投资并没有将中国期望并视为最大红利的科技转让进来。这反映了对于科技转让的天真看法,可天真归天真,感触终归极深。不过,最高层无疑希望,而且需要更多外国投资使经济保持前进,因为改革期间,吓得不敢花钱的消费者把每一文钱都往银行里存。外国投资者也在重新思考。经济放缓提醒他们,投资的目的是要赢利。因为一个极大而快速发展的市场所产生的欣慰感,已经让位于投资要赚钱的硬道理。如果中国的改革成功,那就不成问题,可是,1999 和 2000 年看起来不太容易过。好消息是,中国推行改革的管理层到目前为止已躲过震垮亚洲其它国家的金融灾难。坏消息是,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我们才能看个明白,中国的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到底会不会重蹈韩国的复辙。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