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开发内陆地区投下了高风险的赌注
作者: Richard Tomlinson
在重庆,就连本地人也会迷路。这个城市还没建设好未来,就已经抹掉了过去。重庆位于长江上游,距上海 2,400 多公里,二战时曾是中国的“陪都”,现在是有 700 万人口的工业大城市。在这里,到处都是修了一半的公路、快要竣工的办公大厦、刚刚拆毁的建筑物,一幅杂乱的景象。重庆居民哀叹,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街道到了明年是否还会存在。26 岁的张雅薇(音)的花店有可能要被推土机铲倒,她说:“我知道我们肯定会拆,但不知什么时候。”
尽管底层的百姓看不透现状,但中国领导人却很清楚这座城市要走向何方。四年前,中国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打算以重庆为中心,缩小内陆地区与繁荣的沿海省份之间的差距。这一战略得到了大事宣传,其关键是位于重庆下游 580 公里的三峡大坝。七年前,大坝主体建设开工,重庆市及它下属 13 万平方公里的穷乡僻壤被划出了四川省,成为中央政府的直辖市。如今,重庆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拥有 3,100 万人口,其中包括 2,000 万生活在周边农村的农民,400 万远郊区和更远的卫星城镇的居民。三峡大坝将于 2009 年竣工,届时大型的远洋货轮将破天荒地能抵达重庆。环保人士对大坝形成的水库将导致长江淤积感到担忧,但中国的规划者却认为,重庆市会成为中国西南边远省份近 2.5 亿人口的市场的贸易门户。
为实施这一战略,中国正投入巨资,建设庞大的公共工程。如今,在笼罩著重庆起伏的街道的浓雾中,又加进了项目施工扬起的团团灰尘。在 2010 年之前,政府将向 105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230 亿美元。其中的大手笔包括:八条公路、一个单轨铁路网、一套排污系统、集装箱码头以及第二座机场候机楼。重庆大胆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将另有 2,000 亿美元投资资本流入重庆,其中大部分将来自私人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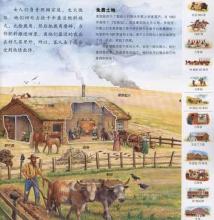
这就是计划。人们都知道,共产主义者的计划均以失败告终,如果这个计划也失败了该怎么办?许多人凭地理因素就对“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否成功表示怀疑。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说:“资本投资总是流向回报率最高的地方。”他指出,最高的回报率来自中国较富裕的沿海省份,它们更接近国际市场。
与深受苏联影响的前任不同,当前中国的领导人也许并不认为他们能推翻经济地理学,不会梦想依靠三峡大坝这样的宏大工程去征服自然。但是,中央政府显然认定他们必须做点什么,以减轻内陆地区的先天不足。中国的统治者担心,如果内陆地区与沿海省份的差距过大,会给维持社会安定带来困难。因此,重庆就被当作了决不能失败的示范性尝试。
尽管重庆正在积极建设桥梁、公路和铁路,但是,能让重庆摆脱共产党数十年来管理不善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六年前只占重庆经济产量的 30%,目前已达到一半。只要重庆的新一代企业家不断增长,他们必将像推土机一样推倒旧经济秩序。
在重庆市解放纪念碑一带新建的商业步行街上,你每晚都可以隐约看到这个城市未来的中产阶级。衣著时髦的青年男女在整洁的林荫道旁漫步,在哈瓦那俱乐部等时尚的新型休闲场所喝鸡尾酒。哈瓦那俱乐部是重庆市第一家拉丁风格的夜总会。36 岁的律师曹平说:“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了。”
去年,受到 39 亿美元公共项目开支的推动,重庆的 GDP 增长率达到了 11.3%。今年上半年,达到了惊人 12.4%。由于中国政府决心阻止经济过热,重庆不会保持这样的速度。不过眼下大多数重庆居民过得还算不错。2003 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近 1,000 美元,周边农村地区农民人均收入 250 美元,均相当于沿海省份的 2/3。由于当地的物价比东部沿海地区便宜一半,所以这一切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是,人均收入不能说明全部。重庆和中国其他内陆城市一样,有人从发展中获益,有人不能,贫富差距拉大了。夏天的重庆酷热难耐,是中国的“火炉”之一。在这儿,因被经济发展甩在后面而感到失落的人非常多。或许有一天,他们的怒火也会爆发出来。
在重庆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挑夫,用竹竿挑著货物,穿行在城市曲折的大街小巷。在渡船码头,你不难听到这些挑夫的怨言。一位 40 岁的四川农民抱怨说:“这里生意很差,我们好多个人抢一个客人。”他每年要在重庆待半年,以贴补种田的收入。这位农民(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一天的收入一般在 2.5 美元到 3.5 美元之间,而吃住就花掉了一半,这使他剩不下多少钱支付两个孩子读高中的费用。据他说,每个学期的学费总共要 145 美元。
在重庆市人民大会堂门前的广场上,可以找到更多对现实不满的人。在夏天大多数傍晚,都会有妇女在广场上跳舞,显出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但当我这个外国记者出现时,一切就变了。有两位 50 来岁的女士争著向我讲述她们的苦命遭遇,讲述她们如何失去了在国有企业的工作。这是自 2000 年以来成千上万重庆工人共同的命运。由于这些工人仍然享受著原单位住房之类的福利,重庆市政府公布的 4% 的失业率并未把他们算进去。其中一位女士原先工作的建筑公司被卖给了私人,她也下岗了。她忍不住发泄起来:“气死我了!我们单位从前的领导从买我们企业的老板那里受贿。”
这些故事是否真实,很难知晓。但显然,尽管重庆的国有企业(包括很多化工、汽车等重工业领域的亏损工厂)仍占城市经济的一半,它们已经毫无希望。希望全在崭露头角的民营企业身上。不过,民营企业自身仍在演变之中。
这类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是尹明善。他今年 66 岁,是摩托车生产企业力帆实业(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尹明善上一次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是在六年前,那时的他还很苦闷。1959 年至 1978 年间,他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尽管已经接受了政府对他受到的对待所做的道歉,但这位身材瘦削、充满干劲的企业家在做生意时仍然遇到了困难。尤令他感到恼火的是,他很难从银行那里得到扩大公司所需的贷款,这些银行更喜欢国有企业。如今,尹明善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银行对我好了,”他说。“我有钱,所以银行就喜欢上我了。”
尹明善忙碌的工厂里张贴了许多中英文标语,上面写著他的经商格言。这些标语意在激励全厂 5,000 名员工不断进取,也为了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在工厂大门口就有一条标语,上面写著:“今天工作不勤奋,明天忙著找工作。”这样的劝诫似乎产生了效果:去年,力帆集团的税前利润达到了创记录的 1,500 万美元,销售额 5.53 亿美元,按营业额排名,力帆集团是重庆第四大企业。如今,力帆集团每年的海外销售额为 2 亿美元,在越南开设了分厂,还计划在印度、巴基斯坦和保加利亚设厂。同时,尹明善还把自己年轻的女儿送往英国的私立学校。他说:“我希望力帆能够成为一家国际公司,所以要她学习英国的语言和文化。”
显然,尹明善的政治待遇也得到了改善。他不是共产党员,也无意入党,但在力帆集团新总部宽敞的办公室里却挂著他与中央政府高官的合影,其中包括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中共宣布承认民营企业家地位的仪式上,他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合影,这张照片同样让他骄傲。他说:“中央政府对民营企业家的新政策有了很大变化。”
当然,尹明善还不能代表绝大多数重庆企业家。阮永开(音)是另一类企业家的代表。他今年 41 岁,从前是物理教师,1996 年创办了一家小型公司─旺国(音)技术研究所,专门生产保持电脑机房清洁的塑料鞋套。研究所的工厂坐落于重庆市西南郊区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上,由两座破败的楼房组成,许多年青妇女忍著高温在里面用缝纫机缝制鞋套。女工的日均工资为 2.4 美元,相当于重庆同类工人的一般水平。研究所看上去像一家血汗工厂,但里面的女工却好像为能有这样一份工作而心存感激。20 岁的赵莲(音)是重庆某郊县农民的女儿,她在广东省的某家制衣厂干过一段时间,去年进入阮永开的工厂。“这里的天气太热了,”赵莲说。
阮永开总在为工厂的利润担心,不过,他的效益似乎还挺好。据他说,去年他的税前利润为 9,700 美元。他估计今年的利润额会下滑,因为他有一半的时间都要待在新加坡,他儿子正在那里读书。阮永开离开公司时,他把生意交给两位副经理掌管。不过,他想在重庆长期干下去。他说: “我希望能在这里生产别的产品。”
类似于旺国技术研究所这样的企业为吸收重庆的剩余劳动力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些企业的增长前景却有限,因为在这个市场中,低成本的小型制造企业已经过剩。为了给发展提供一个更坚实的平台,重庆市的民营企业需要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专业人才,如会计、律师以及懂技术的大学毕业生。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类人才多涌入沿海城市。
每到宜人的周五傍晚,就有许多年轻的职业人士在南滨路演绎著重庆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在三公里多的滨江地区,到处都是餐馆。在这什么都能见到,从香榭丽舍餐厅到怀抱电吉他的长发街头艺人。在一家餐馆,27 岁的重庆女商人严月娟(音)正与几位朋友们聚会谈天。严月娟学的是师范专业,但毕业后她没有去距离重庆市四小时车程的农村任教,而是决定去做生意。起初,严月娟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随后她又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去年她决定自己开公司。“我再也不想给别人打工了,”严月娟说。她的广告公司招收了 12 名员工,尽管她目前仍然与父母合住,但她计划结婚后重新安家,未婚夫是位医生。两人正考虑购买一套价格为 3.6 万美元的住房,以及一辆 1.2 万美元的汽车。
严月娟给公司起名为重庆攀登广告公司,表明她对重庆的未来充满信心。她说:“我希望留在重庆。这是我的家乡。”但是,她的朋友并非都对重庆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其中一位为外国外交使团工作的女孩说:“我的同学大多离开了重庆,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从重庆其他一些年轻职业人士身上也能看出这种矛盾心理。曹平便是一个例子。他出生于内地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家中第 11 个孩子(其中四个夭折)。 36 岁的他经过不断进取,而今终于出人头地。他 14 岁开始学英语,在一所中学当了四年的英语教师。他拿到了大学英语专业的学位,1992 年又拿了一个法律学位,后来他赢得了英国政府的奖学金,去伦 敦学习法律,之后他在广州和上海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去年,曹平决定返回家乡重庆。他用非常地道的英语说:“我认为,重庆市投资在增加,我的机会也会更大。”
如今,曹平是重庆盛世文辉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负责管理公司的国际业务,帮助外国投资商了解中国复杂的房地产开发法律和组建合资企业。他的大多数客户来自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但他也想从西方的大公司那里拉到业务。曹平夫妇和女儿以及曹平年迈的父母一起生活在一个私人住宅区,离他的出生地非常近。但他并不打算扎根于此,而是计划在 40 岁时返回伦敦。“我不清楚自己是否会一直喜欢重庆,”曹平说。“伦敦是我梦想中度过余生的地方。”
在重庆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新重庆,你可以在解放纪念碑附近的商业街和南滨路上的餐馆发现它。另一个是丑陋的旧重庆,尽管城市已经有所改变,但你仍会看到被污染的环境、颟顸的官僚和亏损的国有企业。
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的主厂位于长江边,占地将近 3 平方公里。煤尘和浓烟从工厂的鼓风炉中喷涌而出,遮蔽了夏日的天空。1997 年,公司的一部分作为独立运营的子公司在香港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持有其 62% 的股份。去年,创记录的钢价使这家上市子公司利润丰厚。2003 年,它的销售额达 6.78 亿美元,税前利润为 1.17 亿。
然而,据公司董事长唐民伟说,尽管子公司的销售额占总公司的 75%,税前利润占 80%,但在全公司 3 万名员工中,有三分之二的员工在公司的未上市部分里工作。62 岁的唐民伟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为集团工作。他说:“我的职工太多,管理我们公司比管理一家民营企业要难得多。”母公司不对外公布具体业绩。集团还承担了管理医院之类的社会责任,如果把这些考虑进去,它大概很难赚到钱。集团的员工几乎不关心盈利状况。“我的职工都是靠国家养活的,”唐民伟说,“他们的思维方式很难改。”
这家钢铁公司至少还可以靠香港的子公司活命,而重庆市大多数国有企业却只能被扔进垃圾堆。重庆市的领导似乎也承认这一点 ,但他们仍然抱有不可能的想法,相信通过与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展开竞争,会增强部分国有企业的实力。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就说:“应该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企业开展充分的竞争。”
重庆市政府还在试图吸引外商投资,这么做要明智一些。不过这显然是一项困难的工作。2003 年,重庆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为 3.31 亿美元,而上海获得了 38 亿美元。重庆市吸引的外商投资中将近一半来自香港公司,其中有一部分可能还是借香港企业的壳以避开大陆高公司税的中国企业。部分市政府官员的思想倾向并没有起到吸引外国投资的作用。负责接洽海外投资者的主要机构重庆市外经贸委的一位官员告诉《财富》杂志,当地的通货膨胀率是保密的,它只会透露给那些持有“相关证明材料”的外国人。但是,重庆市最大的发展障碍还是它的地理位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 拉迪(Nicholas Lardy)说:“如果你准备把自己的大部分产品出口国外,你最好把工厂设在上海走廊或者广州、深圳周围。”
对于那些希望向中国市场推销产品的大型跨国公司来说,这话同样不假,因为中国最富裕、人口最多的省份均集中在东部地区。重庆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BP 石油公司就是很恰当的例证。这家英国石油巨头正在为它与中石化集团(Sinopec)、重庆市政府共同运营的乙酸工厂建造一氧化碳的生产设备。乙酸是可以用在食品、纤维和颜料中的化学品,生产乙酸需要一氧化碳做原料;新建的设备可以使乙酸工厂的产能提高 75%,已能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可是,目前已投入了 1.88 亿美元的 BP 公司还是在南京建设另一家乙酸生产厂,因为南京距离利润更高的沿海市场更近。
BP 等全球化企业来到重庆的真正动机是进入当地的市场。雅马哈(Yamaha)在重庆生产摩托车,绝大多数供应的就是当地的消费者。福特公司(Ford)与当地的国有汽车公司长安公司组建了一家小型合资企业,生产嘉年华(Fiesta)和蒙迪欧(Mondeo)轿车。但今年福特又宣布计划在南京建造更大的工厂,其原因与BP 公司相同。
诚然,在有些大型外国公司眼里,重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资源和工程领域的跨国公司就想从该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获利。例如,今年 4 月,法国建筑材料公司拉法基集团(Lafarge)宣布,它将投资 4,000 万美元,用于提高它在重庆开办的水泥生产厂的产能。但重庆市市长王鸿举也承认:“大多数外国投资者更看好沿海省份。”
按照中央规划者的设想,重庆应该是一座光彩夺目的内陆山城,象征著该地区的经济潜力。这一远景正在重庆的一个角落里开始变成现实。去年夏天,香港房地产开发商罗康瑞与重庆市政府官员签署了协议,成为 12 亿美元化龙桥改造项目的主承包商。化龙桥是嘉陵江边一个破败的城区。与中国其他类似的开发项目一样,该项目引起了很多当地人的不满。今年 3 月,当地居民组织了抗议活动,控诉政府没有把罗康瑞的公司支付的拆迁补偿款全部交给他们。
但是,改造项目仍继续进行,一期工程历时十年,计划于明年初动工。在罗康瑞的瑞安集团(Shui On)驻重庆办事处,可以看到该项目的模型,其主体建筑是一座长江帆船形状的大厦。这幢摩天大楼是市政府坚持要求建造的,因为市政府喜欢它的效果。罗康瑞对此有何想法呢?他说:“如果不计土地成本,建造这个楼或许还值得。”他把重点都放在这个项目的其他工程上,比如有吸引力的低层楼群及宽阔的草地。
化龙桥有可能在十年内成为中产阶级的街区,就像目前的北京或上海。当然,重庆永远也不会与中国东部城市一样富裕,但已经比六年前有很大改善。重庆已经遭受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管理不善,如今它有望成为所在地区的经济中心。虽然在这个地区的 2.5 亿人口中绝大多数是穷人,但收入在不断增长,期望也越来越高。当然,重庆与其他内陆城市一样,需要更多“进军西部”的投资,才能抓住这次机遇。此外,它还要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留在西部。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