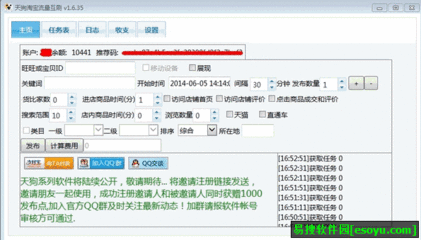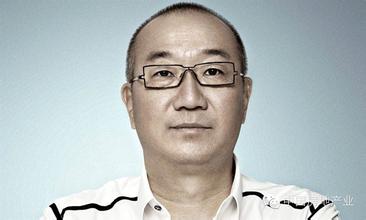每个人一生经历的事情都会在表达上留下痕迹,有的人成了哲学家,有的人成了诗人,有的人成了幽默家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冯仑会说话。
大凡朋友聚会、论坛演讲,冯仑在,总有好听的。咋一听,此君口无遮拦,话语往往向下三路集中,细一想,这个人说得还是有道理。
在饭店吃饭,冯会对妻子说:“我要一盘猪的碎尸肉。”
冯仑讲的“段子”流传甚广,但冯仑说:“我其实没有说过‘段子’。”他可能觉得,把自己的精彩言论归为那种东西实是贬低了它们的价值。
在冯仑那里,说什么和怎么说浑然天成,同样别致。一个企业家,如何有这许多修辞手段?
一个地痞流氓,一个思想者,一个高明的企业家。冯仑说,他的话,不同的人听出了不同的味道。
横着说
“对一件事情肯定或者否定,都很简单,而且现成的流行的判断,拿过来很容易,只是不能给人太多东西。”不想人云亦云,跟着别人不假思索地说好或者不好,怎么办?“我只有横着说。”
在“儒家文化与世界级企业”论坛上,冯仑的演讲煞尾。前面诸位都大谈儒家思想在企业里的应用,冯仑说:“儒家文化跟世界级企业没有关系。它是有用,是后来有用,当企业家变得伟大以后,它可以为之化妆。”他以现场的礼仪小姐为例,说每一位嘉宾上台都有一位小姐陪着,“是因为有了这位小姐你才成为嘉宾的吗?不是。儒家文化于世界级企业,就是礼仪小姐。”
冯仑为会场带来了鄂然和笑声。事后,他承认这个命题是可以探讨的,但是结论不存在。而他的感觉是,现场的嘉宾都在努力证明这二者之间有必然关系。“这不是个大事儿,但是个事儿。人睡醒了出门的时候披着一件衣服,其实没这衣服也没什么。你勃起不是靠衣服,但是没穿衣服的时候勃起就丢人。”
“人类有很多东西是荒谬的。你比如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环保,这是对的,但是太过分了就不对了。我会反过来问,地球舒服了,人不舒服了,我要地球干什么?什么事情都有个限度。”冯仑对盛行的各种危机论也持鄙夷态度:“这也危机那也危机,你知道当年人类会为了盐打仗吗?现在谁还抢盐呢?人类对未来的预测大部分都过于悲观,但事实的发展都是乐观的。”
冯仑说:“当别人认为一件事情有绝对的是非标准的时候,我看见的都是相对的。”比如爱情,冯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东西。他认为,爱情是私有财产继承制度伦理化的一个包装——要保证财产由自己的子女继承,由对偶而配偶,最终成为一夫一妻制,并且被美化:一对一叫多情,一对多就叫滥情。“人们都说追求爱情,要是有,保存就行了,还追什么?”
冯仑习惯于把神圣的东西“掰开了揉碎了”来看,让大家看到“原料”。“不是我失望,而是世界本来如此。你希望,只是你的幻想。”冯仑自认是一个企业家,但他不认为办企业的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企业家是什么?就是职业运动员,就是刘翔,为了那一瞬间的辉煌拼命努力,他身上每一块肌肉的配置都是有标准的。一般老百姓也锻炼,但是没有标准,那叫健身。”
渊源
以男女之事譬喻,在冯仑那里可谓信手拈来。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庸俗的喜爱。“其实大家本质上都是喜欢庸俗的——关起门来做的事都是庸俗的,吃喝拉撒睡,做爱,发火,每天能离开吗?你用这些东西说事儿,全世界的人都懂,但你往高说,很多人就不懂。”
但是冯仑并不同意自己说的是“段子”。“我最多是像李敖一样,把正经的事用荤的素的、俚语的、民间的方法揉碎了说,有时是性解释而不是诲淫。李敖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不勃起没什么用,勃起它就不能少。这叫段子吗?不叫段子。很多人不明白这里面的深意。”
十几年前,冯仑的说话方式并不是这样。他回忆那时候自己的口吻更像是一个机关干部。“你一生经历的事情都会在表达上留下痕迹,并不是有意为之。如果你无罪坐牢一年,癌症误诊,非典疑似,受了这么多委屈,还能心平气和去吹捧、大家说好你也说好吗?”冯以此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说话方式是被扭曲(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经历过一段难言的磨难)的结果。“我糟蹋自己总可以了吧?我娘的儿子我做主,我想欺负他就欺负他。”

冯仑自称是一个混合体:资本家的工作岗位(万通董事长);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15岁入团,20岁入党,满脑子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创业初期一穷二白,苦苦挣扎,所以说很多糙话、猛话),以及自由文化人的精神享受。流氓无产阶级生活方式沉淀下来,形成了一种自由思考的方式,而在表达的时候又把流氓无产者的生活经验加入进去,是谓相得益彰。
冯仑说自己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旧书,所以文言功底很好。他又喜欢鲁迅,认为鲁迅的语言就是文言、俚语等的结合。20年来,冯仑坚持不懈地读各种“小报”——他称为“最庸俗的那种”,脑袋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事情。他知道重庆有一个人具备两套生殖器官,“而且都用过,都生了孩子,一个叫爹,一个叫妈。”“要学会看非正常的人生,”冯仑说,“要去看监狱、产房、火葬场、精神病院。”这话一百多年前一位叫爱伦坡的美国作家说过。
从本科(经济)到博士(法学)给了冯仑逻辑训练,而阅读小报丰富了他的民间语汇,增加了他看待事物的角度。他对讲嫉妒、仇恨、放屁、接吻的书充满兴趣。
如果说冯仑的表达方式是被“扭曲”的结果,那么,他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并将之升华为精神享受。“不是只在台上这样,台下比在台上还猛。”拥有听众自然是让人惬意的,而只有风格鲜明的人才能抓住听众。“你看任志强,总是一股愤青的味道,实际他是很严谨的,但吸引大家的是他的情绪。这就是风格。”
脱光了衣服说话
冯仑不喜欢那种“穿着礼服,拿着讲稿,端着酒杯,在各个PARTY瞎转”的生活,那让他感觉不真实,太累,就如同他不喜欢高深的华丽的用语。“人穿衣服的最高境界是穿出没穿衣服的感觉,裸体是最舒服的。语言的最高境界是让人注意不到语言,大家一听就心领神会。要是大家不断问你这个词什么意思那个词什么意思,等于你穿了很多衣服,谁也没看见什么,失去了表达的意义。比如你要给人讲解男性生殖器,你就告诉他这就是个□□(此处删两字),他马上就听懂回家了。一定要透彻,让思想赤裸裸地在世界上行走。”
冯仑认为,一个人要做到达观、犀利,首先自己必须是真实的。“你不真实,你就看不见真实。内心要自然、平静,极度放松。当然,还需要思考和阅读。”而为了传播观念,一个人就要具备多种语言系统,比如不同国家的语言,不同阶层的语言。“你可以用英语说,也可以用汉语说,可以用学者的语言说,也可以用流氓的语言说。这样,任何场合听众都爱听。”
以前王石不能接受冯仑的说话风格,总建议他改一改。前不久,王石对他说,其实这样效果挺好,并不影响形象。这让冯仑感到高兴。冯今年45岁,前22年在西安度过。他说西安骨子里非常骄傲,因为那里曾是帝都。“对外人都很给面子,但内心非常固执,你说你的,我就是不改。”
尽管话语充满“谐谑、反讽”(冯仑自称),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一些事物的坚定信念。“我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前景,真的是深信不疑。”
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语言是思维的媒介。像冯仑一样说话,就是要像冯仑一样思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