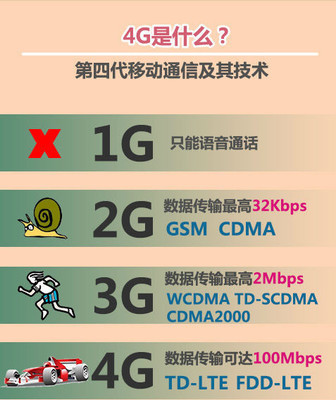被指责为“别有用心”的“泡沫论者”左小蕾,自称只是在与资本市场的潜规则作战
文/本刊记者 钟加勇
“我不会一直盯着大盘,我只看一下结果。”
现在的左小蕾,是一个刻意和热闹股市保持适度距离的经济学家,和其他那些局内人不同,这位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坚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去观察股市。然而,她没有想到,随着股市一再疯涨,自己却身陷“空头”的责难之中。
“其实,我发现,人们并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左小蕾感到些许的遗憾。这位股市上著名的“泡沫论者”调侃地说,“如果说涨就是看多,我应该是看多派。因为我是最早预期股市将来有泡沫的,而股市不大涨,哪里来的泡沫,不过涨势是否合理,是看‘多’和看‘泡沫’的区别。”
一些网友指责说,由于听从她的预测而错过了大好赚钱的机会;一些市场中的“牛派”人物,甚至在公开的会议上连连向她发难。有人怀疑她唱空、打压股市,就是为了能让QFII抄底,她摇头,苦笑。
那么,真实的左小蕾是什么样的呢?
6月22日,记者在金融街采访了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那一天,沪市跌了近140个点,掀开了新一轮调整的序幕,按说这正是“空头”预言家乐于看到的情景,但左坚持对此不作评论。
可是,不说股市的左小蕾还是左小蕾吗?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三个半小时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还是涉及股市,其间,左小蕾没有喝过一口水。
“我们那一代人很看重精神层面的荣誉”
这是怎样的一间办公室。地上、桌上、书柜上,到处都是一摞摞形同小山似的书籍和研究资料,本来用以接待客人的茶几也被其占据。采访时记者就坐在左小蕾办公桌的对面,可是须仰视和侧身才能越过资料书籍,看清对方。
无论是大学时念数学系,还是后来所从事的职业,左小蕾所处的位置都是男人们竞相争抢的地盘。
当时在武汉大学数学系,两个班一共一百多个学生,只有七八个女孩子,所占比例不到10%,而后来选择经济学,进行理论研究的就更少了,“因为数学、经济这些东西很枯燥,好像不太适合女孩子,女孩子应该比较感性、浪漫和情绪化。”
左小蕾喜欢用很严谨的逻辑和思维方式来对待生活中间的很多的问题。她是一个理性胜过感性的人,对于自己的经历和人生,她很少用戏剧性的语言来描述。
她出生在武汉。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每个学校都有一个红领巾大队(少先队),她就是大队长。
那时候,左小蕾的梦想是打乒乓球,小小的她当时就被挑选进入业余体校训练,并且打到了武汉市汉阳区的冠军。她至今还记得当时的老师对她说:“左小蕾,希望有一天看到你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小学毕业的时候,武汉市办了一个综合性的体育班,招一些将来有前途的体育人才,她又被选上了,只是父亲比较保守,认为小孩子不能玩物丧志,所以没签字。后来左小蕾总跟父亲开玩笑说:“你扼杀了一个中国乒乓球的新星。”
“我挺努力,挺认真,从小就是这样,给我机会我就会努力。”左小蕾说,要不是因为打乒乓球,那时候她也有机会去少年宫学音乐指挥。“其实不是我有天赋,主要是我比较努力,总能够不负众望,所以我得到许多机会。这是后来我理想化的基本原因,因为一切顺利,因为一切都很美好。”
如果说有什么不好的,就是小学毕业进中学的时候,可能因为父亲是走资派,左小蕾没有被选上去北京串连。这是她小时候遭受的最沉重打击,因为“原来自己是全校一千多人选一个都能选上,而现在一个班选好几个都没被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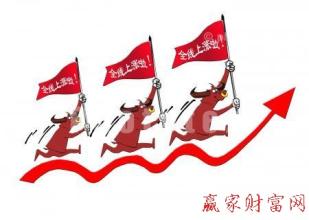
左小蕾说:“我们那一代人很看重精神层面的荣誉,很理想化,我们奉行先做人后做事的原则。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看重别人对我这种品质的认可。我不在意你对我的观点有什么争议,都能接受,但是如果你是无中生有、刻意诋毁的话,我是不能接受的。”
大学期间,左小蕾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汤敏,现在的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们是武汉大学的同学,大学毕业后,两人同时被挑到国外留学。当时的使命是,学术要跟国际接轨,要看懂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文献和模型。出国的时候,左小蕾去了法国,汤敏去了美国。两年以后两人在美国会合。
左小蕾的印象中,当年武汉大学数学系的同学,成为夫妇的共有3对,但到现在只剩下他们夫妇还“志同道合”。“我们两人互相欣赏,除了经济学以外,很少讨论别的东西。”左小蕾说。显然,左小蕾对自己的家庭十分满意,儿子今年考上了斯坦福大学,丈夫在她的心目中是个坦荡君子,有水准,有修养。
左小蕾和汤敏第一次在国内引起反响的合作是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国家正在想办法扩大内需,两人于是提出了“大学扩招的课题”。这项建议后来由于就业难而引发一些争议,那已经是几年之后环境变化的事情了。在左小蕾看来,“起点公平是这个社会最需要的,而扩招就是这样的机会。”
2001年,左小蕾就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选择银河证券,也是歪打正着。”她说,此前自己一直当老师,上大学之前已经是中学的数学老师,后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亚洲管理学院也是教书。
“首席经济学家服务于3000万投资者,我在为13亿人做事情”
怀揣美国伊里诺依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左小蕾回国以后才感觉到,中国依旧处于转轨之中,它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法规的框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大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就会出现很多的偏颇。“一些临时的规则逐渐地被人演变成潜规则,然后大家就长时间按照那些潜规则去做,而越来越多的人就认为那个规则是市场规则,其实不是。我比较理想化,我认为潜规则就是不对的,哪怕你阶段性地把它变成了一个东西,它也不是真理。”
“每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可以诉求你自己的利益,但是你不能伤害别人的利益。这个观念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这里这个概念很淡薄。有人可以无限制地诉求自己的利益,不管伤害到别人多大的利益,因为没有规则限制他。”左小蕾说。
她虽然看到了问题所在,但有的时候也无可奈何。“我们遭遇的一些观念上的冲突,显得我们太理想化了。”左小蕾说,海归总被人教导: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国情,存在就是合理的,你是海归,你们不了解国情,你们不了解情况。“但我觉得这本身都是些误导的东西,不是我们不了解,而是认为这些被认定的‘天经地义’的东西应该被改变。”而她惟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不停地去说。
最近资本市场发生基金的老鼠仓的问题。在听到各种为事件开脱的说法后,左小蕾认为老鼠仓是对投资者利益的最大损害,不能因为基金经理不能直接投资基金赚钱,就破坏规定、伤害投资者的利益。
在左小蕾看来,因为监管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把所有的违规违法的行为查出来。一个没有漏网之鱼的监管体系,全世界也做不到。美国的安然事件也是出来以后才发现监管上的一些漏洞,所以后来就出了个《萨班法》,死死地管住。关键是查出一个就要严加惩处,才能有震慑作用,才能遏制没有被查处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对那些违反规则的行为不认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个很糟糕,这就造成一个法不责众的局面。”
左小蕾说,我们的股市很有意思,涨的时候它不愿意政府去干预,但是跌的时候它很需要政府去托市,不是从规则上来说的,而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取舍的。
左小蕾认为,中国的股市为什么不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上没有一个首席经济学家这样的群体,他们来认真解读政策,把宏观经济大形势和证券市场联系起来,做一个很好的梳理,在理论上做一个很好的诠释,引导大家。
“我努力想扮演好这个角色,可我发现越来越难。”左小蕾叹了一口气。“国外经济学家对应的投资者群体不太一样,整个水平都很高,无论是基金经理还是一般的投资者,只要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都有这样的基本常识,比如说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华尔街的首席经济学家比我容易。”左小蕾自言自语道。
“如果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就是我把更大的利益群体当作我的客户,超出我的服务范围。”左小蕾解释说,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它并不需要你这样做,但你这样做以后可能对整个经济有好处,换句话说,“我是在为13亿人做事情,但是首席经济学家为3000万投资者服务就够了。”
“看报看题,看书看皮。现在干脆也不看书不看报了,就看网络上的标题。”左小蕾这样来形容股市高涨下人们的心态。
对于一些人向她频频发难,左小蕾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看她的文章,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他们老说我看空市场,其实是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
左小蕾顺手抄起手边的《非理性繁荣》一书说:“泡沫在这本书里面说得很清楚,就是 ‘反馈循环理论’。我们的新股发行刚开始引起第一轮高涨,然后这个财富效应就吸引新的投资者进来,资金一轮一轮的增加,工行的6800亿、中行8000亿,到了人保就是10000亿,到了交行和中信银行就是13000亿、14000亿,交易量不停地放大,价格不断地被推高,这就是所谓循环,这就是泡沫。第一轮上涨的财富效应吸引新的资金,推动第二轮的上涨,新资金再进去,又把它推高,推高了以后这个更大的财富效应就吸引更多的人,更多的资金进去,资金推动资金,这就是投机性泡沫的形成。”
“有人鼓吹纳斯达克崩盘之前是大涨,日本金融危机之前也是大涨,东南亚也是如此,所以中国资本市场现在也会大涨。”左小蕾说,这样说话不负责任,我们既然看到它大涨了以后就要掉下来,为什么就不能让它更理性一点、更平缓一点?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推到那么高的位置?为什么一定要经历那种大涨以后又大跌的崩盘?
在左小蕾看来,当整个市场都非理性之后,只有政府有办法让股市炒作停下来的。“就目前政府出手的这几招,就有可能使中国避开了一次经济危机。”她指的是政府提高印花税,查处违规资金入市和非法交易,财政部发债回收流动性等。
“台湾在走到12000点之前有三次这样的调整,最后还是被推上去了,这中间就是因为政府的犹豫,股民跟政府博弈,进一进,又退一退,结果在最后一次调资本利得税的时候一下就崩盘了。”她说。
左小蕾办公室的对面就是城方街,平时一抬头就能看到对面的银监会和央行。她突然指着对面,调侃地说,“我监管他们。”清彻的声音似乎透过了玻璃窗。
最后,左小蕾不忘叮嘱一句,“别写股市!”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