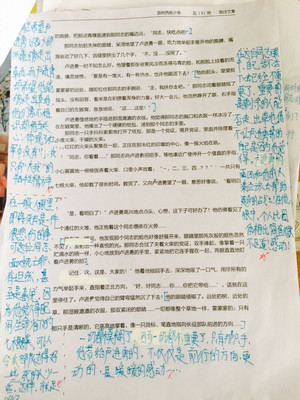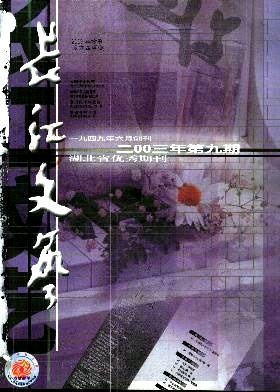一个社会的刑法要不要去依据、尊重这个社会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凝聚力?这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
文 | 梁治平
中国人很讲“名分”,从孔子开始就在讲,这“名分”不光是个家庭的原则,也是一个政治的原则。所以家庭的伦理和政治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宗教的一个基本的特点,比如五服制度。这些是在法律里面,堂而皇之列在上面的,作为法律的一个适用的准绳。清末(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1906制订《大清新刑律》)为什么会围绕《大清新刑律》产生一些争论的焦点?就是因为现代法律里边这些东西完全归零,完全“拉直”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等差的关系没有了。这对儒家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整个礼制礼教,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原因,是人的定义一个部分。
像黄宗羲、顾炎武当年讲的,“亡国”,是一家一姓的问题;“亡天下”,是神州陆沉,实际上是指文化的问题,文化倾覆了,那就是亡天下了。所以当时围绕这个法争论的时候有人就说,当时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一国的问题,是一个天下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有争议的两条,第一个就是“无夫奸”的问题。“无夫奸”实际上就是说,和没有结婚的女子通奸是不是犯罪?在传统的法律里面是犯罪的,“凡合奸,杖八十。男女同罪”。第二个就是“子孙违反教令”。规定也是很清楚,而且还有解释:“教令可从而故违,家道堪奉而故缺”,你自己一贫如洗,自己都没有吃的却不养,那可能还是可以原宥的。但你自己还过得不错,你对父母不奉养,那个就叫做“违反教令”,要杖一百。另外就是说必须要祖父母、父母亲“亲告乃坐”,就是不告不理,必须是自诉的案件。就这么两条,争议非常大。当时争议的双方是在报纸,在论辩中提出了很多的观点,里面实际上都涉及到现代性、现代法的一些方面。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律与道德的问题。中国法律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法律去执行道德的要求,所谓“出礼则入行”。你违反了礼的规范就可能会带来刑罚的惩罚,所以在当时和无夫之妇通奸,就肯定犯罪了,犯“无夫奸”。
那我们来看他们这个论辩。沈家本是修例大臣,也被说成是中国法现代化的开山鼻祖。他就说“今日学说家多主张不编入律内,此最为外人着眼”。意思是说,你把这样的东西归进里边去了,说轻一点是贻笑大方,很耻辱,说重一点,人家外国人就说你这法律不行啊,还是很落后,很野蛮,所以说“此事有关风化,当于教育上别筹方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法律编制局也说“礼之与法,分为二事。风俗改良,端在教育”,实际上呢,就是要礼法要分开。
另外一方,像劳乃宣,保守派方面的一个主干,讲了三点来批评这种主张,而且他非常准确地把对方的问题归结到法律道德两分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第一点。劳乃宣说,把法律和道德分成两种东西、把法律看成是无关于道德教化之事,“一味摹仿外国,而于旧律义关伦常诸条弃之如遗”,是站不住脚的。在他看来,西方的刑法也是根据西方的礼教来的,天下的刑法都是从礼教出来的,而你们现在要把这两样东西分开,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二点,“无夫奸”这个罪,如果你从效用的角度上来说,“禁之无可禁,诛之不胜诛”,所以不应该禁止,那还有其他的罪行呢,法律上不也是无能为力吗?比如吸毒,就是抽鸦片烟,赌博,甚至更严重的杀人放火,这些罪你是不是都能够说因为法律没有办法去阻止它,你就让它放到教育上去,不用法律去惩罚?所以这是从效用上来批评。最后一个,“畏外国人指摘,独不畏中国人指摘乎?“,就是说从这个认同的方面来说,法律到底是为谁而制定的?你到底是要给外国人看的法律,还是要给中国人,要不要符合中国人的习俗道德,符合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
其实这三条满有意思,这个守旧派并不是说,这是祖宗的礼教,我们不能改,不是简单地这样,他们是有论辩的。
道德与法律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还有非常著名的一场关于风化问题的争论,就是关于像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是不是法律要去干涉?那时有个叫德福林的,主张干涉,但是另外有一个委员会专门作了个调查,写了个报告,关于英国的这个社会状况、法律的改革等等,然后就是说这个问题上法律该不该介入。当然今天,几十年以后同性恋还可以结婚了,变化很大,在当时的英国,这根本是无法想象的,法律根本不可能去承认同性恋,最多是不处罚而已。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家之一的哈特就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说法律不应该去干涉这些私人的事情。而德福林则代表了传统的比较保守的英国法律传统,认为法律不能脱离道德。
一个社会的刑法要不要去依据、尊重这个社会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凝聚力?这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晚清当年是简单的处理的。在中国的这场论争当中,没有时间、也没有那种机会坐下来仔细地去梳理它,只能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处理。
关于道德和法律的界分,如果从我们比较熟悉的定义来说说,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量来推行的这种规范,道德呢靠公共舆论。但这个定义可能是有问题的,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逻辑化的、形式上的定义。任何规范都可以是法律,任何规范都可以是道德。比如说同性恋,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那大家就认为它是法律,因为这是国家强制力来禁止。十九世纪英国的文豪王尔德,就是因为这个有伤风化嘛,娈童癖,被法院审判定罪了,这种情况这个很多社会都会有,所以这个定义不能够解决道德与法律边界的问题。
那还有一种定义就说,我们可以把道德和法律看成是一个内容上的区分,就是说这个内容就是道德,你就不可以把它变成法律。但是如果这样来分的话,那标准在哪里呢?这个标准就不是一个逻辑的标准、不是一个形式的标准了,它是一个实质的标准。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标准,看你这个社会,你这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道德的偏好。那么在当时,在这个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那么这个道德偏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认为“无夫奸”是有罪还是无罪呢?可能像劳乃宣他们反而是代表了中国的这个文化的、社会的那个判断。而新的法律呢,更多的是从西方而来。当然,西方在十九世纪以前,“无夫奸”也是犯罪的。换句话说,这在西方是一个演进的一个过程,它在历史上曾经被认为是犯罪,后来被认为不是犯罪,为什么他认为不是犯罪呢?那是因为我们说的新教伦理、个人主义等一系列的近代的发展。所以到了哈特的时代,问题仍然存在。但是近代的自由主义国家,它把这个公共的生活跟这个私人的生活分得很清楚,而且认为国家是一个中立的国家,那这个国家就不应该去干涉私人的道德,法律就不应该去干涉私人的道德。宗教,打个比方,就变成私人的事情。
正好这个时候中国和西方相遇,那么西方带来的法律从内容上和中国的这个法律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区别。而如果你这个法律要考虑西方人的标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牺牲掉中国人的标准。
我们看现在今天中国,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案件,在这种案件当中,善良风俗的问题,要不要在法律中加以考虑?因为《民法通则》里面还是承认善良风俗的规则的、原则的。2002年的时候,四川南充中级人民法院判了一个关于财产遗赠的案件。这个遗嘱人,是把那个遗产赠与“二奶”,正妻就出来反对,对簿公堂,最后呢,法官判定是违反善良风俗,遗嘱无效,据说那个庭上一片掌声。这样的法官是得到民众的支持的,但是呢,我们法学家基本上一面倒地就是批评法律和道德混到一起了。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来去认识?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课题其实是非常大的。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梁治平先生2008年1月12日在传习社的讲座“法与现代社会”实录的节选,文稿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呼应·延伸]
不靠制度的管理
文 | 肖知兴

梁治平先生这一段探讨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在企业管理层面,相对应的问题是制度与价值观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如果说在国家层面,中国传统的思路倾向与夸大道德的作用(所谓泛道德主义),法律沦为道德的助手和附庸;在企业管理层面,中国人习惯的做法却是夸大制度的作用,忽视甚至藐视企业统一的价值观所能起到的作用。
其实按秦晖老师经常用的“共同体”的概念,治理国家这种大共同体,政府应该紧紧守住法律这条线,不要擅闯私人空间;而企业不管发展到多大规模,相对而言,仍属于小共同体,企业成员之间存在密切的利益和感情关系,道德,也就是企业的价值观,能够起到的促进合作和推进共赢的作用,往往要比在国家层面大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人们对中国这几千年来的泛道德主义专制文化的一个反对吧。一方面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类的满口仁义道德,另一方面是“宁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荒淫无耻行径,中国人见得太多,大家对陌生人的诚信水平的心理期待早就落到了冰点以下。所以,一谈到管理,大家的第一直觉就是靠制度,而且往往是瞄准人性最为幽暗角落的那种惩罚性的、提防性的制度。西方从基督教的性恶论出发,努力在公共领域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诚信体制,消灭了对陌生人的恐惧,扩大交易的范围,奠定了企业更多地依靠价值观来进行内部合作的基础;中国人从孔孟的性善论出发,“满街都是圣人”,最后却陷入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交易成本无比高昂,企业内部合作的价值观基础,自然是荡然无存。
成本高,这是用制度来管理员工行为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例如,一个简单的考勤的问题,从自觉,到签名,到打卡,最后到按指纹,成本自然是一步一步上升。从中得到好处的,是劳动法律师、考勤机和防盗门的生产厂家。很多中国民营企业迟迟过不了规范化管理这一关,按他们的说法,不是因为他们认识不到规范化管理的好处,下不了决心,而是因为“太贵”:付不起请咨询公司和职业经理人来进行大规模地建章立制的费用。
第二,计划赶不上变化。任何制度制订的基础都是对可预测的环境作出的一种程序化的反应。但环境天天都在发生变化,制度怎么办?所以,更可取的办法是努力让大家接受制度背后那些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原则、精神和价值观,郭士纳接手IBM的时候,他知道,最最重要的不是去改变IBM各个部门那时很多已经过时的具体规章制度,而是返回传统,重新回到老沃森的三个基本信条:“追求卓越、优异的客户服务、尊重个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八大原则”,从而建立一种“以原则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教条为基础”的管理。所以,和所有其它伟大企业一样,IBM百年变革的背后,真正起支撑作用的不是具体的制度,而是他们不离不弃的核心价值观。
第三才是最致命的:制度,尤其是那种提防性的制度,有一种自我繁衍的内在倾向,制度生成新的制度,新的制度生成更新的制度,直至无穷。管理层忙于这些内部事物当中,丧失了对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敏感;被管理者诚惶诚恐,所有的精力都耗散到如何明哲保身这些事情上,创造性的劳动根本无从讲起。一财经杂志编辑跟我讲起他们的老板决定监视员工上网的事情,不胜其烦。好了,既然决定监督上网,那就得有人去做一个“与工作无关的网站”的定义和列表了;任何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发生争执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又要组成一个“网络使用委员会”来裁决有争议的情况了……最可怕的是,你既然把我当小偷防,我不偷点东西就对不住您老人家。
道德是私事。企业管理属于私人领域,所以作为企业价值观的基础,领导人的道德的问题就成为一等一的问题。与梁治平先生提到的“无夫奸”问题相关的是,一些老板私生活不检点,娶二奶,甚至要离婚,换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老婆的问题。不管是“有夫奸”还是“无夫奸”,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好像是屡见不鲜了。在中国创业有多难,太太不管是创业团队的一员还是家里的贤内助,对丈夫的支持和做出的牺牲有多么重要,大家心里都有底,你“一阔脸就变”,嫌弃家里的黄脸婆,员工怎么看你?员工或者不知情,你身边的一起打江山的高层团队怎么看你?你能这样对待曾经情深义重的结发之妻,你将来会怎么对待我?因为类似这种问题而断送企业发展前景的例子,我们身边应该都不少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