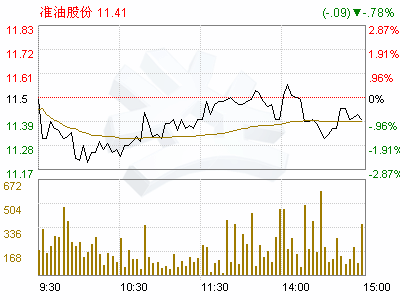企业研究院主要是为公司从事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和技术创新。如果不把它当战略来做,没有先进的研发机制,很难成功
文 | 本刊记者 王勇
“如果把中国本土企业的研发看成一个糖葫芦串:最前面是商业化,中间是应用研究,最底层是前沿研究。整个糖葫芦串的水平都不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系统结构研究部主任孙凝晖如此评价。“即使是中国过去10年所做的所谓填补空白的工作,其实质也是用二流技术来满足国人的需求。”
这得到了微软全球高级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的认同。“中国的科技界和产业界有一个问题:基础研究不基础,应用技术不应用。大学和科研院所不该去想太多的市场,热衷于做企业,或者把获得国家级评奖作为目标;企业所做的研发则往往偏离市场很远,普遍都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张亚勤说。
原因有很多,中国企业研发体制的落后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时至今日,全球化的研发已进入第三代研发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企业的研发活动有明确的策略;另一方面,企业在制定战略时,是以充分考量企业的研发预期、研发能力为前提。在这种模式下,研发成为企业整体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与企业整体的流程融为一体。研发不仅仅是企业管理者关心的事情(正确地做事),而且是企业领导者关心的事情(做正确的事)。
中国企业近年来纷纷加大了对研发的投入,联想、华为、中兴、海尔等极少数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甚至已经超越了定义做一代产品的阶段,组建了企业研究院,开始探索建立世界级研发体系的道路。
“企业建立研究院是大势所趋。事实上现在中国企业的研究院也是越来越多,但这类机构有个特点,它主要是为公司从事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和技术创新。如果不把它当战略来做,没有先进的研发机制,事实上很难成功。”在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总经理杜江凌看来,中国已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具吸引力的研发地,未来一定会成为全球的创新科技中心,但中国企业缺乏组织一流人才进行研发的体制和方法论,缺乏有长期发展的战略和长远的心态。
显然,在“中国制造”艰难地向“中国创造”转型时,谋求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上移的中国企业需要更先进的研发管理模式,需要了解更多全球顶级企业是如何运作的,需要知道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构建世界级研发体系的正确选择,从而避免前进道路上的陷阱。
至今,微软和英特尔在华设立研究院已经十年。有鉴于此,《中国企业家》选择了微软、英特尔、联想三家全球顶级企业,从组织、制度、文化三个层面入手,展示出第三代研发的不同侧面。微软怎么做基础研究,英特尔如何将研发与产品相结合,联想在构建世界级研发体系上的艰难探索,为探索阶段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借鉴。
[案例1]
微软: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
微软用自由度和鼓励创新做成世界级的基础研究
“事实上,我很反对大部分企业建立研究院,那是一种误导。”微软全球高级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对《中国企业家》明确表示。在他看来,基础研究是公司管理者最痛苦的战略决定,只有企业拥有一定的实力才有能力成立专门的机构做基础研究。
微软亚洲研究院(简称MSRA)正是这样一个机构,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甚至将其誉为“世界上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它1998年从3个人开始起步,2008年已拥有350多名研究员,占微软全球研究员人数1/3以上,是微软在美国以外最大的研究机构。
短短10年间,它把超过260项创新技术转化到了微软产品中,获得了近千项专利,有多项技术被国际专业协会指定为行业标准,并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和期刊上累计发表了3000多篇论文。特别是在互联网、人机界面、多媒体、搜索等领域,MSRA发表的论文数量占了世界第一流期刊和会议上发表的10%。
有史以来,没有任何公司级研究单位能做到这点。MSRA成功背后的奥秘是什么?
研究自由度
“MSRA的成功跟微软大手笔研发投入是密不可分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告诉记者,微软每年投资在研发上的资金在80亿美元以上,是全世界在研发上投资最多、比例最高的公司,而且长年坚持。
“Windows是1985年开始推出的,一直到10年后Windows95出现才真正成大器。Windows Server是1991年做的,直到2000年才真正赚钱。”洪小文说,像这样的项目,其他公司早就砍掉了,但微软坚持赔钱做很多长期的工作,这样才能确保在科研方面的优势。事实也证明了这种策略是能带来丰厚回报的。
洪小文承认,这样的投资规模不是普通企业支撑得起的,但他强调资金只是一个方面,是否具备这样的魄力和战略眼光更为重要。
他认为,数万人的微软,简单看来,可以分成销售、产品开发和研究院三块。研究院是三个部门中最小的一块,人数只占公司的1%左右。“销售部门是赚今天的钱,产品开发部门赚明天的钱,研究院则希望赚后天的钱,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研究院正是这样一种长期投资。因此,虽然金融海啸肆虐全球,但微软依然在加大对研发机构的投资。张亚勤说,“未来三年,我们计划在中国用于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将超过10亿美元,这些投资不包括在中国的合并和收购。”
张亚勤不赞成企业办研究院,但认为企业应该有个工程院,因为企业毕竟是营利机构,做好下一代产品开发要比做基础研究迫切得多。但MSRA建立时,微软在中国并没有什么产品开发可言。
“很多公司是先在中国做产品开发,到一个地步才成立研究院,而微软恰恰反过来。”洪小文认为这是微软研究院在创建时与众不同之处。微软当时看中的是中国的人才,而非中国的市场。
随着技术的不断积累,MSRA越来越感觉到技术产品化的需要。于是在2003年,MSRA几位资深员工着手创建了微软亚洲工程院,这是微软在中国的第一个比较原创型的产品开发部门,定位是做明天的东西。2005年,MSRA又孵化了搜索技术中心、服务器与开发工具事业部等部门。2006年,这些部门被整合起来,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简称CRD)就此诞生。
洪小文以此为傲。“我们是整个CRD的源头,如果把这些部门看成不同的公司,相当于MSRA的人出去创业。我们在做最高端的研究,在替公司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创造新科技,同时也培养出了一批最好的人才。”
在他看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研究自由度的重要性。MSRA本身并没有清晰的定位,研究员只做技术研究,不管应用,但事实上MSRA很多技术成果得到应用。“从长期来看,做得好的技术总会对社会有用。”洪小文说。
他强调,MSRA对外宣称研究员自由度是100%绝非虚言,即便是他也不能强迫研究员去按自己的想法做事,真正的决定权在研究员自己手中。“拿我自己做个例子,当初我做过一个语音系统,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我走的方向跟我的老板想到方向完全不一样,他不同意我的做法,但他支持我这样去做。这就是研究院所需要的文化。”
信任是最强大的竞争力
即使有资金、人才和公司的支持,做世界级的基础研究机构依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管理研究人员?怎样保证自由度不被滥用?
洪小文认为,“研究工作一定要有自发性,要自下而上。产品部门需要计划,需要有人负责,是自上而下的。历史上很多革命性的研究都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你只有创造出一个最宽松的环境,才可能做出最了不起的研究。”
平衡研究自由度和考核之间的矛盾便成了洪小文头疼的问题,他甚至认为这是研究院管理人员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一般的管理很简单,白纸黑字写清楚目标就行。研究工作却不能这样,既要鼓励研究员踏的脚步大,担更多的风险,又要去做到公平。这个平衡和取舍就很困难。比如你三年一直没出成绩,这时候怎么办?是继续投资还是把这个项目砍掉?说不定再过两个月你就做出来了。”
因此,MSRA的管理并不特别看中量化,对人的考核其实靠的是判断力。“我们尽量相信个体,相信我们雇的是最好的人,他们会对自己负责。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模式。”洪小文承认研究不能在短期内出成果,但可以通过拉长时间来解决。“时间越拉长,他们就越可能让他们的梦想去实现,也更容易考评。”洪小文说。
洪小文表示,在微软研究院内部实行的是导师制,让资深研究员指导年轻研究员和实习生,就是希望通过制度建设帮助年轻人更好的为自己负责。
事实上,洪小文目前考虑最多的问题并不是用什么样的考核机制考评工作,而是用什么样的机制去鼓励研究员创新,承担更大的风险,敢去做一些比较大的突破。“过去十年,我们比较谨慎,步伐迈的小一点,因为我们觉得必须先学会走,再去想跑的问题。我们确实做出了很多成绩,但我认为在高风险研究方面我们做得并不多。”洪小文说。
他并不担心出现过分鼓励大家做高风险研究的情况,真正担心的是考评指标忽视对创新的重视,阻碍了研究员创新的积极性。“我通常会问研究员:你两年不出成果怕不怕?我希望能创立出一套机制,对那些风险大的、周期长的研究予以很大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奖励,鼓舞更多人去做长远的研究。这是我们必须更努力的工作方向,也是未来十年中我的工作重心。”
Microsoft Research Asia
微软亚洲研究院
简称MSRA
成立于1998年11月。MSRA是微软海外开设的第二家基础科研机构,同时也是海外最大的基础研究机构。MSRA的使命是:让未来的计算机能够看、听、学,以自然的语言与人类进行交流。
[案例2]
英特尔:摩尔定律背后推手
注重反应速度和差异化保证了英特尔的研发奇迹
英特尔始终跟摩尔定律联系在一起。40多年来,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摩尔定律即将终结的喧嚣,但英特尔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推动它的持续。
“欧德宁曾经说过,绝不能让摩尔定律终结在他的手上。因为摩尔定律是关于人类创造力的定律,它已经成为英特尔人的信仰。”在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简称ICRC)总经理杜江凌看来,先进的研发体制是确保英特尔40年来维持这个奇迹的关键,而这正是中国企业研发做不好的关键。
成功的关键
“跨国公司全球研发体系在本土以外能否成功的关键有两点:反应速度和差异化。”杜江凌解释说,如果遵循全球研发体制使得反应速度减慢,任何决定都要经过层层流程到总部转一圈再下来,必然会损害到本土以外研发机构的竞争力和积极性;如果全球研发体系不考虑本地化的特殊要求,本地市场的特点不能在研发体制内反映出来,就会造成总部与海外机构沟通上的障碍。

杜江凌口中的总部,指的是英特尔企业技术事业部(简称CTG)。它是专职的公司级研究机构,现有1000多名研究员,分布在全球11个地区。ICRC则是CTG在中国的桥头堡,也是英特尔在美国本土以外最大、成立时间最久的研究机构。
ICRC的飞速发展超出了英特尔高层的想像。究其原因,杜江凌认为除了员工的勤奋,关键在于研发体系的灵活性。
“ICRC十年前成立时,大家都没什么经验,不知道工业界应该怎样做研究,于是就把美国做研发的制度和方法论搬来,我们按照英特尔全球准则来做事。但是,对于不是太大的项目,本地领导就可以决策,这样对反应速度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同时,在搬移过程中,我们也培养出了一批理解美国以外创建世界级研究机构的人才。”杜江凌说。
而对于差异化,杜江凌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ICRC的定位是英特尔全球研发体系的一个结点。他坦承ICRC走过一点弯路,认为既然是在中国,就要做跟中国有关的研究,所以最初研究的语音识别、汉字识别等,都是致力于把ICRC做成一个能独立工作的个体。但最终发现这个愿景过于狭窄,独立并不是ICRC的最终目标。
“事实上,我们大部分项目还是全球的一部分,纯本地化的项目基本上还没有。虽然跟本土有关系,但其本身也是英特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杜江凌认为这是十年来最大的认识改变。
他解释说,研究与开发联系紧密,但也有很大的不同。在产品开发方面,了解本地化特有的需求是非常必要的,但一个世界级的研究中心必须是全球化的。某种程度上,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争论在科研领域是个伪问题。
“因为本土特色产品和全球化产品之间的交集会越来越大,ICRC完全可以开创一些研究方向,领导英特尔全球在这些方向上的研究。”杜江凌认为。
逐梦三部曲
杜江凌赞不绝口的研发体制,在英特尔内部有个形象的比喻:逐梦三部曲。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做梦、选梦和圆梦。逐梦三部曲背后的支持则是英特尔的两大机制:技术战略长期规划(简称TSLRP)和携手探路机制(Joint Pathfinding)。
TSLRP是英特尔最高层的创新孵化器。它由首席技术官和企业技术事业部共同制定,是英特尔内部一年一度的流程。技术部门会对今后5-10年内会对公司产生潜在重大影响的技术做一个评估,从中选择出3-5个主题,然后成立专门的团队,投入资源进行研究,对该主题在技术上的挑战和机遇做出具体的判断,形成报告上报到公司的最高领导层。
“这是一个沙里淘金的过程,每年英特尔会在公司动员员工提出建议,鼓励大家大胆‘做梦’,发掘各种奇思妙想、甚至是具有颠覆性的创新点子和梦想。一般来说,每年会提出五六百个新点子。但这么多新技术里,只有少量的技术最终会对业务产生重大影响,所以要借助TSLRP流程‘选梦’。”杜江凌说。
圆梦则是指如何高效地把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ICRC董事总经理方之熙告诉记者,ICRC的首要职责是帮助公司的现有业务,或者通过研发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其次才是成为世界级的研究实验室。“总之,做的事情最后要见到产品上来。”方之熙说。
但技术转化是众所周知的困难环节。研究部门和产品部门在文化和方法学上的差异造成了很多的困难,经常出现技术上的工作已经做完,但产品开发相应部分的资源投入还没有开始的情况。两者之间出现一个空白地带,英特尔称之为“死亡谷”。
建设性对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特尔三四年前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了“携手探路”机制。它由公司高层甚至CEO直接领导,对处于过渡期的项目专门成立由研究部门和产品部门人员组成的联合团队。联合项目组的人员配备是否充足、资源是否到位等也成为研究和产品部门考核的重要指标。
联合团队的组建方式有很多种。当某项技术在市场上有客户需求和竞争压力时,团队就会搭建,但依靠更多的是正式机制。研究部门会把相对成熟的技术介绍给产品部门,产品部门也会把市场需要反馈回来,如果双方都有合作的兴趣,携手探路便随之展开。
ICRC通信技术实验室高级研究经理刘东介绍,英特尔有个制度叫“五乘五”。每个季度会有一次例会,CTG派出5个技术专家,产品部门也派出5个技术人员,双方联合开会和调研,最终确定出一个Top10的名单给研发部门。
“坦白说,这个单子里有些是纯搞笑的,技术上完全不可能实现,但绝大多数确实比我们想像的要好。因为就技术角度而言,你没法确定哪个技术更加值得投入。但如果产品部门告诉你,A有100倍的市场,B有10倍的市场,这个方向就很容易决定了。”刘东说。
这种携手自然也会带来冲突。刘东就曾遇到过,“当时我们去美国的产品部门做研究,产品部门觉得新来了几个劳动力,安排我们做其他工作。他们说的也很清楚,安排的工作对三四年以后的产品贡献很大,但问题是那不是我应该做的,我们越做越像他们下面的一个小部门。”
但英特尔的开放帮助刘东解决了问题。“我们和产品部门都互相理解,大家都是在找最有价值的项目。英特尔鼓励建设性对抗,对抗是公司的六大文化之一。把冲突摆在桌面上,做公开、公平的谈话和讨论,这是携手探路必须有的文化保障。”刘东表示。
而在杜江凌看来,携手探路机制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非常值得中国的同行们借鉴。“中国能做到像ICRC所做工作的企业比较少,这是实力问题,短期内不可能解决。但国内很多学校在提倡产学研联合,这方面完全可以借鉴‘携手探路’的机制。”杜江凌说,“企业就是产品部门,大学和科研单位就是研究部门,政府就是CEO。客观地说,这比一个公司不同部门间的配合难度更大,但这方面的可能性和想像空间确实很大。”
Intel China
Research
Center
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
简称ICRC
创建于1998年11月。ICRC是英特尔在亚太地区设立的第一个研究机构,是除美国本土之外最大的研究中心,也是成立时间最久的研究中心。目前的研究领域包括微处理器技术和通信技术。
[案例3]
联想:平衡短期与长期利益
中国企业早期做研究院,必须平衡好业务战略和长期技术战略规划的关系
毋庸讳言,与微软、英特尔等全球顶级企业相比,中国本土企业在研发的认识和投入上都存在巨大的差距。能够把研发提到企业战略层面,设立了公司级中央研发机构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但联想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是国内最早做公司级研发机构的企业。谈国内的研究院怎么才做得好,我们更有体会。”联想研究院院长贺志强告诉《中国企业家》,这是中国企业在创建世界级研发体系道路上的艰难探索。
定位是关键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二级研发体系,我觉得这对中国企业比较重要。”贺志强说,联想研究院以及后来成立的先进系统开发中心、创新设计中心是公司级研发,看的是未来18个月甚至是5年后的技术;事业部级研发则看未来18个月的产品,主要是做开发,各业务部门有自己的开发团队。同时,联想还建立了专门的产品链管理部,负责整个事业部研发和公司级研发的沟通。
这听起来很像英特尔CTG与产品开发部门的关系,但中国企业做研发不过是近十年的事,认识到这一点经历了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联想研发部门历史上的多次分合,便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
1992年前后,联想研发项目很多,但一直没有像联想汉卡那样创造出新的利润增长点,被内部评价为“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为了让研发部门创造效益,公司决定将研发部门并到各事业部去,直接面对市场。当软件业兴起时,联想中央研发中心再次建立。但由于与联想的主要市场几乎没有关系,集团在人力、财力以及核心领导层的关注投入上又严重不足,研发中心变成公司里的一座孤岛,几年下来一事无成,最终于1997年被再次并入子公司。
“柳总(柳传志)最后发现,仅有事业部层面的研发中心是极其危险的战略失误。”贺志强解释说,IT发展一日千里,联想当时却没有一个部门从全局层面看总体技术发展趋势,导致在新产品研发上没有战略部署,没有人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负责,这是联想下决心成立研究院、构建二级研发体系的原因。
贺志强认为关键在于定位和手段上的循序渐进,“早期我们根本不懂研发的规律,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依然在受这个问题困扰。”
在他看来,持续投入和高层支持是研究院能否顺利发展的基础,确保这两点才能谈后续的发展。“研究院成立时,我提的惟一要求是无论公司业务好坏,必须保证对研究院的长期投入。万一因为公司业务不好而卡费用,或许此前的投入就全泡汤了。”
定位则是中国企业能否做好研究院的关键。“这么多年来,联想研究院的定位上的变化非常小。研究院必须支持公司现有业务发展,同时促进公司不断的技术进步,提升竞争力。”
贺志强承认,联想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远不能与微软、英特尔相比,但他强调这是中国企业最现实的选择。“中国企业早期做研究院,必须平衡好业务战略和长期技术战略规划的关系。如果对短期业务支持不够,跟事业部没有一个良好的互动,研究院在公司内部体现价值的过程就很慢,容易被边缘化。”
相反,如果研究院能对短期业务做有力的支持,所获得的支撑就会越来越大。“最初的投入不过1000万人民币,现在则是每年两三亿元。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开始就做很深的基础研究,但现在开始越来越深。”贺志强很欣慰。
因此,联想研究院在考核中极为强调技术成果的转化,贺志强认为创新成果被事业部接受是管理研究院最大的挑战。“我们不是大学研究所,不能发几篇论文就算完成任务,最终还是要看创新是否在5年甚至8年后变成了客户价值。相对来说,事业部的价值链都在自己手里,卖出产品赚回利润。但研究院创新只是价值链的一部分,成功需要打通整个价值链,这相当有挑战性。”
打开视野
与英特尔、微软的看法不同,贺志强认为制约中国企业研究院的最大问题不是资金,而是视野。在他看来,联想并购IBM PCD是联想研究院发展历程中的大转折,研究院借此机会大幅度扩展了视野。
“视野不仅仅在于是否了解行业发展,更重要的在于是否了解全球市场和资源,是否能用好不同地区的人才。”贺志强越来越能感受到来自这方面的挑战。
“以ThinkPad X300为例,这是美、日、中三地一起研发出来的结果,以前中国团队做设计时考虑的只是中国市场,整合后所有的消费设计突然都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要跟全球设计第一流的公司去竞争,就必须要用全球最好的资源保证它能实现。比如我必须让松下把X300的DVD Driver从9毫米减到7毫米,这就是在考验联想调动全球资源的能力。”贺志强说。
除了创新要求的标杆更高,文化和经历背景的不同也是一大挑战。贺志强认为,“此前我们做项目一个PM(项目经理)就够了,而PCD要有一个PM负责流程管理,同时一个TPM(技术项目经理)负责技术管理。我们弄不懂TPM和PM怎么分工,他们很不理解只有一个PM怎么可以把这个事就做了。”
贺志强坦言,IBM很多流程让他们大开眼界。“过去联想如果有个创新技术做得不错,我们就会直接把它放在产品里,投入市场检验。但现在多了两个环节。我们首先会在整个业界做扫描,看有哪些技术跟我们差不多,或者是做得比我们好,看看这个创新是不是世界第一流的。这就是跟PCD学的。”
第二个环节是在客户沟通方面。“IBM以前是做大客户,而我们是做消费客户,所以他们的客户沟通比我们深入得多。受他们影响,我们现在进步很大,不但创新技术要找一些客户验证,在早期就会做一些验证。”
贺志强说,联想已经把双方流程中最好的部分拿了出来,整合成了一个统一的从创新到最后生成产品的流程。而且,联想研究院也已经在美国、日本、中国形成了一个“创新三角”的布局,初步具备了全球合作的能力。
“中国未来很可能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因为从IT角度讲,中国有全世界最复杂的IT应用,这些复杂的应用环境会对技术提出需求,而中国的研发人员就有机会第一时间去面对这些需求,这是中国的先天优势。”谈起联想研究院的未来,贺志强很是乐观。
“阻碍中国创新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良好、互动的产业环境,对创新的投入不应该是少数企业,应该是一批企业,中国在这方面比硅谷差很远。我相信企业做研究院的趋势会继续,而中国的创新环境也会因此受益。”贺志强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