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民义务或家庭责任的范围内,政府不能随便耗费纳税人的钱,过于积极地承担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事情。
5月25日晚,温岭一女子因情感原因,跳河自杀,男子下河营救反而双双溺亡。家长雇请民间捞尸队打捞,开价6000元一位,最后在民警协调下,共支付3000元,才得打捞上来。消息传出,引发舆论热议,有的认为捞尸队漫天要价,趁人之危,缺乏道德;有的表示“干活赚钱天经地义”;有的认为监管不到位,捞尸队才敢开高价;还有的主张由政府组织公益救助或扶持志愿救助机构,来解决问题。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子女出意外,父母肝肠欲断,再遇到捞尸队狮子大开口,雪上加霜,令人同情。联想到多年前,湖北几位大学生因为救人溺亡后,也曾遭到“挟尸要价”,所以才会有人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类似难题,提出“公益救助”的设想,听上去不错,但真的行得通吗?
先来看所谓“挟尸要价”的说法是否讲得通。春秋时期郑国有一人专靠代人诉讼为生,名叫邓析。某甲之父溺亡,尸体被某乙捞起,某甲前往索要,对方“挟尸要价”,双方谈不拢,只能作罢。某甲便找邓析咨询,邓答曰:“除了你,谁会要?尽管等着,他一定会给你。”某乙听说了,心里发慌,也来找邓析,答曰“除了你,他上哪里要去?尽管等着,一定回来要。”史书没有记载争讼如何解决,但记载了邓析最终被主政者,相国子产杀了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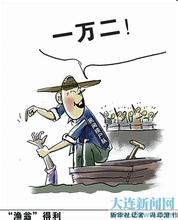
在严格意义上,上述故事中占着别人尸体要高价,才是真正的“挟尸要价”,而温岭民间捞尸队只是达不到预期价位,就不愿下河打捞而已,尸体没有在他们手里,自然也就说不上“挟尸”。虽然死者父母值得同情,但在政府未曾定价的场合,商业服务应该由双方协商着定出一个价格,双方差得再远,也不能说就一定违背市场原则:如果当地多几支队伍,充分竞争下,应该更能达成死者家属能够接受的价格,但为什么没有呢?这或许因为河里溺亡的情形不多,不可能有很多人以此为生,一旦遇到有尸体要打捞,在自然形成的垄断下,收费肯定会大大高出合理成本,或许因为受传统文化影响,愿意从事这行的人不多,才使得捞尸队“物以稀为贵”。不管怎样,对死者家属来说,有人愿意打捞,即便要价高了,也比没人打捞,只能看着被水冲走要好。
至于有人提出由政府出面或扶持民间机构,提供“公益打捞”,来避免死者家属被“胁迫”,初衷虽然不错,但会遇到有关政府公共职责的边界何在的难题。如果有无名尸体漂浮河里,为维护水体质量,防止污染,政府有责任委托或组织人员打捞之后,妥善处置,因为公共卫生和环境整洁是政府职责所在,不容推辞。现在死者是自杀身亡,亲属已来到现场,那么捞尸入殓自然就是亲属的责任,怎么可以随便推诿给“公益救助”?这就好比打捞上来无名尸体后,查不到家属,只好政府出资火化,但要是知道家属名姓,政府绝对不会主动将火化尸体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里的关键是政府的责任是有边界的,在公民义务或家庭责任的范围内,政府不能随便耗费纳税人的钱,过于积极地承担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事情。
值得深思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不少人仍然太依赖政府,甚至不顾公共职责的范围,而要求政府做这做那。有些本应交给市场来解决的事情,只要一涉及情感道德,有人就会否定市场的解决方案,而求助于政府的公益性行为,却完全忘记了政府行为最终都需要纳税人买单。富有同情心当然是好事,但因为个人的一点恻隐之心,政府就必须出面买单,那是搞错了现代公共政府的概念内涵:除了维护个人基本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不能随便作为。最近李克强总理多次表态,政府改革必须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就是这个意思。个人如果实在心有不忍,完全可以自行组建志愿机构,这样既可以避免市场上供求失衡带来的“挟尸要价”,也可以避免发生政府过度卷入个人或家庭责任的情形。在现代社会中,市场、政府和公益这三块必须分清楚,不能搅浑了。
 爱华网
爱华网



